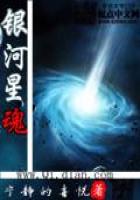认假成真舅舅甥甥弄成活鬼道真还假擒擒纵纵算就深机
词曰:
可怪狂且,诱他母子,赚入私居。恨奸恶贪婪,利伊赀橐;阴柔秘妙,计在锱铢。甥舅俄称,恩仇已昧,那怕他人不畏予。料应这,疑团未破,笑杀痴愚。 何须撒网惊鱼,不使机关一着虚。笑活鬼迷人,私相惊溃;巧妻佯纵,自号贤妹。有路逃生,无家托足,痛杀家园不我余。还应有,受恩深处,反免沟渠。
右调《沁园春》
丽容来到陈家,乔氏携手而入。走进后厅,陈与权正在那里坐等。一见丽容走近,慌忙立起身,鞠躬施礼,口里喃喃的告罪。乔氏携丽容坐下,陈与权也就坐在旁边,着实赔礼道:“前日我心上有件不得意的事,适值大嫂与我吵闹,一时出语唐突,心里至今不安。尝清夜扪心,深负干兄这些恩惠,枉做个须眉男子,甚是汗颜。故特屈大嫂过舍,一樽相敬,少谢前愆。大嫂须念往日情谊,不要记在心头吧。”丽容道:“你纵有别事在心,论理也不该把我尽情躁脾,置人于无地。”陈与权道:“天在顶上,那个说是该的。只因愚性粗直,不知不觉在口里落了出来。过后想一想,好不懊悔。”丽容道:“既是说话因性子直,说了出来,你坑赖我没有田产寄你,难道也是性子直吧?”陈与权道:“前日因心上着恼,我故意说的话,怎便认起真来。我若敢于坑赖,今日便不清来算明还了。”丽容道:“既如此说可算一算,天已将晚,家内无人,要早些回去。”陈与权道:“帐还没有写清,且慢慢用了便酒,我去誊来。”丽容道:“酒到不消吃,只求就算了好。
”乔氏道:“你又来做客,写帐还有好一会,难道空坐着等吗?”丽容道:“你这两日不写停当了?”陈与权道:“东西日日有得讨来,如何结得定数目。”乔氏道:“好暴躁奶奶,我家丈夫明日要上京,也不如此性急。你回去有多少路,却这等着忙。”便搀住手,要他进去。丽容被强不过,便道:“既是这等,只领你个情吧。”就同乔氏起身,陈与权自往外头去了。乔氏同丽容入内,大排华宴,珍羞罗列,果盒纷陈,十分丰盛。丽容问道:“今日你家的酒,为何如此齐整?”乔氏道:“一则为干奶奶在此,二则我家丈夫上京,算是饯行的酒。”丽容也不在话下,就同儿子坐着,乔氏殷勤斟劝。吃了几杯,干浚郊便要回去。丽容道:“儿子,你耐心吃些东西,停会儿就领你家去。”便叫丫头去看陈爷,可曾写完帐了。乔氏道:“丫头不知事,我自去看来。”便抽身而出。干浚郊见乔氏去了,便说道:“我酒也不饮,东西也不吃,前日他家把我母子们怎生怠慢,今日岂是真心为好?我只要回去。”丽容骂道:“小孩子家不知世事,我在此岂是贪他的饮食。
这许多田产,难道不料理了回去。”干浚郊便不敢开口,乔氏也走来了,对丽容道:“还有一会哩,你且再用些酒着。”丽容又坐了一会,看看天晚,干浚郊又只管催母亲回家,丽容只得又叫乔氏去看。乔氏方欲起身,陈与权手拿一本帐簿,一个算盘正走进来,说道:“干奶奶可曾用饭了?”乔氏道:“酒还未吃完,怎就用饭。”丽容道:“天晚了,情已领过,酒饭都不消用。”便立起身,要候他结帐。陈与权道:“大嫂来得久了,不曾用些点心,若算起帐来,还有一会,可不饥吗?”便叫了丫头,快取饭来。丫头连忙送上汤饭,丽容勉强吃半碗儿,干浚郊只一粒也不肯沾口。丽容刚吃完饭,只见一个小厮,走到门口说道:“广州胡爷在厅上,要请老爷相会哩!”陈与权道:“干奶奶在此,我要算帐,不得工夫,回了他吧!”小厮道:“他晓得爷明日起身,要来约同舟,大家省些路费,定要会的。”陈与权道:“这怎么处?你叫他坐着我就出来。”小厮唯诺而走,陈与权向丽容说道:“这胡爷与我是同年举人,也上京去会试,约我同走,只得要出去见他。大嫂宽坐一会,我顷刻就进来的。”说毕竟走去了。正是:
百丈渔竿百尺矶,碧萝磐石坐垂丝;须知香饵投来久,正是金鳞欲上时。
丽容见天已黑夜,好不焦躁,加添干浚郊又连连催去,丽容叫他先回,又决不肯。仍坐了好一会,只不进来,又促乔氏出看他。乔氏去了半晌,走来说道:“这胡爷几年不会了,今晚要留他便酌哩。”丽容道:“这怎么好?如今我只得回去,到明日再来吧。”乔氏道:“你今晚只好住在这里,这胡爷与我丈夫明日黑早就要起身,你那里再来得及。”丽容道:“怎么去得恁快?”乔氏道:“因他在此相约,附他的舟,怎好迟慢。”丽容道:“我家里无人,怎么住得在外。”乔氏道:“难道你再不出门!只须叫丫头回去,吩咐一声罢了。若必要回去,我也强不得你,不要我丈夫去后,倒来懊悔。”丽容见如此说,恐怕错过了,只得叫个丫头回去,叮嘱他同众丫头都睡在房中。再吩咐苍头,好生看管门户。那丫头应着去了。干浚郊只管埋怨道:“自己有家里不住,却住在这里。那钱财甚么宝贝,怕明日就没有了吗。”丽容心里气闷,反把他打了一下道:“畜生,你晓得甚事,好端端田产不要,日后将甚过话,娘做的事也要你埋怨起来!”干浚郊哭了几声,便不插嘴。直等到二更天气,陈与权方才进来,口里说道:“为这些俗事,倒牵缠了这半夜,累大嫂在此等候,着实有罪了。
便摊开帐簿,排下算盘,请丽容当面看了,逐宗逐项,结算明白。好个陈与权,一毫不苟且。丽容满心欢喜,算定了帐,便将花布货物,凭丽容估了价钱,陈与权并不争论。然后,又将银子来兑。成色高低,也凭他折算。刚才兑完,已是四鼓。乔氏忙催丽容去睡,丽容把银子包好,叫丫头拿着,乔氏引他到了卧房。说一声快安置吧,便自去了。丽容见这房内有一副床帐,旁边一张小榻,榻上也有铺盖。丽容与干浚郊上了床,叫丫头就在榻上睡。睡不多时,已是天明。丽容一觉醒来,见窗上微微有光,里头人声嘈杂像个出门的光景。丽容便欲起身,好早些回去。才坐起来,隐隐见地下睡着一个人。因隔着帐子,看不清楚,只认是丫头在榻上跌了下来。及看看榻上,那丫头还的睡着。丽容着疑,一头叫醒儿子,一头穿衣。才提起衣服,早是一阵血臭。连忙看时,可煞作怪,衣上原来都有血迹,尚是湿的。丽容大惊,忙唤丫头起来,自把血污衣服脱下了一层披在身上,走下床来近前一看。不看犹可,看了大吃一惊。原来那人满身满面都是鲜血,僵僵的躺着在地,身边一把尖刀,刀上血迹淋漓。
丽容吓得三魂已失,七魄难收,乃大哭道:“罢了,我中他的计也!”丫头与干浚郊起身看见,都吓得面如土色,干浚郊只抱定了母亲哭道:“昨夜我叫娘回去,娘偏生不肯,如今怎么好?”丽容无言回答。只见有个小丫头走进房来,满房一看,就大喊道:“坏了坏了,干奶奶杀个人在这里。”飞的跑了进去。不多时,陈与权并乔氏,吃惊的都赶出来,把死人一认,乔氏也不说话,先哭个乱横。陈与权乱跳道:“这是我外甥,家中叫他来看我,才到这里两日,为甚么好端端把他杀死。”因指定丽容骂道:“你这贱妇,我家怎生待你,你却记念前恨,把我外甥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