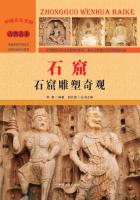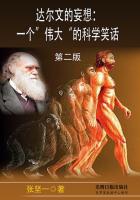真实场景的“戏仿”式呈现
《怪物史莱克》在进行动画片的背景设计时更多地结合了现实生活,体现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将现代美国城市元素杂糅到了动画背景中。整个遥远国都是根据美国好莱坞比弗利山庄设计的,遥远国的标志“Far Far Away”就耸立在与好莱坞(Hollywood)的标志相同的地方。在遥远国的大街上名店林立,其中有模仿星巴克咖啡店(Starbucks)设计而成的Farburks,Versarchery会让人联想到著名时尚品牌范思哲(Versace)。在《怪物史莱克》及其续集中,童话故事发生的背景不再是单纯的中世纪的欧洲,不再是一个完全没有受到现代工业文明污染的理想国。这两部动画片戏仿了经典童话的乌托邦王国,古典童话王国与现代社会的意象交织在一起。而戏仿手法的使用,不仅摧毁了经典童话王国的封闭城堡,也为观影者提供了一个反观现实社会的新颖视角。对迪士尼动画的背景乃至整个经典童话背景的批评、嘲讽、解构和颠覆则寓于对这些意象的描画中,影片制作者将对现代社会的反思融入文化产品的生产中,增加了童话文本的厚度。
《怪物史莱克》中的城市相对于经典童话中的乌托邦来说,不仅更加平等和自由,而且充满了人性关怀,城市中的不尽完美甚至是人物性格的瑕疵,却使其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社会。
(二)城市的符号化重构
《美丽城三重奏》讲述的是一个千里寻亲的故事。从法国的乡村到美国的城市,电影中虽然没有明确告知是哪一座城市,但是从动画片的许多视觉元素中,已经使人很明显地感觉到纽约的气息:摩天大楼林立,商标的体量甚至大过楼房,满街大肥婆的欲望城市里还树立着一个“自由女神”像,手里的火炬变成了冰淇淋。巨大的汉堡、鲜艳的冰淇淋,属于典型的美国“文化”。“美丽城”以纽约为动画片的背景,在重构与杂糅之中彰显了文化的绵延影响力。
重构“纽约”:折射并且戏谑
“纽约”是一个鲜明的价值符号。无论以何种方式,影像中的“纽约”并不少见,它们通常标榜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潮流的前沿以及文化多元化的杂糅地。除了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之外,“纽约”对于电影的意义还在于,它本身无需刻意渲染,便营造了社会意义共识角度上的文化氛围。在动画电影《美丽城三重奏》中的“美丽城”(Belleville)影射的是纽约。作为一部法国动画,《美丽城三重奏》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延续好莱坞电影对“纽约”的狂热追求从而丧失自我,电影以“戏谑”的方式,凝练的符号,个性化的色彩风格,折射出社会变迁中作者对城市的理解。在《美丽城三重奏》中,当夏平的外婆乘船来到“美丽城”时,被重构的“自由女神像”和“好莱坞”显示了动画片的城市背景。纽约被重构的同时,也显示出了一些符号元素,它们是城市文化的一个折射。例如,码头上被重构的自由女神雕像,身体肥硕无比,手里的火炬被改编成冰淇淋。而在遥远的背景处,赫然耸立的山上写着“Hollyfood”,显然是影射好莱坞(Hollywood)。自由女神和好莱坞都是美国向外输出的文化象征,换言之,动画中“美丽都”的生活就是创作者眼中的美国城市的社会缩影。
《美丽城三重奏》中的城市——纽约,浓缩了整个拜物主义世界的符码。肥胖的身体是放纵食欲和懒惰的结果,势利的餐馆服务员向大亨180度大鞠躬,草菅人命的赌场老板为了比赛的刺激而现场杀人,参加赌博的都是物质富有而精神贫乏的矮子,仿佛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克隆体,丧失了个体特征,高雅的艺术已经被“后现代”的现成品撞击声所代替,音乐屈服于商业化的发泄,艺术家被逼到城市的底层,色情交易充斥着低级旅店。这些伴随着机器大工业产生的社会癌症正把整个美丽城变成一个丑恶的地狱,或者甚至可以说,摩登时代和欲望都市都来自于人类的恶趣,根本就无法将两者取一舍一。[6]作为动画背景的纽约超越了动画场景的单一功能,而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城市的特点、功能和典型的文化特质。在《美丽城三重奏》中,作者的意图以及文本呈现出来的影像无一例外地将“美丽城”指向了“纽约”,在美丽城中,一方面的确具备纽约的许多城市信息。通过对城市信息的放大或者夸张,描摹着城市生存的哲学和状态。动画片的角色在扮演虚构人物的同时,荧幕前的受众也在观影的过程中扮演自己。另一方面,“美丽城”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都市的缩影。从动画片的城市背景中同样很容易看到许多国际大都市的痕迹。所以说,在动画片中,“美丽城”约等于“纽约”。动画电影《美丽城三重奏》通过重构城市符号与解构城市元素,塑造出一个虚幻和真实交相辉映的城市,这个城市相对于法国的乡村,拥有工业文明和先进技术,但是同时拥有罪恶和丑闻、贪婪和自私。电影结尾的时候,胜利者永远离开了美丽城,离开了霓虹灯下的纽约,重返乡村也象征着回归自然。当影片结束的时候,夏平和奶奶或许在心中留下了诸多遗憾,抑或是一种无奈的离开,牵挂乡村生活,又难以舍弃霓虹繁华,这种矛盾是城市化过程中大多数人都需要面对的。
寻梦“美丽城”:关于美国的诠释
除了《美丽城三重奏》对于“美国”、对于“纽约”的文化诠释之外,“美国精神”成为了许多动画片直接或者间接表达的主题。在动画片《美国神话》中,同样出现了自由女神像。在空寂的海面上,那尊傲然的自由女神像,在老鼠的视线里显得更为高大。当远渡重洋、经历了艰难险阻、最终见到那尊映衬着夕阳余晖的女神像时,船上的老鼠们激动地欢呼起来,它们将无一例外地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创作者用鼠类的视角,表达了一种普通大众对于“美国”的向往。动画电影中的老鼠们,折射着一群通过移民去寻求“美国梦”的社会群体。记得有首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颇为流行的电影插曲这样唱道:“在老纽约,我的一切将从零开始。如果我能够在这里成功,我就可以走遍天下。全靠你了,纽约!”在一段时期内,纽约是一个寄托着成千上万来自全球每一个角落的移民们的梦想的地方,也常被视为美国梦的象征。动画片用老鼠的视角诠释了一个群体集体性的梦幻,在它们集体寻梦的过程中,“美国”成为它们脑海中的精神地标。
同样,在另一部以老鼠为主人公的动画片《料理鼠王》中,诠释了美国梦的另一重文化寓意。动画电影并没有因为故事场景移至巴黎而削弱对于“美国梦”的表达。动画片以一个老鼠的经历和成长过程,释义了所谓的美国梦,或许就是一种相信只要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致美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成功,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
这种充满了自由气息、充满了想象力的氛围,对于那些身处重重压迫之下的人来说显得那么地具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神话》中的老鼠们历尽艰辛和巨大的代价也要选择远渡重洋移民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料理鼠王》里,雷米要告别老鼠社会,就如《美国神话》里的那些移民漂洋过海来到美利坚的土地上一样,怀着梦想而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说,“这部影片已经超越了一个普通厨师的成长,而成为一个美国梦的典型标本。”雷米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起步,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伟大的厨师,这种梦想如果不是在电影里面,那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只有在这个贫寒出身的林肯可以当总统、高位截瘫的罗斯福可以当总统、身无分文的洛克菲勒可以创下财富神话的国度里才能实现,只有在这个有梦想且能成就梦想的国度才能实现。“这种美国梦一方面打破了旧有等级制度和出身的束缚,给了人以发挥自我才能的巨大空间,另一方面也当然地为美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辩护,告诉世人美国是一个梦想家的乐园,是一个人间天堂。”
(三)世俗思维与都市景观
无数的文学影视作品均以地铁作为背景进行创作呈像,弗朗索瓦·特吕弗拍的《最后一班地铁》,吕克·贝松的《地铁》,张一白的《开往春天的地铁》,还有几米的经典漫画《地下铁》……这种颇具戏剧性的空间类型,有助于演绎各种类型的故事。地铁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邂逅之地,就像戴望舒的《雨巷》,悠长、具有某种封闭性、让人心头一颤的陌生人等种种元素都在地铁里得以呈现,而这种感觉在宽阔的广场和充斥着汽车尾气的快速路上是不会有的,可以说地铁就是一种现代版的雨巷。
地铁:城市文化的象征
在《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中,伊芙特·皮洛把大城市写作“泯灭人个性的地方”,她说,“尽管城市生活千变万化,这里仍有许多刻板的常规:由于各种规章的日益增多,事件和人日益趋向形式化和物化。”由于“大城市使人彼此疏远和隔绝”,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人们选择了保持缄默。“地铁文化”是这个时候闯入现代生活的,人们希望在旅途的短时间内,释放压力,排解空虚,有单纯而明丽的情感,让人可以忽略思考,而只是去享受。
几米的漫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人们的视野的。清新的小品,带着格致的颜色和令人迷幻的笔触,让匆忙之中的人们在拥挤的车厢里,寻找自己生命力的秘密花园。台湾的城市影像也点点滴滴地渗透在作品中,就像在《向左走,向右走》里描绘的城市,“如同没有围墙的囚房,令人疲惫、窒息”;与此“繁复”相对立的是“简单”的定位,有时会“简单到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于是,城市里有了像罗大佑一样的深情迷人;多感而精致的叙事风格,流畅的诗意画图,是几米漫画的主要风格。几米让“图像”成为另一种清新的文学语言,散发出深情迷人的风采。
杜琪峰、韦家辉的《向左走,向右走》和马伟豪的《地下铁》改编自几米的漫画手绘本。而在电影《地下铁》中呈现出来的地铁场景,却拍摄于上海。横跨两岸三地的电影自然带有这些城市的色彩。从影片伊始就带着明显的漫画风格的装饰纹样和高饱和度色彩的《地下铁》,讲述了四个人在都市里迷路又不甘心放弃,时而会疲惫和哀愁的点点滴滴。漫画开始的时候是满目绚烂的水彩透明质感的彩色,配以辛波斯卡诗中的句子:“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电影里把漫画中斑驳的色彩进行了提纯,作为特殊的视觉元素添加在了路面上、墙壁上和楼宇间,加上电影胶片的质感,让“最美的一次邂逅”有了童话般的开始。
拼凑与想象:城市呈像的修辞方法
香港,是一个有地铁的城市;香港,亦是一个有着特殊地域文化的城市,搭乘影片里的地下铁穿梭于城市的隧道之中时,可以找到那个天使,找到那只猫,找到一次次上错车又下错车并见证城市多雨与灰蒙蒙的天空的孩子。
漫画里的盲女孩不断地迷路,总是失去方向,却希望能有一辆“永远不停止行驶的列车”并“隐约寻找心中的光亮”。电影叙事语言某种程度上摒弃了漫无目的和晦涩的部分,使其场景和人物的活动在这个城市里展开,商场、公司、咖啡店、婚姻介绍所和小孩子的金钱观,又不觉中打上了香港文化的烙印。为了影片的生产需要,角色的设置使剧情复杂化,盲女海约和漫画里一样,只是多了几分幽默和不经意间流露的可爱,她不停地寻找心中隐约的光亮,“在跌跌撞撞之后终于明白很多事情是不能强求的”;主人公旭明看得见却又看不见,看不见他身边一些美好的东西,“虽然睁开眼睛,却昏昏欲睡”,他身上有海约的影子;董玲一直流连在地下铁中,等待那个“只给她星星看的人”,就像漫画中的盲女,“等待有人为我撑伞,紧握着我的手,告诉我星星的方向,陪我走一段路”;而钟程是那个在“纷纷扰扰的城市里,寻寻觅觅”的盲女的另一部分。在黑格尔看来,“人不仅具有一个神来形成他的情致,一个真正的人同时具有很多的神,许多神只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包罗在心里。”而在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把性格单一和性格复杂的人分别称之为“扁平人物”和“圆整人物”,漫画中的盲女拥有多种性格,失落寂寞而又充满幻想,知足而又自寻快乐。在电影中,她的这些性格分别赋予了四个人,所以这四个人相似而又不同,因而使影片更适合观赏和放映,人们容易记住每个人的性格,从而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去寻找每个人“心中的地下铁”——“sound of colors”原本的美丽和优雅让行文如同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