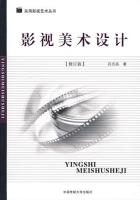(三)爱情情节的渲染烘托
与原文学作品“牺牲女性生命丰富性,把女性抽象为空洞的符码”相比,动画作品《花木兰》更加注重女性日常人生的描绘。动画片增加了爱情的噱头,虽然好莱坞常将爱情作为卖点,但是仍然是一种女性主义精神的体现,最终,这个有着传奇色彩的女孩不但成为国家英雄,同样赢得了爱情和整个家族的尊重。这应该是一个女性,甚至是所有的人最完美的结局,这个女孩做到了,她赢得了爱情和整个世界。迪士尼以适度的女性主义和中国传奇糅合在一起,迎合全球口味,创造了好莱坞东方题材的成功范本,一方面取得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另一方面使迪士尼动画的女性形象丰满起来,女性主义诠释成熟起来。
对于动画电影《花木兰》来说,影片中,画面如中国山水画般柔美,音乐颇有中国风味,是一部标榜女性主义的真正佳作,只可惜这个有着中国外壳的女子却浑身洋溢着美国精神。不得不指出的是,原作在女性主义上是一个文化的断代层,一方面,女性形象与男子主义不得兼容,在木兰佯装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没有体现出一点女性品格和女性特征;另一方面,木兰在“可汗大点兵”之前是一个“织女”的角色,“脱掉战时袍”之后仍将回归原来的家庭角色,仍然无法逃离古代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
三、改编中的多义性与模糊性
动画片《花木兰》最初来源于中国的民间传说,因为原文本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从而为动画片对原著的改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花木兰的故事有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和北朝的乐府诗《木兰辞》等诸多来源。关于她的真正姓氏和家乡所在地都存在着诸种争论,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木兰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类似于女英雄的角色——虽然木兰可能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是在古代中国的现实中,必定出现过类似她那样的女英雄,而木兰则集中反映了她们的特质,象征着对她们的业绩的一种文学或文化上的承认。正是因为文本的不确定性,才使“木兰从军”的故事有更大的创作余地。关于木兰的民间传说很不完整,其故事的情节性也较弱,木兰的姓氏和传说发生的具体地点和时间也不是十分具体,这些空白点某种程度上为动画艺术家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故事正是在中国的古代展开,有长城,有烽火,中国的风貌被展示成为一幅悠远的风景画。“在开满深红色杜鹃花的树下,坐着促膝谈心的花家父女。父亲指着空中的一枝花,告诉正为相亲失败而苦恼不已的木兰,那最晚开放的花,或许才是最美的。”《花木兰》角色创作者张振益在面对记者采访时说:这样恬静的场景是原著中不曾提及的,迪士尼动画因为文本的模糊性,更好地利用了文本并融入现代的元素,提供了新的阐释,塑造了一个追寻自我价值的现代女孩。
正如美国影评家兼诗人米切尔·埃利卡·格林所说的,《花木兰》“是一部可以和孩子们,尤其是需要榜样的女孩子们一起看的伟大的电影”。她称《花木兰》是“迪士尼影片中最好的一部”,木兰的力量“不在于她女扮男装所取得的成就,更在于她作为女性在一个认为妇女应当美丽、沉默、安静的世界所做出的业绩”。她说,“《小美人鱼》中的爱丽儿想通过改变她的身体赢得王子,《美女与野兽》则认为暴虐的男人所真正需要的无非是一个好女人的爱来驯服他,在看过这些影片之后,只有《花木兰》的力量真正感动了我。”学者尹鸿表示,女人都是两面性的,比如我们说“女强人”,那她可能缺乏必要的宽容、柔弱、善良;另外一方面,过分柔弱、善良的女人,在动画《花木兰》中,有女性柔美的一面,有足够的叛逆和独立,还有智慧和自我价值的追寻,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实属难得。
用女性主义的批评视角去重新审视动画,对男权中心意识下的电视进行分析和解剖,建设性地批判那些电视当中的男权意识,从一种更有穿透力的视角提出一些我们以前视而不见的问题,指出人们习焉不察的传统男权观念,提出比要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更深层次的问题,会使我们对许多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新的观察和思考。这样,更有助于人们去注意和理解动画中那些与妇女现实生活和地位有关的问题及其根源和复杂性,也有助于动画暗示和影响女性受众在自我认知、自我解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些。
第四节 女性品格缺失的文化思索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动画中的女性形象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仍是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掩盖两性世界的不平等关系的角色,或是处在被忽略的位置,性别特征无法得到体现。因此,女性主义认识到要想在动画作品中彰显女性的独立和自强,并不能寄托于社会“女士第一”的绅士精神,而应来自民族女性主义深层意识的彻底觉醒和成熟,来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成熟。目前,女性品格的缺失归结起来症结有三:
一、沿袭封建意识,动画改编无法走出原著意识形态的桎梏
中国的大型动画多改自经典名著。改编自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的就有许多: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片《铁扇公主》;52集电视动画片《西游记》、《哪吒传奇》;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金猴降妖》;香港动画电影《红孩儿大话火焰山》等。还有改编自著名神话《封神演义》的电视动画片《封神榜》,改编自明代小说《平妖传》的动画电影《天书奇谭》等。这些名著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等种种原因,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的阶级意识。
例如,电视动画片《西游记》中,孙悟空是没有“母亲”的孩子,这与剪纸动画片《葫芦兄弟》如出一辙。葫芦兄弟是从七个葫芦中跳出来的,如果说葫芦兄弟的表象来源的话,那便是精耕细作、爱葫芦如(孙)子的老汉了,一个中国普通的农民形象——男性角色。对于“母亲”形象,柯云路在对文学名著《西游记》的分析中说道:“她是维护父亲权威的,是贯彻父亲意旨的,同时又是怜惜儿子的。她的目的就是将儿子引上父亲规定的道路。一方面,对于儿子所受的责罚,作为母亲,她知道这是维护父亲权威所必要的,是维护整个秩序所必要的,也是儿子未来人生所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不破坏父亲权威的前提下,在坚定不移地引导儿子走上正确人生道路的前提下,她又流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温情。”[7]诚然,动画并没有跳出原著对于女性形象忽略的藩篱。
在文学著作《西游记》中,但凡美丽的女性形象都是以女妖出现的。原著《西游记》一共出现了十一个女妖,其中以“狐狸”为原型的就有三个:玉面狐狸、九尾狐狸和白面狐狸。一方面,这说明男权社会中已经将“狐狸精”作为恶女人的符号了。猪八戒有一句名言:“粗柳的簸箕细柳的斗,世上那见男儿丑?”这与妖精化作的美女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性的存在是以美丽的外表为依托的。另一方面,在这些女妖身上有许多“可贵的品质”,例如,他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已经全然走出了她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系统。她们已经抛开了“父母之命”而改为主动追求终生幸福了。可惜的是,这样超前的、积极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行为却全部赋予在女妖精的身上。反面角色的某些宝贵的行为品质却不被观者所认可了。当然,原著的影响是大部分的症结所在,原著的写作背景决定了文学名著《西游记》维护封建统治的阶级立场,但是动画片并没有呈现出独立的女性意识,在某些方面延续了文学作品中的男权主体意识,在作品中,女性人物基本处在边缘和陪衬的地位,作为特殊群体的秀美女妖精主动追求的行为模式,却是为了突出妖精的邪恶来衬托取经人的虔诚的,所以,女妖精往往是“祸水”的代名词,其结局当然是化为原形被天神收走。在动画对原著进行改编时,并没有剔除原著的封建思想和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动画继承原著,将邪恶的动物画作美丽的女子,这些美艳的外表掩盖了内心的邪恶,无形中强化了女性在审美活动中的被观赏和从属地位,于是人们在潜意识的心底,在男性之镜中照出男人需求的种种女人形象,是巫,是妖,女性虽然无处不在,但并未能够得到真实的映像。
二、动画片题材选择的局限致使女性形象缺席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动画片诞生于1926年,在对中国自1926至2006年的近千部动画片(包括电视动画和影院动画)以及迪士尼1937至2005年的40几部影院动画长片进行角色研读和主题探讨后,那么完全可以用数字来说明中国动画中女性形象的缺席。
(一)国产动画存在低幼化现象,以人物为主角的动画本来就为数不多
国产动画的低龄化现象已经不是热点,在我国,动画片一度被认为是“孩子们的专属”,我国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赋予了动画片以说教和政治形态宣传的功能,这种教育主义、工具论的观念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并且造成动画理论一直未被纳入主流电影理论领域进行研究,而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低幼化”主要表现在故事情节和结构上,另外就是表现在动画形象上。形象的选择大多数以动物为主,以人物为主角的动画相对来说较少,女性角色就更不用说了。
相比之下,迪士尼以及其他动画制作机构将作品定位突破“少年儿童”的局限,把动画当作一种艺术表现的手法,而不是孩子们的专利。例如动画电影《狮子王》就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名著《哈姆雷特》,影片用动物形象替换了原作中的人物形象,呈现出非常复杂和成熟的故事以及性格鲜明的角色。东欧的许多实验动画更是如此,黑色幽默借助动物来诠释早已成为一种手法,用以表达创作者的温情的微讽和对人生百味的理解。在类似的动画作品中,女性形象并不缺少,女性品格也更多地被保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