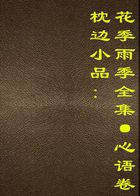一、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时事情结”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普遍存在的警世心态、救世心态、劝世心态、愤世心态和隐世心态,汇总融合,化而为一,可称为是一种“时事情结”。所谓时事情结,是指在明清之际小说各个流派的作品中,都表现出一定的关注时事的心理心态。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时事情结”的形成,源于他们所遭受的两大集体创伤体验——魏阉暴政和大明王朝的覆亡。
在文学创作心理学领域,“体验”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经验是作家生平所经历事情的总结,而体验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是以主体在认识过程和心理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内容为对象的,是对经验的带有情感色彩的回味、反刍和省悟。体验是比经验更加深刻、强烈、活跃、生动的心理活动。
魏阉暴政对当时士人的心灵打击很大。魏忠贤结交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内外弄权,在内敢于逼死皇帝的妃子,在外任意残害论劾他们的朝廷命官,天启三年,魏忠贤、客氏逼死裕妃、成妃。天启五年,加害左光斗、杨涟、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等人。天启六年,迫害缪昌期、李应升、周顺昌、周起元等人。且手段之残忍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明史》中这样记载魏忠贤的淫威:“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侧目。”魏阉集团爪牙的奏章上称魏忠贤为“千岁”、“九千岁”,魏忠贤的“生祠”遍布各地,有明一代作恶多端的宦官王振、刘谨等人,都不曾达到这样的程度。一宫奴太监和一保姆联手,而能作恶深重,贻害天下,视官吏大臣之命如草芥,对此,士人心灵受到的压迫是深重的。
历代政治黑暗时期,士人都要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的愤懑之情。在明清之际,诗词曲赋,似已不足以表达士人的愤懑情绪,他们便借助明朝以来兴盛的小说的创作,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崇祯元年,魏忠贤虽然已死,但魏阉势力尚未被完全肃清。而此时,迫不及待的小说作家已纷纷倾泻久蕴胸中的对魏忠贤的愤恨之情,于是描写魏忠贤恶行和可耻下场的小说《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皇明中兴圣烈传》相继刊行。
魏阉暴政被推翻了,但威胁明朝存亡的危机并未结束。辽东边患持续,内地天灾人祸,流民起义,并且势力越来越大,终于使大明三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致使大明王朝覆灭的两大直接因素,是流民义军和清朝军队,而堂堂大明王朝竟然毁于“奸民”和“夷狄”之手,这是广大汉族士人心灵所不能容忍、不能承受的。在他们看来,流民义军以下犯上,杀戮大臣,逼死君父,是大逆不道;满清王朝以夷制夏,剃发圈地,践踏文明,对于大明士人来说,更是奇耻大辱。
流民义军不久又败亡于满清王朝之手,小说作家敢于通过小说创作直接表达他们对流民义军的愤恨。如《新编剿闯小说》、《铁冠图》、《樵史通俗演义》,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创作的。而对入主中原的满清王朝的愤恨之情,却因新政权得以确立、畏惧遭到新的统治者的残酷迫害而被压抑起来,只能通过曲折隐晦的方式表加以达。如陈忱的《水浒后传》借李俊等人建立的海上王国,描写光复故国的理想;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借古讽今,谴责清朝统治者的血腥罪行;连放浪形骸的李渔,也常常在作品中透露出追悼故国的哀伤之情,如在他的戏曲《巧团圆》上场诗中写道:
出钱买父司家产,这样新闻天下罕。
世事如今都改常,如何不教流贼反。
在剧中,他又借剧中人物王四之口说:
种种新闻,都是不祥之兆,明朝的天下,决失无疑了!
在下场诗中又写道:
莫怪人心诧异,只因世局缤纷。
儿子既可买父,臣子合当卖君。
由儿子买父这样一个社会新闻,联想到明朝是否应当灭亡这样重大的政治命题,说明明朝灭亡这一事件在李渔心中形成的巨大阴影。每一个从明入清的士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追问、要反思明亡的原因。“灵霄殿”为什么会“光油油儿从天缝中滚下来”?董说《西游补》第三回写孙悟空“看见四五百人持斧操斤,抡刀振臂,都在那里凿天”,这些人 “刚刚凿开灵霄殿底,把一个灵霄殿光油油儿从天缝中滚下来。”在李渔看来,都只为明末封建纲常伦理已失去了控制人心的力量,才会发生儿子买父、臣子卖君这样稀世罕见的新闻。“世事如今都改常”,这句话饱含着李渔对明清之际纷纭时事的深沉感叹。
这两大创伤体验三大刺激来源,对读书人心灵的打击是持久而深重的。以至于他们纷纷发出“天崩地裂”、“乾坤覆亡”的感叹。其中魏阉集团和流民义军两种刺激力量,在崇祯和顺治初期渐渐消释。而对满清王朝入主中原这一刺激来源,却因遭到压抑,而在人们心中顽固地持续着。在满清王朝统治中原的260多年中(1644~1912),反清斗争从没有断绝。对满清王朝的反对者来说,“反清复明”是一种最富于号召力的口号。康熙十二年(1673),杨起隆自称是崇祯皇帝的儿子朱三太子,在北京城内密谋起义,失败后逃往陕西,康熙十九年(1680)被捕,不屈而死。康熙十二年清廷主张“撤藩”,激起吴三桂、耿精忠等“三藩”叛乱,他们打的也是反清复明的旗号。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起义,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水教徒王伦在山东寿张起义,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徒刘之协等人发动川、陕、楚三省教民大起义,咸丰元年(1851)发生洪秀全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些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无不标榜他们的起义是为“反清复明”,这说明反清复明的思想是多么深入当时广大汉族民众的心灵。
二、明清之际小说作家的群体体验
文学创作心理学认为,体验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早先的和后来的各种体验总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对作家心态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八种体验——童年体验、崇高体验、缺失性体验、丰富性体验、愧疚体验、神秘体验、孤独体验和归依体验。这些体验形式,在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心态生成过程中,几乎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童年体验
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在童年(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经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童年体验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形成影响颇大。
中国古代文人的童年体验可能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在发蒙时期接受私塾的教育方式。私塾在教给小孩子识文断字的同时,还用四书五经的内容灌输给他们忠孝节义的儒家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也不例外,他们的警世、救世、劝世心态,都与接受正统儒家教育的童年体验有关。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各自具体的童年体验,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但他们大都富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希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当命运不济无法实现他们的雄伟抱负时,又大都期望能够通过创作小说,有补世道人心。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心理前提,是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国家和民族的一分子,同时对国家和民族具有一种“我的”认同感。这种心理正是作家自我扩展的表现。
2.崇高体验
崇高体验,是作家经由自然或社会的某种外在刺激所唤醒的压抑在内心的带有痛楚和狂喜成分的激情体验。这种情感潮流,常常会自觉地变成作家的内驱力,强迫他以呐喊、吁求的形式,或以实际的行动进入生活,投入创作。崇高体验是作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由衷而诚挚的高尚情感体验,大都是作家遭受心理挫折时的异常体验,有时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献身精神。作家崇高体验的表达,主要通过成就动机的萌生与达成来实现。成就动机是人在强烈的企图发挥自我优势能力的欲望支配下,希望倾其一生去从事对个人未必有益、对社会可能有重大意义的活动,并尽力取得惊世骇俗的成果的动机。作家从崇高体验中萌生成就动机,总是由社会或自然给以种种难以忍受的刺激开始的。
明清之际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天灾人祸的黑暗现实,激发了一些作家的成就动机,促使他们采取小说创作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崇高体验。
崇祯元年(1628),吴越草莽臣在《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中,流露出他因崇高体验而萌生的创作动机。冯梦龙曾取“草莽臣”为号,萧相恺先生认为吴越草莽臣是陆云龙。他说:
予少秉赋劲骨,棱棱不受折抑,更有肠若火,一郁勃,殊不可以火沃。故每览古今事,遇忠孝困于谗,辄淫淫泪落,有只字片语,必志之以存其人;至奸雄得志,又不禁短发支髿立也。本段及以下四段引文均出自《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正因为他素有这样一种疾恶如仇的崇高体验,在甲子年(天启四年,1624),偶然读到邸报上有一篇杨大洪先生弹劾魏忠贤的疏,引发了他的万千感慨。他由此联想到杨大洪因此疏而落入魏阉党羽的魔爪与左光斗等人同时遇难的事件,痛感魏阉乱政之时:
太阿倒持,元首虚拥,徒扼腕于奸之成,而国事几莫可为。
但当时魏阉集团气势熏天,吴越草莽臣尚不敢有所作为。崇祯皇帝即位之初,立即摧毁魏阉集团,他以为:
若禹鼎成而妖魑形见,雷霆一震,荡然若粉齑,而当日之奸皆为虚设。
吴越草莽臣在欢欣鼓舞之余,又为自己身在草莽,无法为铲除奸佞出力而深感遗憾。他说:
越在草莽,不胜欣快,终以在草莽,不获出一言暴其奸,良有隐恨。
虽然他宽慰自己说:“大奸既拔,又何必斥之自我。”然而,心中的“隐恨”还是促使他要为“斥奸”做些事情。怎么做呢?他说:
唯次其奸状,传之海隅,以易称功颂德者之口;更次其奸之负辜,以著我圣天子英明,神于除奸;诸臣工之忠鲠,勇于击奸。俾奸谀之徒缩舌,知奸之不可为。则犹之持一疏而叩阙下也。是则予立言之意。
吴越草莽臣选择创作小说,通过描述魏忠贤的奸佞情状,使四海之人都明白魏忠贤的奸恶,封住那些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之口;称颂崇祯皇帝处置魏忠贤的圣明决策,表彰诸位忠直大臣;警戒奸谀之徒,让他们知道作恶必没有好下场。这样一来,吴越草莽臣感觉自己好像仿效了杨大洪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做法,自己的一片忠勇之心终于得以表达。
吴越草莽臣非常痛恨魏忠贤的恶行,非常敬佩杨大洪等忠臣义士反抗魏忠贤的壮举,难以忍受自己没有为铲除魏忠贤作出贡献,于是便以写作《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来表达自己的心志,补偿心中的“隐恨”。他的“斥奸”、“警世”心态,来源于自身受到压抑的崇高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