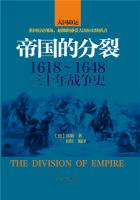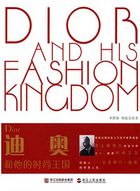董说出家之后的情况怎样呢?他所追随的法师是“以忠孝作佛事”的南岳和尚,他侧身其中的灵岩四大弟子均是遗民色彩浓厚的儒僧。明清之际很多文士“逃禅”,大都出于不得已,并非真心皈依,如归庄等。归庄自谓“虽作头陀不解禅”。董说虽是解禅的头陀,却也同样是遗民色彩浓厚的儒僧。
光绪《乌程县志》卷十六记载云游四方的南潜和尚(董说)会见明遗民黄周星时的情景:“曰:‘此古之伤心人也。’展《桑海遗民录》,黯然而别。”
但最终他还是一个不彻底的佛教徒。严可均在其《吕海山画董若雨树霜苕帚遗像》诗中说:“风景河山劫后灰,小庵丰草破书堆。只应净扫兴亡恨,安稳蒲团入定来。”说“只应”,当是生前并未“净扫兴亡恨”,并未“安稳蒲团入定来”。
董说遗民和僧人的双重身份,已经引起前人的注意。钱某人《读〈西游补〉杂记》说:“若雨令妻贤子,处境丰腴,一旦弃家修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彻者,不仅以遗民自命也。”“不仅以遗民自命也”,前提是“以遗民自命”。不仅以遗民自命,也不仅以僧人自处。
《西游补》第五十九回中所说“戴巾的长老”,应当是明清之际遗民常态。头巾气,儒生气,欲超脱而未能超脱;僧不僧,俗不俗。
作者具有遗民和僧人的双重身份,其小说作品相应也具有遗民和僧人的双重身份。《西游补》正是如此:不但悼念明亡,还苦思原因。《西游补》中对于明亡原因的追究,虽然不如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那样具有系统深刻的理论性质,其思考确也比较深入,触及到了政体本身。
三、主旨新议
对宗法政治的思考是文人小说的特征之一。一般通俗小说往往不能上升到此高度。明清之际之前的文人小说(即浦安迪所谓的明代四大“奇书”),都体现出作者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入反思。四大“奇书”对宗法政治、伦理道德、人的本质都有严肃的理性的思考。其中《三国演义》思考政权归属问题;《水浒传》叹息政权与行政职能的矛盾;此二书又都对“忠义”思想隐隐提出质疑和反讽;《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都比较尖锐地指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人的价值究竟何在等问题。明清之际文人小说是这些思考的延续,最典型的是《豆棚闲话》借对历史故事的颠覆与反思,在嬉笑怒骂中闪现自己的独特见解。
至于《西游补》中的理性思考,学者多有注意并有较高评价。有人认为,“董说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整体性的透视,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比以往任何小说都更全面,更深刻”,大致所言不虚。《西游补》虽不见得在此方面超越以往任何小说,但的确全面深刻地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整体性的透视。
贯穿《西游补》第二层面的主线是亡国引发的对政体的严肃、理性、深刻的思考。在中国古代社会,“天”不但与自然相关联,还往往与宗法政治有密切的联系。宗法政治的代表人物、极权人物——帝王就号称“天子”,中国古代“天下”、“皇帝”总是与政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西游补》一开始就把小说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天”被破坏、欲补“天”而无望、郁闷问“天”、追究“天”破原因的象征高度。
《西游补》究竟有无亡国之恨?这个问题由于《西游补》写作风格的空灵剔透而变得更加复杂。其中问天一篇、凿天一篇、审秦一篇,可看做轻松幽默之笔,可发一笑;也可看做饱蘸血泪之笔,于调侃的笔墨中深寓沉痛巨哀。
在这个意义上,第二回《西方路幻出新唐绿玉殿风华天子》最值得注意。第一回《牡丹红鲭鱼吐气送冤文大圣留连》其实是一篇小说的缘起,通过花红心红的迷境点出行者入梦的原由,第二回才是一部小说正文的真正开始。作者在第二回一开始就把关注的焦点指向“簇簇新新的天下”、“新皇帝”、被偷的“灵霄殿”。
此回写道:
行者又不觉失声嚷道:“假,假,假,假,假!他既是慕中国,只该竟写中国,如何却写大唐?况我师父常常说大唐皇帝是簇簇新新的天下,他却如何便晓得了,就在这里改标易帜?决不是真的。”躇踌半日,更无一定之见。
行者定睛决志把下面看来,又见“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十四字。他便跳跳嚷嚷,在空中骂道:“乱言,乱言!师父出大唐境界,到今日也不上二十年,他那里难道就过了几百年?师父又是肉胎血体,纵是出入神仙洞,往来蓬岛天,也与常人一般过日,为何差了许多?决是假的。”
他又想一想道:“也未可知,若是一月一个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八个都换到了。或者是真的?”
“簇簇新新的天下”,“一月一个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八个都换到了”,联系清廷初立、南明频繁更换皇帝的写作背景事实,不免令人生疑。调侃也好,愤慨也好,总之有着浓郁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作为一介文人,作者无力回天,只有在笔底倾泻郁闷而已。
第五回写行者被冤枉是偷天贼,自思“闻得女娲久惯补天,我今日竟央女娲替我补好,方才哭上灵霄,洗个明白”。及至“走近门边细细观看,只见两扇黑漆门紧闭,门上贴一纸头,写着:二十日到轩辕家闲话,十日乃归。有慢尊客,先此布罪。”连“久惯补天”的女娲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天地改换的境况真正是无可挽回。
此回又写:
行者又叫功曹:“兄弟们何在?”望空叫了数百声,绝无影响。行者大怒,登时现出大闹天宫身子,把棒晃一晃像缸口粗,又纵身跳起空中,乱舞乱跳。跳了半日,也无半个神明答应。
此段文字令人想到闯王攻破北京城之时,崇祯呼百官而不见人来,手下无人乃至煤山自殉的情状。再往下看:
行者越发恼怒,直头奔上灵霄,要见玉帝,问他明白。却才上天,只见天门紧闭。行者叫:“开门,开门!”有一人在天里答应道:“这样不知缓急奴才!吾家灵霄殿已被人偷去,无天可上。”
“吾家灵霄殿已被人偷去,无天可上”。当非虚笔。其后又写一个手拿一柄青竹帚的宫人的自言自语:
呵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做“眠仙阁”哩!……
只是我想将起来,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做风流天子的也不少;到如今,宫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
不要论秦汉六朝,便是我先天子,中年好寻快活,造起珠雨楼台;那个楼台真造得齐齐整整,上面都是白玉板格子,四边青琐吊窗;北边一个圆霜洞,望见海日出没。下面踏脚板还是金镶紫香檀。一时翠面芙蓉,粉肌梅片,蝉衫麟带,蜀管吴丝,见者无不目艳,闻者无不心动。
昨日正宫娘娘叫我往东花园扫地。我在短墙望望,只见一座珠雨楼台,一望荒草,再望云烟;鸳鸯瓦三千片,如今弄成千千片,走龙梁,飞虫栋,十字样架起。
更有一件好笑:日头儿还有半天,井里头,松树边,更移出几灯鬼火;仔细观看,到底不见一个歌童,到底不见一个舞女,只有三两只杜鹃儿在那里一声高,一声低,不绝的啼春雨。
这等看将起来,天子庶人,同归无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尘!
此段令人荡气回肠的文字,读来有似曾相识之感。其意蕴情感与脍炙人口的清初传奇《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中《哀江南》曲极为相似。《桃花扇》中苏昆生在《哀江南》中《离亭宴带歇拍煞》一曲唱道: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辛巳本该回评语云:“中间珠雨楼一段,是托出一部大旨。”“一部大旨”是什么?将此一段与《哀江南》同看,可以清楚得见遗民的相同心迹——感叹兴废。只是《哀江南》感叹的是五十年的兴亡,珠雨楼的兴亡因《骊山图》而与“那用驱山铎的秦始皇帝坟墓”联系起来,逆推至两千年的历史,从而具有了超越明清兴废的普遍意义。这也是《西游补》高出《桃花扇》之处。《桃花扇》止于感叹明清之际的易代兴亡,《西游补》则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更为深刻的思考。尽管他的思考带有强烈的感性色彩,与同时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家黄宗羲等人的理性论述不能同日而语,但毕竟拓展了小说内涵的深度和广度。
第四回在“天字第一号”放榜情状那一段著名的讽刺科举的文字之后,作者进一步借行者之口从理论上批判现行的科考制度对文章和文化的荼毒:
孙行者呵呵大笑道:
“老孙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炉中,听得老君对玉史仙人说着:‘文章气数:尧、舜到孔子是‘纯天运’,谓之‘大盛’;孟子到李斯是‘纯地运’,谓之‘中盛’;此后五百年该是‘水雷运’,文章气短而身长,谓之‘小衰’;又八百年,轮到‘山水运’上,便坏了,便坏了!’
当时玉史仙人便问:‘如何大坏?’
老君道:‘哀哉!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做的文字,更有蹊跷:混沌死过几万年还放他不过;尧、舜安坐在黄庭内,也要牵来!呼吸是清虚之物,不去养他,却去惹他;精神是一身之宝,不去静他,却去动他!你道这个文章叫做什么?原来叫做‘纱帽文章’!会做几句,便是那人福运,便有人抬举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
当时老君说罢,只见玉史仙人含泪而去。”
正是这段文字,被傅世怡认为描写放榜诸生患得患失之状“曲尽人情,人之七情见焉,未离本书大旨”,但随后的抄白第一名文字以及老君论文章气数,“极讽刺之能事,作者鄙科第如土苴,弃功名如敝屣,情溢乎辞,暂离题旨,殊不可取”。其实,这段文字正是《西游补》作为文人小说的理性深度所在。不但与自己生活和感受结合,寓有不第秀才的激愤心态,还有着对当世科举制度的理性批判,对文化命运的深沉忧虑。
第三回《桃花钺诏颁玄奘凿天斧惊动心猿》中有一篇“问天”文字。行者“见四五百人持斧操斤,轮刀振臂,都在那里凿天”,生疑自思:
他又不是值日功曹,面貌又不是恶曜凶星,明明是下界平人,如何却在这要干这样勾当?若是妖精变化感人,看他面上又无恶气。
思想起来,又不知是天生痒疥,要人搔背呢?不知是天生多骨,请个外科先生在此刮洗哩?
不知是嫌天旧了,凿去旧天,要换新天;还是天生帷障,凿去假天,要见真天?
不知是天河壅涨,在此下泻呢?不知是重修灵霄殿,今日是黄道吉日,在此动工哩?
不知还是天喜风流,教人千雕万刻,凿成锦绣画图?不知是玉帝思凡,凿成一条御路,要常常下来?
不知天血是红的,是白的?不知天皮是一层的,两层的?
不知凿开天胸,见天有心,天无心呢?不知天心是偏的,是正的呢?
不知是嫩天,是老天呢?不知是雄天,是雌天呢?
不知是要凿成倒挂天山,赛过地山哩?不知是凿开天口,吞尽阎浮世界哩?
就是这等,也不是下界平人有此力量;待我上前问问,便知明白。
这篇文字简直就是一部《天问》。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董说“问天”与屈原“天问”的关系。丁国强认为董说与屈原“问天”的原因相同——报国无门,回天无力,只有去“问天”;二者含义相近——屈原“天问”是“诗人在历经磨难、国家复兴无望的情况下,对君主制提出的疑问”,“董说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整体的透视,答案是无药可救”;只是“问天”后的归宿不同:一个自杀,一个禅隐。他认为“忧国忧民的屈原死得悲壮激烈,同样忧国忧民的董说走得恬静安详”。
其实不然。自杀是痛苦彻底的了结;禅隐则是难忘世间苦痛的不彻底的禅隐。屈原在《离骚》中的第三次飞天其实是可以成功的,却因回顾故乡关怀故土而无法自求解脱:“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后世的苏轼等文人都难以舍弃现世关怀而入佛入道自求解脱,自幼儒家文化“修齐治平”的熏陶使他们无法在苦难的现实中作一个身心无碍的“自了汉”。董说也是如此一个文人,《西游补》中体现的也是如此一颗文心。
后来的文人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都表现出成熟而理性的文化批判意识、社会承当精神、悲剧意识。《西游补》则用幻笔和诗笔,展示了心灵与梦境变幻多姿的美,并对现实存在进行批判与反讽,流露出独特的个性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