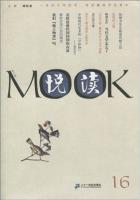李渔与当时名士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从《李渔全集》中可以看到许多他与如龚鼎孳、尤侗、余怀以及“西泠十子”(清初杭州诗人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孙治、张丹、吴百朋、沈谦、虞黄昊、陈廷会的并称)等的酬酢书信和唱答诗篇,如《端阳前五日尤展成、余澹心、余澹仙诸子集故苏寓中观小鬟演剧,澹心首倡八绝,依韵和之》诗和《与龚之麓大宗伯》文等。顺治十七年(1660)李渔纂辑《尺牍初征》,请吴伟业为之作序。当年又在西湖与丁耀亢等人交游。为李渔《十二楼》作序的杜浚也是当时名士,杜浚与余怀、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袁于令入清后与杜浚、褚人获、洪升等人关系密切。
丁耀亢顺治五年(1648)在北京居于陆舫时,也与龚鼎孳、张坦公、王铎、傅掌雷、刘正宗、贾凫西等人交往密切,其诗集《陆舫诗草》中,多处录有与他们的唱和之作,如《张大理玉调张尚书坦公载酒同过草堂二首》、《秋日答贾凫西候补思归》、《次王觉斯大宗伯游华山八律》等。顺治十七年(1660)丁耀亢赴任途中路过杭州,与杜浚、李渔等人徜徉西湖之畔,逗留月余。
与名士的交往,不但可以提高作家的艺术修养,为他们的小说创作提供无形的熏陶,还往往会直接促进他们的小说创作。譬如前面提到过的丁耀亢创作《续金瓶梅》,很可能最早起因于在董其昌处接触过《金瓶梅》。
小说作家与官员的交往也颇引人注目。有的作家与官员交往,是因这些官员本身就是名士,而有些作家与官员交往则是为了谋生。一般说来,小说作家交往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名士,有些作家本身既是官员,也是名士,是相同的志趣将他们吸引到一起来的。纯粹为了谋生而有意与官员交往、迹近“打抽丰”的小说作家,比较罕见,似乎只有晚年的李渔一人而已。李渔于顺治十五年(1658)着手编辑名为《尺牍初征》的名人书信集,其中一部分作品选自古人的书信,而另一部分则由李渔发函给全国各地的官僚名流,向他们广泛征集其作。李渔在《征尺牍启》中说:“三十年间,兵燹以来,金石鸿编,遗弃殆尽,而况名贤手迹耶!仆广为搜猎,淹久岁月,仅有是编,颜曰初征。”通过这个搜集“名贤手迹”的方式,他得以认识不少官员,为他下一步“游走江湖”、四处“托钵”的生活打下了良好的人际基础。
丁耀亢顺治五年(1648)游走京师,也是为了谋生,即所谓为“升斗计”。正是由于他在北京交往广泛,得到官员的有力帮助,才可能有后来拔贡和做官的仕途生涯。他于顺治十六年(1659)乘赴惠安知县任之机,于当年十月起身,途经扬州、瓜州、常州、无锡、苏州,年底到杭州,第二年才入闽。
小说作家与僧人多有交往,这似乎是明清之际的一个特殊现象。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易代之际隐入寺庙出家为僧的名士非常之多,如明朝宗室朱耷、名士方以智等;再是乾坤倒覆、江山易主的变故,对士人心灵的打击很大,为追求解脱,自然会频繁与标榜“四大皆空”的僧人交往。中国古代文化中,佛教思想是儒、释、道三教之一,深入到多数读书人的心灵深处。这是他们与僧人交往的前提。那些在别号中标明为“居士”的作家,可能都具有一定的宗教思想。而董说、丁耀亢等,则最终侧身僧人之流。
董说与僧人交往密切,可以说深受他的父亲董斯张的影响。董斯张十岁时目睹家族由盛转衰,心灵中一直有师从佛教追求解脱的念头。据董说自述,他在很小时就常常跟随父亲去寺庙。董说《楝花矶随笔》记:“六七岁时,每新春及重九,借庵先生必命遍礼溪上诸院。”他还从小诵读佛经。他的《丰草庵诗集》卷一中有诗云:“记得竹床残暑后,枇杷树下教《心经》。”董说八岁即皈依开元寺闻谷大师,被赐名为“智龄”。如前所述,甲申之变后,董说与苏州灵岩寺南岳大师过从甚密。以后几年中,董说眼见南明政权节节败退,反清复明的事业越来越无望,他就常常到灵岩寺参谒夫山和尚,最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在夫山大师门下剃度为僧。
丁耀亢与僧人的交往虽然未见直接资料,但从《续金瓶梅》中可以看出,他一贯具有颇为浓厚的宗教思想。在顺治十七年(1660)遭遇了因《续金瓶梅》而入狱的打击,以及相继而来的双目失明的厄运之后,他终于弃绝尘世,撒手出家。
第三节小说作家之间的交往
小说作家之间的关系,是从作家与师友、与书商的关系中抽离出来的。有的小说作家之间的交往,本来就是师友关系或书商与作者的关系。但对小说创作来说,作家之间的交往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可能在交往中互相切磋创作经验,这种交往直接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和内容。譬如吴山谐野道人在《照世杯序》中,谈到酌元亭主人“过西子湖头,与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纵谈今古,各出其著述,无非忧悯世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三人对小说创作诸种问题形成一致的看法:“且小说者,史之余也。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贻身后辱。’是则酌元亭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即紫阳道人、睡乡祭酒之素心焉耳!”他们的交往对彼此的创作影响都很大。《照世杯》和《续金瓶梅》的创作主旨都是“忧悯世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都明显表现出作家劝诫世人的创作心态。
由于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在杭州、苏州、南京一带活动,又都与书商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他们彼此之间应当比较容易发生交往。据目前可知的材料,大致可以梳理出一个松散的小说作家团体,这个团体以杭州为主要活动中心。
以冯梦龙以中心,可以串起两个小说作家交往链环。第一个交往链环包括冯梦龙、袁于令、杜浚、李渔、丁耀亢、酌元亭主人等人。在叙述小说作家的贫困生活时,我们曾举杨恩寿《词馀丛话》中所记冯梦龙为袁于令修改《西楼记》的轶事,可知冯、袁二人有交往。袁于令入清之后与杜浚、褚人获、洪昇等人关系密切,而杜浚又与李渔、丁耀亢、酌元亭主人等人过从甚密。丁耀亢在北京居于陆舫时,与张缙彦有交往,丁的《陆舫诗抄》卷五(癸巳,即顺治十年)就是张缙彦鉴定的;张缙彦在任浙江左布政使时,与李渔颇有交往。如前所述,顺治十七年(1660)丁耀亢在杭州与杜浚、酌元亭主人等交往密切,此年李渔也和丁耀亢、丘海石等同游西湖。如此形成一个交往链环。这个链环的活动中心在杭州。
第二个交往链环包括冯梦龙、李清、陆云龙、陆人龙、方汝浩等人,或许还有董说。冯梦龙与李清相识,李清是陆云龙的老师,陆云龙曾为方汝浩的小说作品作序,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与方汝浩的《禅真逸史》是同一个刻工刘素明所刻。如此形成第二个小说作家的交往链环。这个链环的活动中心也是在杭州。
这两个交往链环中的成员因与冯梦龙的关系而串成一个松散的团体。所谓松散,一是指这个团体并无明确的交往宗旨和共同组织,二是指其中的一些作家彼此之间可能并不相识,只是都在这个团体之中而已。他们大多与复社、几社联系紧密,董说是复社中人,或许也在此团体之中。
另外,西子湖伏雌教主所著《醋葫芦》,前有署名“笔耕山房醉西湖心月主人题”的序,而醉西湖心月主人是《弁而钗》和《宜香春质》的作者。《醋葫芦》和《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中的附图和刻工都署有“武林项南洲刊”的字迹,不知西子湖伏雌教主和撰《七十二朝人物演义》于“西子湖之萍席”的秋磊道人有无直接交往。若有,则西子湖伏雌教主、醉西湖心月主人和秋磊道人也组成一个交往链环,这个链环也是在杭州活动的。《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第六册《醋葫芦》所附前言中,认为西子湖伏雌教主和醉西湖心月主人是同一个人,未知确否。至于《皇明中兴圣烈传》的作者“西湖义士”,则不知与上述诸人有无交往。
第四节作家交游与小说创作
人际交往对小说作家的创作颇有影响,往往会影响到作家对题材的选取,有时还能促进作品的出版。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大多交游广泛。譬如凌濛初,其《墓志铭》中记载:“公为人豪爽俊逸,倜傥风流……一时名公硕士,千里投契,文章满天下,交与遍寰区。”再如艾衲居士,紫髯狂客在《豆棚闲话》“评语”中,说艾衲居士“遍游海内名山大川”, 天空啸鹤在《豆棚闲话叙》中也说他曾有“算将来许多盟兄社弟”,则其足迹所到之处很多,所交社友也很多。
明清之际小说作家中,游历生涯最长、游历地域最广的,似乎当属李渔。他的游历生涯多半出于谋生的需要。他曾自述:“予担簦二十年,履迹几遍天下。四海历其三,三江五湖则俱未尝遗一,惟九河未能环绕,以其迂僻者多,不尽在舟车可抵之境也。”
广泛的交游,对小说作家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前文所引白眉老人的《玉闺红·序》,记录了东鲁落落平生的生平经历和交游情况。接下来,白眉老人又记载了其创作情况:
退而著述,所作甚多。而印行者,仅诗集两卷而已。今春间君以近作《玉闺红》六卷见示……君他作尚多,计有《金瓶梅弹词》二十卷、《梵林艳史》十卷、《兵火离合缘》四卷、《神岛记》一卷,皆未刊之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