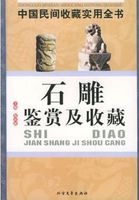在波德莱尔那里,“过渡、短暂、偶然”的诗意表述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体现了现代主义艺术变动不居的“创新”特性和人们永无止境的“创新”追求。他曾把热切渴望现代性的现代人比作“富有活跃的想象力的孤独者”和“片刻不停地穿越浩瀚的人性荒漠的游历者”——他们“把从时尚中抽取隐含在历史中的诗性的要素作为自己的工作。”[70]康拉德则宣称:“我是现代人,我宁愿作音乐家瓦格纳和雕塑家罗丹……为了‘新’……必须忍受痛苦。”[71]对此,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卡林内斯库指出:“‘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以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的雄心”,以至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72]
保罗·德曼则通过对尼采的分析来阐释审美现代性的创新内涵。他说:“尼采的无情的遗忘,他以此使自己投入一种减轻以前一切经验的行动中去的盲目,并把握住了现代性的真正精神。”“现代性存在于渴望涤荡一切东西的形式之中,存在于最终达到可以成为真正现代地步的希望之中,达到标志着一个新出发点的源泉。有意遗忘和同样也是一个新出发点相结合的相互作用,便获得了现代性观念的全部力量。”[73]在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进化论价值旨归时,李欧梵指出:“自晚清以来,日益面向当前的思想(以区别于过去面向经典儒学的总倾向),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讲,都充满着新‘内容’:从1898年的‘维新’运动到梁启超的‘新民’概念,到具体表示五四的新青年、新文化和新文学,‘新’这一形容词几乎伴随着所有的社会和知识界的运动,使中国摆脱昔日的桎梏,从而成为‘现代’国家,因此,‘现代性’在中国不但意味着对当前的专注,而且也意味着放眼求索‘新意’,从西方求索‘新奇’。”[74]
当然,事实表明,“创新”有其辩证法,一种“为创新而创新”的价值取向必然为人诟病。对此,豪泽尔指出:“促使艺术发展的一种最有效的力量,一方面来自自发情感与传统形式的矛盾,另一方面来自创新形式与习俗情感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决定了艺术史辩证法的生命力。”[75]这就要求我们,面对具体的文本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3.在审美价值和社会功能的维度,审美现代性意指一种审美反思性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曾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性”是现代哲学的重要概念。它指涉自身,因为所有知识都可以从反面加以解释。在反思者那里,他/她强调一种自觉的矛盾意识,即,提供思想发展资源的人恰恰又是破坏追求这种知识的人。这就好像一个赶路的人不断提醒自己不要走错了方向,并不停地审视已经走过的路,发现自己的得失成败。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有研究者指出,它“不只是预示着强大的历史欲求和实践,以及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方面发生转型,同时在于它是社会理念、思想文化、知识体系和审美知觉发展到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也许,更重要还在于现代性表达了人类对自身的意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人类不仅反思过去,追寻未来,同时也反思自我的内在性和行为的后果。”[76]在西方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通常是以一种批判、否定和超越“启蒙现代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现代主义艺术就是这一“形式”的集中体现者。甚至,经过现代主义艺术的折射,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成为了“审美现代性”的主要规定性。在这里,由于这种规定性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认真分析、甄别其性质是我们准确把握审美现代性理论规定的关键。
哈贝马斯指出:“美学现代性的精神和规则在波德莱尔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轮廓。那时,现代性以各种各样的先锋派运动形式开展起来。”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破坏历史延续性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图,我们也能够依据新美学意识的颠倒力量对此作出说明……它沉醉于带有渎神行为的恐怖的幻觉之中。”[77]在价值和功能的维度,这表明,“现代性”这一“杂音异符混合体”存在着“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立关系。其中,后者是以批判前者的姿态出现的。那么,在现代性的内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情形呢?要言之,原因在于启蒙现代性的僭越,即,启蒙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异化出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滋生了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和市侩主义。对此,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艺术家都有充分的揭示。
马克思指出:西方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78]这“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79]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也指出:“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现象不是进步道路上的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况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的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时刻。”[80]在韦伯那里,“合理化”在促进西方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使现代生活变成了工具理性统治的“铁笼”,并且,“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81]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于,“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一般的工具。”[82]“技术逻各斯被转化为持续下来的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的解放力量——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83]
无疑,“‘现代性’确然有解放的功能,个人的自主性之扩大是现代性的主题,但现代性也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疏离感’、‘意义的失落’、‘心灵的飘泊’等,更深刻的是现代化虽基源于‘理性化’,但‘工具性理性’的膨胀实在是对‘理性’(reason)的逆反。”[84]事实上,这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各式各样“反现代化”、“去现代化”运动的根源。这样一来,面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经济系统与文化系统、资本家的经济冲动与艺术家的文化冲动等一系列矛盾冲突和价值对立,一种“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规定了审美现代性,[85]进而使审美现代性的感性成为了启蒙现代性的反拨和纠偏,使“审美”成为了被异化了的人生的“救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极力推崇荷尔德林“诗意栖居”的生存论价值,并强调,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诗性——只要能认识到时代的贫困和自身的贫困,便有从非诗意中开辟出诗意的可能。波德莱尔则告诫资产者,“宁可三日无面包,但决不可三日无诗”,以便借助艺术和审美使“灵魂之力的平衡建立起来”。[86]
当然,在西方语境中,“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这种矛盾与不和谐是必需的。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历史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间充满张力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其文化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需要的和谐。因为一开始就怀疑那些对和谐的连篇累牍的描述不过是对自己的臆想点所作的苍白无力、漏洞百出的反思,现代性的历史将它们纷纷抛弃。从这种快速的抛弃中,现代性的历史获得了自己的怪秘而又史无前例的推动力。出于同一理由,这一历史可以被视为进步的历史,人性的自然史。”[87]然而,如果将审美现代性的“反思性”仅仅理解为“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甚至将其泛化为“审美现代性”普适性的理论规定,那就既不符合逻辑,又不符合历史。具体说来,第一,在主体性原则上,尽管理性主体和感性主体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矛盾,但审美现代性并非一味拒绝和否定“主体性”。实际上,它只是通过倡导“感性主体”而实施对现代性的“重写”,并力图以审美之力重新激起对生命存在和快乐幸福的渴望,从而使人再次回到主观性和个体性。第二,人们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并非否定其自身,而是否定其因“僭越”而带来的消极因素和结果。实际上,启蒙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金耀基认为,当今时代,“‘去现代性的冲动’毕竟有它‘内在’与‘外在’的限制,要停止或倒转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现代化虽出现了不少‘病态’与恶果,但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新的机会与‘善果’(goods)却也是真实,更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88]陆贵山认为,“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实践理性都是人类的理性精神的宝贵财富”,“情绪化地和非理性地一概反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是不明智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本身是无罪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关键在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转化和运用的是否有效、合理和适度,是否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不能表面化地对待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负面影响,更不能因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对人和社会酿成了某种不幸,便去笼统地反对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本身。须知,以工具和科技形态出现的这些高级的人造物的背后隐藏着并表现着人与人的关系。”
因此,我们“应当坚持和发展人类的理性精神的一致性”。[89]毫无疑问,这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现实意义更是直接的、重大的。第三,审美现代性有“双重”的维度——它既反思“传统性”,又反思“现代性”,而不只是反思现代性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这双重维度,艺术的审美反思才具有广阔、绵延的时间和空间。第四,“审美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价值和功能可以表现为一种“对抗性”,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协同性”。在发生学上,艺术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协同功能,即,通过艺术活动来教化社会成员,协调社会关系,传递文化、道德和行为方式,沟通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事实上,就西方“现代主义”来说,其批判特质是19世纪下半叶以后才开始日益显现的,而在此前的启蒙艺术中,其审美现代性的“协同”价值和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审美现代性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具体性。综上所述,审美现代性在价值与功能上决不是仅仅表现为一种简单的批判性、否定性和超越性,而是一种内涵更为宽泛、丰富的反思性。
1.2.3“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与内质建构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从三个维度揭示了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规定。就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来说,这三个理论规定奠定了一个明确的背景和研究前提。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还需切实回到中国语境,并在中国现代性的解释框架和内质建构中来详细考察其历史具体性。
回到“中国语境”意味着探讨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首先必须正视“西方话语”与“中国言说”之间的关系。具体说来,一方面,“审美现代性”及其美学阐释能力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如果没有这一概念,或把它从我们的理论话语中剔除出去,那么,许多问题就不能解释清楚;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其简单化,更不能因语境的错位而将它变成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语境中,改革剧的审美现代性研究必须站在“中国经验”、“中国现代性”的基石和立场上,而不能亦步亦趋、简单机械地站在西方“后现代性”的角度和立场上。因为,那种“后现代性”化了的现代性理解,是发达资本主义进入到后现代阶段的历史产物。这对那些尚未完全完成现代性建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性的做法显然是不折不扣的错位。
在当前审美现代性研究多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现代性”无疑是矛盾纠葛的焦点——它既和西方现代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以其“中国特色”而同西方现代性相区隔;它既对中国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有规约性影响,又在其审美展开中得以艺术地观照和传达。在这种意义上,要探讨改革剧审美现代性的历史具体性,就首先要对“中国现代性”作出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事实上,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有学者指出,当前学界“尚未在中国现代性的特定含义上打开一条突破之路”,并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开拓的起点”。[90]这表明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中国意识”的自觉,以及摆脱西方现代性研究范式,实现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的创新趋向,具有可贵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在这里,由于“中国现代性”内涵丰富,不同的研究角度会突显其不同的内涵层面,同时,它自身还处于发展、完善之中,因此,要充分揭示其内涵有一定的难度。在这里,我们试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行程”、“解释框架”和“内质建构”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