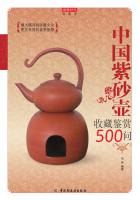今晚是北京的一个雨夜。北京一下雨就是“喜雨”,因为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雨水淅淅沥沥的诗意或滂沱瓢泼的酣畅,但北京少雨,因此,大城市一下雨就会让我敏感地联想到万物生长的快适,甚至听到遥远的田野里稻谷拔节的声音和不绝于耳的蛙鸣。还有,雨夜常常引发我莫名的喜悦,也许像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所透露的心境,也许是绵绵无边的雨帘隔断了身外世界的喧嚣和纷扰,也冲刷着这喧嚣和纷扰,营造出一个单纯、自由的思考和想象空间。这时,对我来说,“雨夜”是哲学的。
本书从选题、撰写到修改、成稿,始终贯穿、浸泡着一种思考——关于人生及人生意义的思考,或者说,本书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借助对改革题材电视剧的研究而进行的一种人生思考。改革开放30年间,作为生命的个体,每个人都有源自时世变迁的丰富、鲜活的现代性体验。其中,不管是渐次解放的欢欣,还是开拓前行的艰难;不管是命运沉浮的波折、沮丧或峰回路转,还是人生机遇的幸运眷顾与得天独厚;不管是传统留存的负荷或滋养,还是怀抱创新的冲动,义无反顾地奔向未来……这些来自日常生活的现代性体验无疑都需要我们认真检视和反思。特别是,对60年代生人来说,他们的成长经历和改革开放30年所展开的生动实践有着紧密的关联,他们的所见所思、他们的一步一履都和时代生活的精神脉动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而,他们在时世变迁中对现代生存境遇的切身体验、生命态度,以及价值的深层体会和生存智慧容易滋生一种人的“自知”,同时也具有一种历史见证和历史反思的可贵性。对我个人来说,作为农民子弟,我生长于乡村,成长于城市——对于乡土,最深刻的印象是,沙渚上白色的鸟儿依旧在灌木林上起起落落,是精灵翩舞于青山绿水之间,但房前屋后那成排成片的枣树、李树却已悄然退隐,现在只能在记忆的深处或梦回的雨夜,眺望它们果实累累的曼妙倩影;对于城市,尽管南转北折,但总的感受是,所有的城市大同小异。如今,身居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都市,小我联系大我,小我又时时反思大我赋予的生活要义。当思绪穿行于城市、乡村,常常让我紧张思考的是生活其间的“人”。
新时期30年来,我们已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改革开放”显然使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着蓬勃生机,13亿中国人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然而,历史无可避讳。当下经济生活中的失序、贫富之间的悬殊、人性的摧残与扭曲,以及人文精神的失落、伦理道德的滑坡、人格的被迫分裂等,作为坚硬的现实化解了古道热肠,也使简单的生活理想在风风雨雨中变得扑朔迷离。这表明,“改革开放”决不是一首轻松的抒情诗,而是有着剧烈阵痛和艰难曲折的历史进程。当然,对于生命个体来说,生存和生活本质上是具体的、个性化的。惟其如此,我们就须常常自问,在树欲静、风不止的时世变迁和穷、达两难执行的尴尬中,风景会否这边独好?或者,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纵使生命的航船有了确定的航标,也有执著的追求,但谁能断言,它会遂人所愿,最终抵达心安理得的寂静彼岸?在本书的思考和写作中,我以为,作为个案模型和世纪转型期的精神地形图,丰富的改革题材电视剧文本及其审美镜像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多样、深刻的现代性体验,也可以领会到多样、形象的人生解答。而我不揣浅陋的分析和阐述意在分享,更在对话,但对于时代和人生的思考和发言无疑最终取决于特立独行的你、我、他——事实上,惟有千千万万个特立独行的你、我、他,才能一起完成我们对于中国现代性的书写。
本书的基础是我2006年初完成的博士论文。客观地说,关于时代、人生及其意义的个性化思考是导师蒲震元教授所不能全部传授于我的。但蒲先生显然在字里行间已明了我的意图,并在言传身教中成了我的对话者和指导者。不仅如此,在艺术的领域,“中国现代性”不仅是理性思想层面的,也是感性体验层面的;在学术的领域,关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不仅是人生价值性的,也是学理操作性的,因此,在对话中,经由蒲先生的思维激活与磨砺,我多年的电视文艺从业实践转化为一种感性的积累优势,并在理论探索的纵深中,使我的研究在“术”之外有了一些“学”的价值。还有,胡智锋教授是一位思维活跃、经验丰富、思想深刻的学者,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胡教授言简意赅的指点让我获益匪浅。当然,我的思考和写作更多的是在一种群体性的对话中完成的。特别是,广泛阅读中的无言交流使我从许多求真、向善、趋美的思想者那里吸取、濡染了弥足珍贵的智慧和才情。如今,跳出书外来看“书”,自然是冷暖自知:留下的遗憾,须在以后弥补;坚持的己见,只好道同则谋。
今晚是北京的一个喜雨之夜。欣喜之余,我们还可以赋予“雨夜”一个澄明的时刻。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一个甲子一个周期,现在正是一个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时间点,就像一个旅人驻足回望、反思,然后再踏上新的征程。如果说,在改革题材电视剧的审美镜像中,我们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奔涌的历史诗情,那么,站在时世变迁的边缘,澄明的时刻让人悟生一种关于主体间性的启迪,一如智者所说:“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不舍不弃;来我的怀里,或者让我住进你的心里——默默相爱,寂静欢喜。”
2009年5月26日于北京朝阳定福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