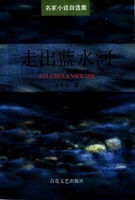检视改革剧30年来的艺术创作,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优秀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常常是选择一系列尖锐的、处于质变状态的矛盾冲突,并采取强化的办法把它们集中起来,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跌宕起伏中,使观众急切地关注着主人公的命运发展。比如,《苍天在上》将严肃、重大的反腐主题融入惊险的戏剧化故事情节之中。全剧一开始就以女市长和公安局长的相继自杀引出一系列的尖锐矛盾,而新来的代理市长黄江北却情况不明,且势单力孤,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形下,作品进一步采用“抑制—延宕”的叙事手法,不断形成密集的矛盾纠葛和紧急危机,使情节的发展如云遮雾罩般扑朔迷离,又如波涛汹涌般起伏消长。这就有效地使观众在紧张、猜疑的心理状态中完成了对黄江北反腐行为的心理认同。与之相似,《抉择》将一个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反腐主题抽丝剥笋般细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其中,腐败分子的专横跋扈、道貌岸然和李高成的高尚气节、正义凛然形成鲜明的对比,并有机地交织在一起。不仅如此,李高成的艰难抉择与其夫妻之间的亲情、战友之间的友情等紧密结合,进而使作品的艺术叙事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渐次推进,也使观众在这“渐次推进”中时时有所担忧、时时有所期待,直到忠奸分明,云开雾散,朗朗乾坤。
当然,随着改革剧艺术实践的日益丰富,其“主旋律”叙事在传统“故事化”和“戏剧化”的基础上还有不断的创新和发展。择要说来,一是人物内在的性格冲突不断得以强化。相比之下,新时期早期的一些改革剧作品往往只注重外在事件的矛盾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改革剧的艺术叙事除了注重外在事件的矛盾冲突外,还特别强调彰显人物内在的性格冲突。像《选择》、《岁月长长路长长》、《车间主任》、《人间正道》、《三连襟》、《忠诚》、《省委书记》、《世纪之约》等作品,无论是立足于风口浪尖的时代波涛,还是着眼于平凡状态的生活潜流,它们均力图在“人”与“事”的相辅相成中将人物的性格冲突表现得有声有色。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方法讲“好”一个故事。不必赘述,讲一个“好”故事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讲”好一个故事。比如,情节节奏的把握、场面和细节的丰富与细腻,以及整体性的驾驭等。在《省委书记》中,尽管其场面并非新颖,细节也并非完美无缺,但作品之所以被观众看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情节的节奏安排张弛有序、生动流畅。三是营造出故事叙述的“朦胧美”。在一般的理解和实践中,人们往往强调要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然而,艺术叙事中的“朦胧”,或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比如,在《苍天在上》中,田副省长就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他就像曹禺《日出》中的金八、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老爷一样,人虽未出场或出场很少,但却时时控制着章台市的全局,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再比如,在《乡下人·城里人·外国人》中,草儿的身世之谜贯穿全剧。这不仅是剧中人物都关注的问题,也是观众急切想了解的悬念。在叙事效果上,这不仅使呈现在“前台”的故事讲述有了一个时隐时现的深厚背景,增添了情节发展的纵深,还极大地增强了观众收视的期待。无独有偶,在《世纪之约》中,作为一个辅助的故事情节,梁小可的身世之谜推动了叙事进程的发展。不仅如此,其身世之谜的揭开还成为了她回归集体主义价值观,实现民族情感认同的重要转折点。显然,这对作品的人物塑造和主题升华无疑起到了良好的烘托和推进作用。
就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而言,如果说,“故事化”是其叙事方式上重要的审美表征,那么,在“故事化”的基础上,它还体现出鲜明的“风格化”特征。具体说来,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是显著的:
一是不同类型化叙事因素的杂交与综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影视剧类型化叙事经验的增多,改革剧的“主旋律”叙事在学习、借鉴多种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类型因素和美学因素的同时,还在融会贯通和创新发展中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风格化”审美特征。比如,《浦江叙事》成功地借鉴了言情剧的叙事方法;《苍天在上》将悬念因素渗透到故事讲述的内在结构之中;有些作品则广泛吸纳多种“类型片”(Genre film)的叙事因素和叙事技巧,把言情、警匪、侦破、枪战、打斗、青春偶像、商战等多种因素杂交、综合在作品叙事之中。
二是“情节剧”叙事模式的借鉴和推陈出新。“情节剧(Melodrama)”本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戏剧形式。一般说来,“在观点上,‘情节剧’强调人性和道德,在情绪上充满了热情和乐观精神,最后美德得到报答、罪恶得到惩罚,以寓言式快乐的结局而结束。”其显著特征有:追求感人的效果、夸张的表述、强烈的行动、过度的修辞、道德上的二级化和善恶有报等。[36]由于“情节剧”可以容纳紧凑丰富的内容、曲折多变的情节、急促惊险的动作,而且,它还具有浓厚的、通俗性、娱乐性色彩,因此,它的一些叙事技巧和特点被有效地化用到改革剧的“主旋律”叙事中来。比如,在《农民的儿子》、《沟里人》、《好爹好娘》、《郭秀明》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种本土化的审美改造,那种以“苦情戏”为核心场景的叙事技巧逐渐成为了一种感动观众的有效手段和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像《郭秀明》,作品通过主人公的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自我牺牲等优良品格来形成叙事结构中对立双方的力量对比,并通过“感化”来争取矛盾各方的支持与理解。在艺术接受上,这不仅使人物的性格塑造在一种特殊的情感状态得以完成,还使观众在一种泪如雨下的忘情状态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预置视野达成融合,并具有润物细无声的艺术感染力。
三是喜剧因素和喜剧风格的调用与渲染。由于题材、主题的严肃性,一般说来,改革剧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崇高的正剧风格,但在许多作品中,其“主旋律”叙事中出现了诸多轻松、诙谐的大众音符,并逐渐呈现出一种特色鲜明的风格倾向。比如,《忠诚》、《刘老根》、《至高利益》、《三连襟》等。在这里,我们之所以说这一喜剧性风格是一种“倾向”,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其最多见的情形是在整体的正剧叙事风格中出现了许多“喜剧化”的情节、场景等。比如,在《忠诚》中,高长河一个人去明阳市上任,途中巧遇镜湖县县长胡早秋;两人一同去查办污染案,却因为“随地小便”而被当地的联防队员扣留了起来,最后,还开着一辆破车“逃”了回来。在《三连襟》中,整体上看,由于孙天生们的精神升华必定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作品的艺术叙事相应带有严肃的风格色彩,但作品在表现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却加入了轻松、诙谐、幽默的格调。其影像和动作引导观众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去作一些深层次的人生思考。在《至高利益》中,作品的喜剧性特点集中体现在平岗镇党委书记计夫顺和镇长刘全友这一对“活宝”身上:由于前任镇长花建设留下了巨额的亏空,因此,他们俩一面是住着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一面是守着上千万的欠债单唉声叹气,艰难度日。在作品的叙事进程中,喜剧性的细节和场景处处皆是。比如,刘全友到处被债主围追堵截,常常落荒而逃;他向别人讨债,却只抱回一只哈巴狗。而计夫顺,为了镇里的日常用度,他绞尽脑汁与林业局督查组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为了镇里的经济发展,他装疯卖傻与上级领导“斗智斗勇”,其行为方式与语言表达常常令人发笑。当然,在这些令人发笑的场景和行为背后,观众很容易就能看到其中的无奈和感伤。与以往此类人物形象相比,其意义负载已超出了一般喜剧风格的范畴,换言之,在“含泪的微笑”中,“小人物”们身上既带有一些鲁迅式灰色幽默的无奈和反讽,又带有一些布莱希特“史诗剧”的间离效果和震惊。
4.2.1.3叙事策略上的“家—国”一体化与伦理泛情化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有着悠久的“家—国”一体化和“政治—伦理”一体化的文化传统。其中,“国家政治通过家庭伦理进人现实人生,伦理的规范性和道德的自律性通过这种一体化而转化为对政治秩序的稳定性的维护和说明”;“政治意识形态借助于对伦理道德规范和典范的肯定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37]在论述第三世界文化的寓言性质时,杰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38]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将“民族寓言”的内涵仅仅理解为狭小的政治投射,而是可以包含更为深广的本土意识和本土问题,以及民族形式的深层因素,那么,将某些改革剧文本看成是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就有其适切性。不仅如此,这种“适切性”还会进一步向我们敞开关于“家—国一体化”叙事的意义面向,即,通过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并使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中接受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
在改革剧“主旋律”叙事的通俗化中,家—国一体化叙事的运用有深厚的文化原因。具体说来,第一,从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审视,正像汉语中“国家”一词所显示的,“国”与“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国—家”融合、“家—国”一体的文化无意识深层结构不仅铸就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规定了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文化视野、文化选择,以及家庭/社会/政治的伦理化表达方式。特别是,在以“家”结构“天下”的过程中,以儒家文化精神为内涵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杜维明说:“孔学,或曰仁学,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和代表。”[39]这种以“仁”为核心的社会人生理想,具有浓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用理性色彩。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深层积淀的民族文化结构和集体无意识力量,它至今依然有形无形地左右着人们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取向。
第二,从影视艺术传统的角度看,有关“家—国”故事的伦理喻示是中国许多电影创作者的基石,甚至,作品的伦理结构还可以看作是结构的结构——一种处于意识深层的能动结构。比如,从郑正秋、蔡楚生到谢晋,家—国一体化叙事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作品的“能动结构”往往以“家庭”为中心场景而展开广阔的人生视阈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并将一个或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与民族/国家的盛衰兴亡紧密结合起来,生动地映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社会的兴衰起伏。像《姊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作品就是突出的例证。时至今日,可以说,这种“家—国一体化”叙事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在泛悲剧时代,“主旋律”影片呈现出一种新的儒学化价值取向。其具体表现是,“在主旋律影片所呈现的当代价值系统中,更多地杂糅进以儒学价值系统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前者如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任劳任怨、公正廉洁等品质,后者如仁爱、仁慈、仁厚、感化、中和、文质彬彬、成圣成贤等品质或风范,这两者形成复杂的相互交融。”[40]
第三,从“国家”一词的现代含义看,在英语中,与“国家”相对应的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词语:“country”、“nation”、“state”,其中,“country”的内涵侧重于疆域和国土,“nation”强调民族和人民,“state”则突出国家机器或政府机构。然而,不管是“疆土”的含义,还是“民族”、“政府”的含义,它们都具有很高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因此,在改革剧的艺术叙事中,“国家”难以成为直接的形象而呈现在影像表意系统之中。与之不同,对广大观众来说,“家”是与每个人的切身经验直接相关的,其形象和内涵也是具体可感的。这样一来,由“家”而“国”,是“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建构和完型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第四,从电视剧的媒介特性看,电视剧是一种大众性的“家庭艺术”。就改革剧的艺术叙事来说,一方面,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风波可以折射出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家—国一体化的叙事策略在社会文化与审美心理层面极大地尊重了中国老百姓的审美习惯,因而,其民族特性、现代品格与电视剧媒介的大众性、平民性、通俗性等有相当契合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