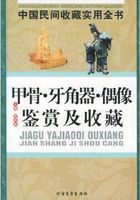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并不会有意识地在影片中寻找思想和意义(当然在看后会有主题需求),更多的是寻求情感的享受和情绪的宣泄,而这种情感是由影片中的人物携带的。正如俄国文学理论家瓦·费·佩列韦尔泽夫所说:“思想要到认知类作品中去寻找,在艺术创作中找寻思想,无异缘木求鱼。文艺作品魅力不朽的奥秘归结为形象所特有的情绪感染力。”电影是面向大众的艺术,更应该懂得用鲜活的形象、用形象表达出的情感来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而当下的视听大片把注意力放在了影像上,为了增强视觉造型的力量,不惜伤害、牺牲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十面埋伏》结尾,为了增加“随风”和“捕头”之间的打斗,为了扩充花海大战的场面,为了延长乌克兰从秋景到飞雪的突变,导演擅自将女主人公“小妹”弃置不顾,翻来覆去地让她死了四次,严重违反了人物形象塑造的真实性,更不管观众的感受,不管实际生活中的逻辑,影片变成了影像的自说自话。
同时,影片对一女两男三个形象的塑造,缺乏情感的基调,这是一个爱情正剧还是悲剧?从最后影像营造的氛围看是悲剧,像影片最后的雪地大战,本来是很苍凉很凄美的,但是正当观众要掉眼泪的时候,却因为“小妹”久而不死的形象哄堂大笑。如果导演按悲剧情感基调来处理,让随风和小妹这两个追求生命自由,用三天时间就爱得死去活来的恋人一起死去,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观众看,这也许是很凄美很悲壮的。但是制造者没有自觉地对人物情感进行细致把握,以至于让人物在雪地大战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以牺牲“小妹”形象的代价换得几分钟的美景。
而《无极》为了获得魔幻影像,凭空添加了一个形象——满神。
这个形象既不是中国的女娃、观音,也不是西方的雅典娜、命运女神。它是一个生造的、没有来源的神。当然艺术作品允许虚构、允许想象,但这个虚构的、生造的神要在作品中发挥她的功能,她要与其他的人物形象发生关系。《无极》中,满神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片头,她预示了女主角倾城的命运,一次是在树林中预言了大将军光明的命运。这个神总是不请自到,总是轻易地说出影片千方百计想体现的内核,总是想说就说,说完就走,她与其他人物没有任何关联。人们并不信奉这个神,这个神也不对这些人负责。人与神既没有对抗,也没有拯救。满神的功能在影片中并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推动叙事,却耗费了不少影像的力量。
《无极》对魔法的过度依赖让人物脱离了故事本身,故事显得玄虚而没有力量:“不要随便把神请下来,除非遇到难解难分的关头非请神来解救不可。”故事的核心是人的故事,只有人的形象立起来了,故事才会有一个好的走向。影片中其他人物形象,倾城、将军光明、公爵无欢、奴隶昆仑和雪国人鬼狼,更多的是一种意义的、概念的体现者,而没有还原为活生生的人。人物的爱恨情仇与创造者的情感并不同步,人物形象自然显得苍白无力。虽然有羽衣、羽毛,有金手指、金鸟笼、流星锤,还有比光速还要快的奔跑,这些装饰增强了一些人物的动作特点和性格特征,并赋予了人物某种情感力量。但由于人物形象的虚弱塑造,这些华丽的、铺张的影像只能展示行动,而不表示“性格”与“思想”。因为太华丽的影像会使“性格”和“思想”模糊不清。
形象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其特有的情绪感染力。因为我们透过艺术形象了解人类生活,体验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的生命。接受形象,意味着感受他的痛苦,体会他的情感、想法、命运。这是观众想要看的,也应该是创作者给予的。
以上谈了影像对主题的呼应、影像对人物的支撑,接下来不能忽略的是电影对细节的关注。在视听大片中,电影人对有些细节格外关注,不惜投入大量的影像。《十面埋伏》中的飞刀几次出现,从飞刀的逼真的形式、声音,到飞刀刺人的瞬间,影像都给予了极度的渲染。观众虽然震撼于飞刀的视听效果,却仅仅视飞刀为一小小的刀具。它是谁的并不重要,它的功能是什么也不重要,它只是一个杀人武器,它可以杀敌人(敌军),可以杀爱人(小妹),还可以杀朋友(随风)。影像给予它过度的关注,但与故事并无多大关联,所以观众并不领情,看过就过。
《无极》中那个金鸟笼,是千百年来权贵们为其占有的美丽女性所筑的金屋。金屋与倾城身穿的羽衣构成了对美丽女子命运的写意表达。还有那片羽毛,羽毛在影片中有一段飞行特写,无欢手下的人为追逐羽毛而遭杀身之祸,无欢面对羽毛是一种矛盾心情:狠命抓住,又不屑地将之丢弃,使羽毛的纯洁和沾血的玷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这些影像着力呈现的细节在实现过程中与剧情有些脱节,细节的堆积没有形成最后的贯穿力和爆发力,全不如《卧虎藏龙》中的那把青冥剑来得出神入化。
《卧虎藏龙》中的青冥剑既是俞秀莲与李慕白爱情的见证物,也指涉了玉蛟龙与李慕白之间看不见的情愫,更隐喻了俞秀莲与玉蛟龙争夺的情感。一个江湖上的器物,却把整个故事串连起来,为故事增添了些许的韵味。
大片中影像与叙事的断裂,是因为在电影创作中出现了一种转向,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轻叙事重视觉造型。《十面埋伏》和《无极》一样,都是“视觉盛宴”。传统电影讲究影片剧本的文学要素,《十面埋伏》的文学性可说是乏善可陈。人们只是啧啧称赞《无极》中比光速还快的奔跑,人们惊讶于《十面埋伏》中竹林大战的完美。毫无疑问,影片创造的视听奇观是绚烂的。然而,如果电影叙事不向人类的心灵开掘,不挖掘叙事艺术的美,电影会不会终归平淡?
国产大片在初期实验阶段,电影剧本都采取了原创方式。电影人希望在有巨额资金的保证和最新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表达自己对电影的态度。他们的努力和尝试得到了不同人们的不同声音。在电影影像的突破和电影产业化方面,初期的国产大片赢得了最多的赞美之词。但在电影叙事和电影精神的传递上,国产大片遭遇了最为严厉的批判。一时间,国产大片将何去何从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国产大片也开始反躬自省。
由于大片是一种投资巨大、风险极高的电影样式,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人,在可能的情况下,都会采取一种极为保守的制片策略来规避风险:大投资,保证没有更多的竞争者;大明星,是极有力的票房号召力;名导演,代表了优良品质。在经历了国产大片初期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国产大片在问题最多的环节——电影叙事上进行了改良,当然,是一种保守的改良策略——名著改编。
《满城尽带黄金甲》借用了曹禺名剧《雷雨》的故事,它将一个中国现代家庭伦理悲剧移植到了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个王室家族中。无独有偶,《夜宴》则把西方的经典戏剧《哈姆雷特》移植到了中国古代的宫廷之中。两部投资过亿的大片,都选择了以历史经典名著为拍摄蓝本,都选择岁末这一黄金时间登场,无疑是想借助经典的永恒魅力和新技术的无所不能,为观众奉上艺术技术都过硬的视听上品。结果如何呢?
《夜宴》招来不少批评声。其中“莎式台词”是最遭观众诟病的。莎士比亚剧中咏叹调式的台词转译成半白半文的中文,怎么听也觉得有些怪;“毒蝎子细节”的照搬挪用显得似曾相识且生硬;“母后”形象的浓墨重彩完全遮蔽了“哈姆雷特”的光彩。可以说,《夜宴》是对《哈姆雷特》一次大胆的引用,却不是一次成功的名著转译。
说到电影改编,人们容易忽略的是,从小说到电影,“远不仅是内容元素的取舍或浓缩,更重要的是两种媒介系统、两种语言间的生成转换,或曰翻译。”这种翻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忠实于原著,保持原作的基本内容和重点,风格上追求相似的特征。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乱世佳人》《包法利夫人》《简·爱》《布拉格之恋》《祝福》《林家铺子》等成功的作品都是忠实原著,让观众领略到文学名著的魅力和风格。这样的改编,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名著。第二种翻译是超越原著,改编者不再以当学生的态度一味地遵从原著,而要表现改编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卡莱尔·雷兹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黑泽明的《乱》、库布里克的《闪灵》、《睁大双眼》、《洛丽塔》等,都是将名著的内容和当代或历史的生活结合起来,引发一种新的见解和思想,从而引起观众的兴趣和思考。《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无疑采取了后者的翻译方法。但它们的改编有了太多的商业媚俗和艺术妥协,没有抓住原著的精髓和改编的要义,使得名著改编影片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夜宴》由于大明星章子怡出任女主角而改变了《哈姆雷特》的故事走向。章子怡年轻而骄人的面容不适合饰演哈姆雷特那个心理复杂的母亲,导演便让她做了吴鸾(哈姆雷特)的情人兼继母——婉后,她成了影片戏份最多的人。她听任厉帝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并委身与他。在吴鸾要复仇时,她又策划了更大的阴谋:杀王夺位。她终于成了一代女王,结局却逃不脱被杀的命运。而吴鸾,原著当中的哈姆雷特,却全然没有王子风采,只成为一个单薄的符号。
《哈姆雷特》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莎士比亚塑造了哈姆雷特这个核心人物,在于作者借哈姆雷特之口提出了一个问题:“To be or not to be?”这个问题萦绕在人们心头,引发无尽的思考。俄国作家契诃夫曾把人类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哈姆雷特,一种是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代表高尚优雅,但不具备行动能力。堂吉诃德鲁莽冲动,但他敢于行动也能够行动。”可以说,哈姆雷特的犹疑踌躇,构成了哈姆雷特的哲学意义。而《夜宴》中的吴鸾由于没有这样的心理动机,完全遗失了哈姆雷特独有的气质。
《夜宴》由于演员的问题(大明星带来的潜在的票房保证)而采取了妥协策略,章子怡取代了哈姆雷特的主角位置,哈姆雷特的故事转变成了婉后的故事。可这样一改,就会碰到一个难题:影片试图要建构一个新的人物谱系和新的价值观念。但是原著是有一个完整稳定的结构,每个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动机都有其合理性,彼此相关,互相勾连,稍加改动都会起到一连串的变化。《夜宴》一方面是沿用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情节,一方面在观念上几乎是一种颠覆性的改编,这样生硬嫁接的结果只能给观众带来困惑和不满足。
2006年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是根据著名话剧《雷雨》改编的。因为张艺谋自己也非常清楚经典名作的力量:“自己编故事总觉得弱。我是一个导演,不是一个作家,我的强项是用画面讲故事,所以要选一个好故事。《雷雨》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故事集中在24小时,戏剧冲突非常强烈,有古希腊悲剧的影子。”
《雷雨》是个悲剧性文本。故事发生在周家大宅的24小时内,周家在周朴园的控制下,保持着圆满与秩序。一切都因为鲁妈的意外到来发生了变化。鲁妈无意中揭开了笼罩在周家的面纱,露出了不堪入目的肮脏底色。人们不堪忍受,死的死,疯的疯,落了个茫茫大地真干净。
悲剧,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里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通过装饰的语言,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他特别强调了“发现”是悲剧的关键词。“发现”指的是“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即使置身于顺达之境或败逆之境中的人物认识到对方原来是自己的亲人或仇敌”。
而恰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将《雷雨》中的“发现”置换了。在《雷雨》中,鲁妈身份之谜的发现是全剧的核心。剧中所有人物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真相。鲁妈在走向周家时并不知道这就是周朴园的家,繁漪也不知鲁妈的真实身份,周朴园更不知繁漪和周平的私情,他们是一群不知情的人,却受到了命运的作弄。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无法挽回的事情,这是一种震惊人心的效果。这是一种苍茫的悲剧感:渺小的个体受到无法抗拒的命运的毁灭是谁也无能为力的。所以说,《雷雨》具有一种古典悲剧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支撑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将这个重要的“发现”让位给皇后的“菊花”。
“菊花”是皇后复仇的工具、兵变的标志,这个发现不是沉重命运的发现,而是复仇阴谋的发现。影片中的人物对自己的处境多少都是知情的:皇后知道大王想置自己于死地;大王知道自己的女人和儿子偷情;蒋氏在进入皇宫为皇后做事时就已经知道大王是自己的前夫;纯真的冲儿也变成洞悉一切阴谋的阴郁三王子。他们不是在命运之手的操控下行事,而是自觉地举起手中的复仇之剑,互相残杀。命运的恐惧和怜悯被个体的残杀而消解。宏大的悲剧,将矛头直指社会、专制权力和女性的悲剧被置换成了一个家族悲情故事。悲剧的意蕴无迹可寻。
《满城尽带黄金甲》仅仅关注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它的改写只在于观赏性需求,而没有提出新的见解。即这部影片缺乏原创,而原创是一部电影鲜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