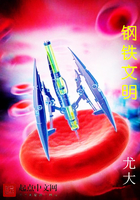戚学民
从1943年中至1945年,郭沫若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分别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其中《十批判书》尤为学界所重,国内学术界多有评论,但是意见尚有分歧。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认为,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果,在近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海外个别学者对该书的资料和观点的来源及作者的学术道德提出异议和质疑。这样对《十批判书》的学术价值的评判就成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本文认为,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评估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重要课题,应当继续讨论。但是评价的方法值得再作考虑,正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当时的特殊时世有密切的关系,既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战斗性,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既然与时事密切相关是《十批判书》的重要特点,那么我们研究讨论其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就不能脱离该书的具体语境和作者的著书动机,包括与此关系密切的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联系这些方面,《十批判书》的丰富内涵就能够得到更加准确的揭示。
但是以往相关的成果显示对于《十批判书》产生的过程研究是不够的,因而有关其学术价值的判断有脱离本书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倾向,直接导致某些结论流于简单,甚至错误。当然以往的讨论都是有益的,但是结合作者撰著动机等因素来考察,《十批判书》的丰富思想内容,尚有待发之覆。这篇小文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尝试对《十批判书》的价值提出自己的看法,具体方法是,先厘清该书的撰著动机,然后联系此讨论作者的论学主旨,在此基础上再评价《十批判书》的价值。不当之处,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一、新史学的研究风气
郭沫若撰写《十批判书》的具体环境和动机是首先需要明了的。很多研究者在考察《十批判书》的思想意义时,都肯定该书是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也有研究者从史学史角度考察,认为该书是作者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学术关怀的延续。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在具体的判断方面尚有一些疏漏。
《十批判书》的产生,固然与当时大后方重庆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政治环境和学术风气有密切关系,因而有着针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客观意义。但是作者的具体撰著动机,尚有更丰富的内容,不可用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来做简单概括。
本书的写作意图,我们首先得了解作者本人的见解。郭沫若关于撰写该书的动机有比较明确的交代,在《十批判书.后记》中他几次说:
同处在一个环境里面,大概是不能不感受同一风气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兴趣,不仅在我一个人重新抬起了头来,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不断有鸿篇巨制出现。这些朋友们的努力对于我不用说又是一番鼓励。我们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而我们的见解或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我不否认我也是受了刺激。我的近两三年的关于周、秦诸子的研究,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恐怕也是写不出的。
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和大家的看法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但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说陈腐了的一句老话,人生如登山。今天这句话对于我却有了新的意义。登山不纯是往上爬,必须窜下一个深谷。今天我或许已经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而比较轻快的是我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
史剧没有写成功,想和古代研究告别也没有办到,这原因我在这儿可以不必缕述。但在这儿却须要提到的,不仅和古代研究告别没有成功,而研究的必要反更被促进了。主要的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过,是在这个期间之内有好几部新史学阵营里面的关于古史的著作出现,而见解却和我的不尽相同,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依旧照旧主张,而对于我的意见采取着一种类似抹杀的态度。这使我有些不平。尤其当我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发表了之后,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这立刻刺激了我,要受他们的攻击,那是很平常的事;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甚至遭受敌视,那却是很令我不安。因此,我感觉着须得一番总清算、总答覆的必要。就这样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心向便更受了鼓舞。
此处引文的意义是明确而又含糊的。明确之处在于郭沫若明言《十批判书》写作动机源于他眼中的具体思想环境和学术风气,就是抗战后期新史学阵营的历史研究“风气”,以及以新史学的立场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的成果,对他的“鼓励”和“刺激”。含糊的原因是此处提到的新史学的研究风气和对郭沫若的“刺激”,当事人很清楚,但是后来的人则对此不甚了了。而这两点却正是了解郭沫若《十批判书》写作意旨的关键,因此本文就力图对此加以揭示。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新史学”研究的“风气”。按我们现在的理解,新史学是泛称,从某种意义上,自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之后,20世纪中国的史学研究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西方的史学为研究范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标志,到抗战时期,大多数学者的历史研究都可以称为新史学。抗战结束前后写成的《十批判书.后记》讲到“新史学”,也会令人理解为是泛指,但其实是特指,略加考证其具体所指是很容易弄清的。
郭沫若在这里说的新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所说的历史研究风气就是指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历史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继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获得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突出表现是历史编撰工作领域,出现了几部以马克思主义立场撰写的中国通史,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两个中心:延安和大后方特别是重庆。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在延安方面是共产党人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愿望和积极作为,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则是出于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压迫和限制。
抗战的特殊环境,让历史学家们跳出书斋,他们普遍投身于决定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去。他们中很多人的史学思想发生了转变,特别注重历史学的现实功能。
马克思主义一向是注重改造世界的实践革命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更是注意历史研究的战斗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撰工作在延安就是这样的严肃革命工作。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谬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面临的挑战,也是形势的客观要求。毛泽东统筹全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作用。陈伯达先后写成了《论孔子的哲学》和《论墨子的哲学思想》,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来到延安的进步历史学家也积极投身于这项革命工作中去,范文澜1940年到延安后,做了关于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演讲,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得到他积极的鼓励和评价。他让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写成的通史。
在大后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也得到了发展,但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反动文化政策。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大后方的政治环境日益恶劣。党为了保护和保存进步力量,陆续撤走了一部分党员和进步人士,对于留在大后方国统区的进步人士,党制定了“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方针。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聚集了大批进步学者和文学家,国民党当局多次干预不果后,决定剥夺郭沫若厅长职务。经过中共方面的争取,国民党另外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仍以郭沫若为领导,其成员也主要是原政治部第三厅的成员。这样在大后方,党在国民政府内部就保留了一个合法的公开进步文化机关。国民党方面规定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从事研究工作,不能进行政治活动。这样,学术研究活动就得到了一定空间,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大后方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积极开展学术研究。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经常举办学术讲座。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组成了读书会,讨论各种问题。在私人交往中也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
在各种学术研究中,历史研究得到特别的重视,在重庆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群体,其成员包括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后来去延安)、杜国庠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杜国庠、侯外庐等人发起组织的历史研究组织就叫“新史学会”,并且郭沫若就是其中一个成员。在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出产了一批成果,如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在此阵营中的人有所体会,不属于马克思史学阵营的其他学者也有所体察。齐思和在评价中国当代史学研究时曾说:“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顾颉刚也曾在私下表示:“范文澜、翦伯赞们所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
延安和大后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研究和编撰工作不仅是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学术研究的巨大进展,而且是党的政治斗争的一个有机环节。他们的工作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文化政策,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也从整体上推动了历史研究学术水平的发展,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郭沫若的著作就是对这种研究风气的回应,而且本身也是这个历史潮流的一个重要成果。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兴趣,不仅在我一个人重新抬起了头来,同一倾向近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不断有鸿篇巨制出现”。
郭沫若所处的,正是后方的新史学的中心之一,并且他本人就是重庆的大后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领军人物,是党树立的鲁迅之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参与到历史研究之中来也是合理的。延安的史学研究成果也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国统区,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作为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作为大后方学术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了解到这些情况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他所谓的“新史学”实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他当时的处境实在不便明说,而且他自己也是党领导下的新史学会的一个成员,用新史学来代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很自然的。
因此说《十批判书》从总体上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化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正是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当局的政策客观上造成在重庆的马克思主义派学者转向史学研究,他们从事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但是就《十批判书》具体撰写动机,并非用打破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政策所能概言,其所针对的“新史学研究风气”,是指马克思主义学派成员及其成果。
二、同道的“刺激”
揭示《十批判书》撰著动机的另一个关键是新史学阵营的“鼓励”和“刺激”。鼓励较好理解,这是一种良性的促进关系。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之间相互讨论、相互促进的情况是很常见的。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曾经不止一次和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讨论或辩论,比如和翦伯赞在抗战时期经常就学术问题通过信件往返讨论。这可以说是“鼓励”的例子。
哪些可以称为“刺激”呢?哪些新史学著作对郭沫若产生了刺激呢?对此郭老有一些提示,却没有明说,但联系郭老著作的内容和当时的材料,我们也不难获知其确切所指。从前引《十批判书.后记》可知,郭沫若所谓的刺激有两点:一是新史学家们编写中国通史时采用“西周封建论”,对他的意见采取“抹杀”的态度,使他感到不平;二是他的《墨子的思想》一文引发了普遍的非难,而遇到同道的非难“甚至遭受敌视”,让他觉得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