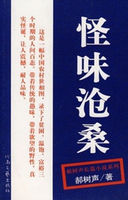第四是说中国人迟迟没有认清西方势力对中国早已形成剪刀式进攻的态势。蒋廷黻认为: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对亚洲和对中国构成的危险就像一把巨型的剪刀,中国就是在这剪刀口内求生存、求发展。蒋氏在此问题上特意浓墨重笔,先后发表《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和《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两篇长文,其意在详细说明“十七世纪的大变动,不在传教或沿海的通商,而在全亚洲北部之更换主人翁。俄人于1579年(明万历七年)越乌拉山而侵西比利亚。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俄国未占西比利亚以前,中西的接触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占领以后,中西的接触加添了北疆的长线。从欧亚关系史看,我们可以说,自17世纪起,欧人分两路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合起来,形成剪刀式的割裂。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到19世纪末后三十年,这把剪子的作用更加积极,不仅如此,更加凶险的是,又加上了“向我们正面砍杀的一把屠刀——日本”。光绪年间的政治家对此严峻形势虽然有所认识,但认识不足。他们比前人虽有进步,但进步不够。其结果是:他们筑堤一寸,而外来的潮却涨了一尺。
第五是说当时的中国人对英国与俄国的对华外交和侵略特点分辨不清,以致误把侵略当友谊,争所不当争,弃所不当弃。蒋廷黻提醒国人,虽然同样是西方侵略势力,但是从海上来的一路其要求主要是通商;而从陆上来的一路,其目的则主要在侵占领土。要求通商与侵占领土两者的利害轻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由于俄人外交,两面三刀、威逼利诱的诡谲手法,则使清朝权贵屡屡上当。蒋廷黻非常痛惜地说:“回顾咸丰年间的外交,实在令人寒心。英、法诸国所要求的是加通商口岸、派公使驻京;俄国所要求的是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数十万方里的土地,利害轻重,不言可知。而俄国仅靠木哩斐岳辐及伊格那提业幅二人的手段就达到目的。英法反费了三年的外交和战争始算成功。缘故是中国人彼时的昧于大势和俄人对付中国的得法。”“识世知彼”也是蒋廷黻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重要尺度之一。对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与琦善,蒋氏的评论是颇为独特的,他敢于批评林则徐这位禁烟的民族英雄,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琦善这个一般史论目为妥协求和的庸吏。蒋氏为什么要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细致分辨,可知蒋氏批评与肯定很重要的、或主要的立足点是是否识世知彼。“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但林则徐对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琦善的立脚点根本与林文忠不同。琦善对于英人的军备切实调查了一番,觉得他们的‘船坚炮利’实在可怕,这是琦善的‘知彼’工夫。”琦善认为,中国当时的军事设备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大海和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统率军事者皆文臣,只会纸上谈兵。“林文忠对于中外强弱的意见完全与琦善相反。谁是谁非,现代的人应该不难决定了。”
三、国际平等,开放通商
蒋廷黻与一般近代史家不同,他不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目的出发,为了配合宣传而无条件地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来维护古人和今人排外的一切态度和措施。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不是一个狭隘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他相信近代国际平等的原则和开放通商的交往是根本有利于落后国家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应当共同遵守的。
蒋廷黻十分重视中俄关系史的研究,他对在中俄关系史上具有极不平常地位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来龙去脉作过详尽细致的探讨和描述,其点睛之笔正是国际平等、自由通商。他说:“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可解释尼布楚外交成绩的大部分。中国外交史上的大成绩是由平等对待及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不是从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传统中得来的。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但是,尼布楚条约不过是个特例,照中国的政治观念,尤其自南宋以后,总以天朝自居,“一统无外,万邦来廷”。根本否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所谓通商,就是进贡。凡来通商的无不尊中国为上国。在藩属方面,他们进贡以表示其恭顺;在中国方面,许其贸易,并不因为利其货品或税收,“不过因而羁縻之而已”,如果蕃邦不恭顺,中国就“停市”。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在接待英国使团上表现十分明显。蒋廷黻认为:马氏的外交失败就是由于中西邦交观念之不相容。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这也是十九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应适时改变自己的旧体制以适应此世界潮流,参与世界生活。中国大臣中,谁能及早接近这一要求,谁就是识时务者,就能得到蒋廷黻的称赞。鸦片战争期间,琦善虽然在他的奏折内也有“谕英夷”、“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蒋说: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可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然而,持琦善这种态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琦善的态度也未必是自觉的。故蒋廷黻指出:“可惜道咸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方不可。”
蒋廷黻研究外交史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了破除与国际平等、开埠通商相对立的妄自尊大、闭关自守的心理定势。在他的著述中,有谴责、有讥讽、有痛惜、有赞誉,可谓用心良苦。由于他的这一信念是自觉和坚定的,所以他在评论条约、人物和某种历史现象时就常常闪现出独到的见地和卓识。直到如今,在中国近代史著作中,是极少有人敢去肯定不平等条约还有积极意义的。可在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中,《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并不全是那样狰狞可惧的锁链。他说这两个条约,“条款虽很多,主要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他并没把英、法打开中国门户看做是件绝对的坏事。他认为开放通商,密切与西洋的关系是必要的,关键是要自己振作。他称赞奕訢和文祥这些人有眼光,绝不留恋过去的闭关时代。他们能大着胆子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蒋廷黻说:“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20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但是,近代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在压迫之下,首要的任务当然是反侵略、反控制、反压迫。蒋廷黻认为反侵略、反控制、反压迫固然必要,不过这不能取代全部的对外交往。资本帝国主义有其侵略、压迫的一面,然而也有其推动物质、技术、资本、文化交流的一面,不能只避其害而不取其利。“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
四、整体现代化
贯通蒋廷黻中国外交史和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更重要、更根本的理念是近代化(现代化),是整体的近代化或彻底的近代化。所谓整体的、彻底的近代化,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从目标来说,是要建设国际水平的、富强的、“能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从结构来说,是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统一体,物质是指科学指导下的机械生产和交通系统,制度是指民主宪政和科学的管理体制,精神是指全体国民具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不为个人的名利而危害国家的利益,不为家乡和家族的利益而损害国家整体的利益,整个国家是团结的、凝聚的;从实现近代化的途径来说,蒋廷黻遵循的是孙中山的道路,即军政、训政、宪政的道路,他认为训政是一个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过渡时期,他主张通过训政时期的中央集权,提倡科学,发展工业和交通,推广近代教育以培育人才,改变士大夫的人生观,最终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领导和努力,带动人民走上近代化的轨道;从学习的国际榜样来说,中国要完成近代化的大业,当然要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和民主自由思想,但是蒋认为中国的近代化要从中国自己的国情出发,应该更注重学习与中国情况相近的国家的经验,所以,他的榜样,不是英、美,不是法、德,而是日本、俄国和土耳其,因此,蒋重视中央集权和政治领袖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他十分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他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希望中国能“火速”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