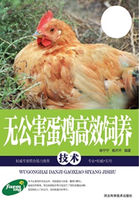二、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形成
20世纪初期,以梁启超为代表,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对旧史学的批判潮流。邓实、汪荣宝、陈黻宸、刘师培等许多人都发表文章,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旧史学,“新史学”思潮也逐渐形成。
在“新史学”思潮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多的言论还是限于批判“君史”建立“民史”的范围里,他们为“新史学”开出的方案是,改记载帝王将相为主为记载民众为主,改一家一姓为主的历史撰述为“民史”、“国史”为主的历史撰述。“新史学”强调“民史”的要求和背后,显然是与当时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和救亡图强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从长远的眼光看,建立“新史学”仅仅改“君史”为“民史”是远远不够的,传统史学也并非就是帝王家谱。全盘否定旧史学作为革命口号提出来是一回事,从学术层面真正构建中国的“新史学”则是远比批判宣言更为复杂的另一回事。对旧史学的批判为中国史学转型开辟了道路,建设“新史学”仍然任重而道远。
“新史学”思潮在这里是一个较为笼统的称谓,其主要特点是批判旧史学、崇信进化史观、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突出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等史学的社会功能、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等。由于对“新史学”基本宗旨的认同,使得许多人投入其中而形成了这一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有深远影响的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因此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意义。如果对“新史学”思潮所涉及的人物、学术观点、政治倾向、学术成果等方面进行考察,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新史学”思潮在当时表现出的复杂性也多有表现。
“新史学”的倡议获得认同,并不等于人们在所有的观点上都一致。譬如,身为改良派的梁启超所坚持的是“大民族主义”,他说:“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蹠于五大陆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也。”这与主张“排满革命”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民族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反映在史学中,怎样看待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作用,尤其是如何看待满族统治者及清朝的历史地位,双方都存在着争议。与此相关的历史纪年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主张以孔子纪年,而刘师培在排满革命高涨的1903年发表《黄帝纪元论》一文中强调,“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主张黄帝纪年,既否定以历朝君主年号纪年,也否定以孔子纪年。另如,国粹派多数人的政治倾向是反满排满,与梁启超、夏曾佑等改良派大异其趣。但是,推崇进化史观、主张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学问、批判旧史学为帝王之家谱、反对“君史”、提倡“民史”等作法,与梁启超《新史学》的观点并无二致,他们在运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一点上也是相同的。
如此看来,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其实涵盖了许多不同政治取向、却都看重史学的社会功能、要求改变旧史学面貌的多数进步学人。包括国粹派在内,他们在史学上的倡议、宣传、研究、著述,尽管因各种原因存在着观点上的歧义,然而异中有同,他们在“新史学”总的目标上是基本一致的,都可以视作是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如果从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史学发展的新动向、新观点、新成果,大多与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的宗旨相关联,“新史学”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之故,不论那些既批判旧史学又致力于宣传“新史学”的人们的政治取向如何,只要他们大致认同“新史学”的基本宗旨,均可以将他们纳入“新史学”思潮的整体范围中,应该从总体上把握“新史学”思潮的走向,进而分析其对于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三、20世纪初期“新史学”思潮的学术建树
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是以史学革命宣言式的态势而出现的,表现出了强烈的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意识。但是这并不是说,“新史学”思潮就仅仅是批判旧史学的言辞、建立“新史学”的设想等口号或提示性内容。对旧史学的批判已经成为“新史学”的标志性特征,“新史学”对中国史学转型的建设性意义往往被其批判锋芒所遮掩。“新史学”思潮在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多为人们所重视。在历史研究硕果丰厚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所带来的在具体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并不十分引人注目,况且,“新史学”破旧立新的突出特征所产生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具体研究层面的成果价值,然而,“新史学”思潮之初,相关学人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研究的努力与尝试,及其获得的成果,尽管有着许多不足,却仍然值得重视。
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就是该撰史计划中的“叙论”部分,只是最终未能撰成全书。还是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之前,章太炎在1900年手抄本《訄书》中所增第五十三篇《哀清史》后就有《中国通史略例》一文,说明他已经开始考虑撰述中国通史。以撰述中国通史作为“新史学”具体研究的最初尝试,章太炎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他的意图:“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两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显然,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审视历史进化之迹象并鼓舞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其基本用意。章太炎认为,通史是实现新的修史方案的理想的史书体裁,希望新型的《中国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说明他仍然看重古代史学的可借鉴之处。此外,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还流露出比较西方史学论述中国史学(通史)的意识。提出撰写新中国史计划的还有陈黻宸,他在1902年《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一文中建议:“自五帝始,下迄于今,条其纲目,为之次第,作表八、录十、传十二。”他的计划是:“十录十二列传,皆先详中国,而以邻国附之,与八表并列,盖庶乎亘古今统内外而无愧于史界中一作者言矣。”
“新史学”所带来的撰述新型中国史的热潮,不仅有梁启超、章太炎、陈黻宸等人写出了相应“叙论”或撰史方案,还有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马叙伦的《史学总论》、黄节的《黄史》等著述的出版。章太炎、梁启超曾发愤撰述中国通史,但进展并不顺利。即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也属未完成之作,前者写至隋,后者仅及西周之末。陈黻宸完成于1913年的《中国通史》(20卷)与他在1902年发表的《独史》中所计划的撰述中国史的内容设计亦相去甚远。“新史学”思潮以指斥旧史学为帝王家谱、有君史无民史、宣传史学的爱国意义和社会功能为发端,伴随于激烈批判旧史学的言辞,如何建设“新史学”这一更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稍能表现“新史学”实施步骤的主要是撰写新型中国通史的讨论和筹划,并且在三两年后即撰写出了几部教科书式的新型中国史书,而此若干建设“新史学”的实绩也未能得到后人的充分重视。平心而论,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思潮的总体走向是对旧史学的“破坏”和“新史学”的建设,实际表现为“破坏”大于建设,但是全面看待“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其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等“建设”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亦不应被忽视,他们撰述新型中国史的努力,对开创后来的中国史研究的新局面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学术层面言之,“新史学”带给近现代中国史学有价值的遗产,是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努力和撰述新型中国通史的尝试。梁启超在20世纪初关于“新史学”的一系列论述,已经涉及包括历史观、历史认识论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迥异于传统史学的理论阐述,使中国的“新史学”开始具备了现代史学的内涵和特色,也使“新史学”思潮的学术生命力得以不断延续。可贵的是,梁启超一直没有中止在这方面的探索。“新史学”思潮在随后几年与复古思潮的较量中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在五四时期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著述为标志,“新史学”以更为全面和成熟的理论建树再次风靡一时,其影响所及断续持至今日。
[作者简介: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