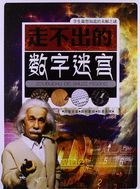史革新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如果以嘉道时期为界把清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那么在前期是汉盛宋衰;而在后期,即晚清时期,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合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一、“汉宋鼎峙”的新局面:晚清宋学家对汉学的批判
清代汉学一直把宋学当成主要的批评对象。从清初的顾炎武、毛奇龄、胡渭、阎若璩,到后来的戴震、阮元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宋学展开了批评。他们的批评有不少切中宋学的流弊要害,突破了理学的一些思想教条,反映出广大士人对理学的不满和理学衰落的趋势。然而,有些批评则是属于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其中不乏偏激语言和不实之词。
嘉道时期,汉学流弊充分暴露出来,引起一些文人学士的不满。汉学的衰败给程朱理学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理学派学者在振兴宋学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正面宣扬、阐发程、朱的思想观点,一是发起学术争端,批判非程、朱的学术派别。汉学就是理学家们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说到这个时期的汉、宋之争,就不能不提到桐城派学者方东树和他的《汉学商兑》。
《汉学商克》是一部学术论辩著作,其宗旨可以概括为“辟汉扬宋”四个字。作者在该书原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
他所说的“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指的是《国朝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把儒家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崇汉抑宋,标立门户。这自然成为激发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的一个直接动因。《汉学商兑》仿朱熹《杂学辨》体例,全面检讨了汉宋学论辩的问题,如学术来源、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大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批驳。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汉学的批判,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迈前人,可谓是宋学对汉学的一次总结性清算。该书点名批评的学者有30余名,从清初的名士到嘉道时期的儒宗,主要的汉学名流大都包括在内,如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同、万斯大、惠士奇、惠栋、戴震、钱大昕、朱彝尊、张惠言、凌廷堪、江藩、钱大昭、臧琳、汪中、孙星衍、阮元、焦循,以及黄宗羲、颜元、李塨等以及宋儒黄震、明儒杨慎等。涉及人数之众非一般批评汉学的理学著述可比肩。
就内容而言,针对胡渭《易图明辨》提出宋儒尊崇的《河图》、《洛书》出于五代道士的观点和毛奇龄《辨道论》斥责宋儒为“居道观之羽流黄冠”的“道士”的说法,方东树在书中做了辩驳,认为,理学所讲之“道”与道教之“道”的涵义根本不同。程、朱所说之“道”是“圣人之道”,“凡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大学之道,何莫非圣学也”,程、朱诸儒则是发扬“圣人之道”的功臣。他说:“盖自汉儒分道为一家,而道之正名实体大用皆不见。惟独董子、韩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经》、孔、孟之言而发明之,而圣学乃著。”说程、朱是“道士者流”,“非但诬而失是非之心,又将使来学视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非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之下也!”
方东树还就汉学家对宋儒关于“十六字心传”、“人心”、“道心”、“存理灭欲”、“格物穷理”、“养性存德”等观点的非议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些非议“鲁莽灭裂”,“徒乱圣人经义,贻误来学”。他不满戴震对程、朱“理欲”说的批判,反驳说:
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亦必民之情欲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而后可。若不问理,而于民之情欲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此大乱之道也。
在治学方法的问题上,方东树坚持程、朱的治学之道,认为训诂固然重要,但是不能迷信。因为古人训诂并不可靠,夹杂着穿凿附会、师心自用的解释。他说:由于迷信训诂,清代的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结果是步入歧途,损害了《六经》的“微言大义”。他主张训诂不离义理,“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
其次,《汉学商兑》带有极其明显的“尊朱卫道”色彩。
方东树高度评价程、朱在发扬孔孟儒学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孔孟之道自孟子后因受到异说的扰乱而长期被埋没,只是由于出了程、朱才重见光明。他在该书《重序》中强调:圣人之道“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他把程、朱比诸于孔子,指出:“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又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针对汉学家指责朱熹说理“杜其聪明,断以一师”,他起而为之辩护,认为朱熹“谆谆教人读汉魏诸儒注疏,文集中凡数十见,即《四子书集注》所采五十四家之言,何尝杜其聪明,断以一师”。汉学家的攻击“是不知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
再次,《汉学商兑》集中地揭露了汉学末流的弊病。
方东树把汉学的弊病概括为“六蔽”,具体是: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如商韩之用法。……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
他对汉学流弊的指摘,主要是从维护宋学的立场上来说的,其中不乏门户之见,然而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如他批评汉学搞繁琐考证,致使士人埋头故纸堆,不关心社会现实和国事民情,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这些批评都切中汉学流弊的要害,颇有见地。总之,在方东树笔下的汉学不仅学理荒诞无稽,无复可取之处,而且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它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杨墨佛老”。他在书中写道:“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是率天下而从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说横议,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
作为晚清宋学营垒的主将,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用程朱理学的观点尖锐而全面地批评了汉学,大胆地揭露了汉学末流的种种弊端,这在当时学界不能不引起很大震撼。因为汉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考据之风深深地影响了学林士子,不少人已经深溺此道而不能自拔。在汉学余威尚炽的情况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树起程、朱的旗帜,批判汉学,这对那些醉心于考据学的人来说无异于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就打破汉学对学界的禁锢,破除对汉学的迷信这点而言,《汉学商兑》的确给学界带来清新之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宋学诸儒不乏微词,惟独对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赞不绝口,评价道:“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于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著作刊行后,不仅使究心于宋学的学者受到鼓舞,而且感染了不少原来对程朱理学抱有成见的士人,使他们“幡然悔悟”,归于“正学”。他们称赞方氏及其著作是“真吾道干城”,“实为南宋以来未有之书,真朱子功臣也”,“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方东树虽是古文家,但在中年以后专治理学,标榜程、朱,俨然一派理学家气象。这对后来桐城派学人产生了影响,使不少古文辞学高手转攻理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有人说:“然桐城自东树后,学者多务理学云。”
然而,《汉学商兑》也是一部带有严重缺陷的著作,作者采取了把对方完全否定的极端化的批评方法,有“矫枉过正”之弊。它批评汉学末流的弊端是对的,有的批评的确击中要害,但是把汉学称为“圣人之道”的“异端”,否定汉学是儒学的一个流派,完全抹杀汉学的研究成果就属于荒唐可笑了,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倒退。由此可见,方东树是从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汉学。
方东树之后,对汉学持批评态度的理学家大有人在,如邵懿辰、方宗诚等人。邵懿辰发表过许多抨击汉学的言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写的《仪宋堂记》。“仪宋”即“翼宋”之意,顾名思义,从文章篇名就可以看出他的“卫道”立场。他批评汉学之尖刻程度亦不亚于方东树。他在文中说:
今自乾隆嘉庆以来六七十年之间,学者以博为能,以复古为高,矜名而失实,务劳精疲神,钩考众家笺疏之说,下至官车制度、六书假借,碑碣盉鼎之铭识,而广为之证。凡传注之出于宋儒者,概弃不录,曰吾以崇汉而已。其徒相与号曰汉学。噫!此岂异夫立熟食大化之世,而追茹毛饮血之俗,挽碣石入海之河流,而反诸大龙门以上哉!不唯骂讥吐弃,于宋儒无毫发之损,亦且推崇奖许,于汉儒无涓埃之益。
方宗诚不仅对汉学末流进行了抨击,而且还批评了清代汉学的开创者顾炎武,认为,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立说偏宕”,不明理学产生流弊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明季学风的败坏是由于学人不懂得“穷理”,而非不知道“穷经”,这与顾炎武的观点正相反。他说:“惟程、朱数子之经学足以当之,若汉唐诸儒之注疏正义,其补于诠训者,因多其穿凿细碎而背理本者亦殊不少,不得谓‘经学即理学’。程、朱由《六经》而洞达本源,后世儒者得其微言而因不知止穷夫六经,诚不免堕于空疏之弊。然谓邪说禅学由是而起,则有不尽然者。禅学之病正由不肯穷理之故,非徒在于不穷经也。”他们的论说与方东树《汉学商兑》遥相呼应,共同上演了“汉宋鼎峙”的激烈一幕。
二、“汉宋合流”的学术趋势
在对待汉学的问题上,清代宋学派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为排汉主张,一为融汉主张。在晚清,这两种观点同时存在,只是各自的表现及影响有所不同。嘉道时期,由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鼓荡,理学中人以辟汉学为时尚,排汉观点占了上风;至同光年间,随着整个儒学内部的变化、调节,调和汉宋的观点逐渐取得优势而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趋势。道光时,理学名儒唐鉴写的《国朝学案小识》容纳了汉学家,体现出汉宋兼采的意向。唐氏以后,宋学派中持汉宋调和论者日益增多,终在同光年间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倾向。这个时期不少学宗理学的要人,如曾国藩、朱次琦、夏炘、徐桐、成孺、刘熙载等都持这种主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宋合流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用“孔门四科”的旗号化解汉、宋学的对立。
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汉学、宋学都看成孔门儒学的一部分,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都是达到圣贤境界的门径。曾国藩对“孔门四科”“缺一不可”的观点所作的阐述尤其明确,指出: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在他看来,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孔门中的一门具体学科,关注的侧重方面虽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有着共同性。“此四者缺一不可”便是对这种共同性的肯定。这种共同性就是汉、宋学相互融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