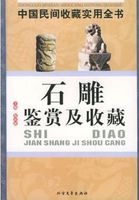其实,要反对观影状态与“梦”、“洞穴”、“镜子”状态之间的类比非常容易,因为即使能够在看电影的状态和那些状态之间找到某些相似之处,必定也可以找到更多的不相似之处。电影观众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嚼爆米花,可以相互交头接耳,可以在自己不喜欢那部电影的时候随时站起来走掉,可以对自己不喜欢的场面发嘘声喝倒彩。做梦的人、洞穴里的囚徒、镜子前面的婴儿和“缸中之脑”显然都无法做到这些。其次,被理论家们一再列举和引用的那些相似之处是否成立,本身也是非常有问题的。比如,据说电影观众和做梦者的一个相似之处是身体活动被抑制了。不错,人们不能跑来跑去地做梦,一般的电影观众也不会跑来跑去地看电影。问题是,电影观众为什么要跑来跑去地看电影呢?这样的类比有意义吗?做梦者的不运动和观众的不运动根本不是出于同样的“机制”,并且如果一位观众真想跑来跑去地看电影,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尽管这可能会招致其他观众的不满。再比如,麦茨说,“与日常生活中的活动相反,被传统虚构性电影导致的电影化状态的特征是一种降低觉醒状态、步入睡眠和做梦的方向的普遍倾向。当一个人没有睡够的时候,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比他看电影之前和之后都更有打瞌睡的危险。”然而,许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都处于高度兴奋的状态,使得人们“有打瞌睡的危险”、“降低觉醒状态”的,并不是所有电影,而是一些糟糕的电影。此外,如果张三在读电影理论著作的时候开始打瞌睡,是不是应该说这些电影理论也有了“梦元素”呢?
但是,当代电影理论为什么会把这些轻易就能驳倒的类比或者隐喻奉为经典,并在此后接踵而来的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视觉文化研究中一再重复和引用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因为各种“幻觉”可以帮助电影理论家轻松地解决关于电影的“大问题”。要是没有它们,那些问题将得不到“根本性的”回答。确实,博德里和麦茨都是雄心勃勃的理论家,他们想要解决的“大问题”就是电影为什么能够带来“快感”。用麦茨的话说,就是“观众为什么去电影院”。而通过在电影和幻觉家族成员之间建立联系,他们就找到了电影带来快感的根源——观众向婴儿的原初自恋阶段退化的满足,对幻象的沉迷,在自我与他人不分的原始的“统一体”幻觉中的狂喜。这个论证思路是一目了然的:
(1)退化性状态(梦、洞穴、镜子)造成的幻觉,满足了无意识中对原初阶段的统一性、完整性、自我与对象浑然不分的状态的本能渴望,因此,退化性状态中的幻觉产生快感;
(2)观影状态类似于这样或那样的退化性状态(根据观影状态与前述状态之间的“相似性”);
(3)因此,观影状态也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退化性幻觉;并且,由于(1),这样的幻觉是能带来快感的;
(4)因此,观看电影产生快感。博德里想要说明观众迷恋电影的“根源”,说明电影带来快感的最根本的原因。但奇怪的是,他不认为电影令人迷恋的原因存在于影像的内容或具体影片的故事之中,甚至不是通过考察某一类影片来探讨电影带来的快感。相反,他把观众获得的快感视为某种“装置”的产物,即一个包括银幕、观众、放映机在内的网络。也就是说,博德里是在观看状态本身当中找到了观众沉迷于电影的根源,而从不考虑他们看的是什么具体影片。在克里斯蒂安·麦茨那里,情况同样如此。麦茨明确拒绝通过对电影元素的分析,对技术、创作手段的分析来说明电影的效果和影响力:“另一条道路——我已经看到的并且已经走上的道路——就在于对电影的精神分析学内涵的知觉考察,它超越了任何具体的电影。”
至今,幻觉理论家们仍然津津乐道观众对电影的“原始的激情”、“本能的渴望”。我猜想,在电影理论世界之外的人,包括制作和发行电影、观看电影的人,如果听说存在着这样一种“本能的”、来自于原初阶段的对电影的普遍“渴望”,可能会瞠目结舌。显然,没有人出于“本能”而“渴望”一切电影。观众们对自己喜欢和讨厌的电影作品向来爱憎分明,他们的渴望和迷恋总是针对具体的电影作品,而不是对一个抽象的、全称的“电影”概念。正因为如此,一些电影导演才会成为票房“毒药”,一些影片才会在放映时门可罗雀。
其实,“观众为什么喜欢电影”这类问题,是貌似有意义的虚假问题,因为它隐含了如下全称判断:所有的观众喜欢所有的电影。正因为这样,支持幻觉论的电影理论家才会到人类普遍的深层心理结构中去寻找电影快感的源泉。然而,“所有观众喜欢所有电影”是一个明显错误的判断。并非所有观众都喜欢电影,观众也不会喜欢一切电影。想在人类的普遍本质、深层欲望当中找到电影的吸引力的根源,注定是徒劳无功的。研究者最好在具体的电影作品中、电影运作的方式中以及那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寻找某部电影作品或某种电影类型的吸引力。
此外,电影是人类自己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人类的产品。而各种退化性幻觉却不是——按照它们的定义,即便它们存在,它们也是被决定的,而不是人类自己所能够控制和支配的。也就是说,人们对电影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了解,比对退化性幻觉的了解要多得多,也要直接、容易得多。毕竟,电影作品、电影技术、社会文化和观众的身心状态等等都是可以直接观察和研究的对象,而各种幻觉和那些深层心理状态甚至不可能是“意识”的对象。它们不应当充当解释元素。观众为什么不活动,观众为什么会对某些电影手段(如视点镜头、平行蒙太奇等)产生特定反应,某些类型的电影在某些社会历史时期为什么会产生轰动效应,经典好莱坞电影为什么会发展为全球电影的主流形态……要解释这些电影现象,其实根本不需要诉诸退化性幻觉和那些神秘的理论性构造物。
2.“梦中梦”与“幻觉背后的幻觉”
前面已经提到,幻觉家族在电影理论中的第二个影响,是创造了越来越多元化的理论局面,并且推进越来越“深刻”的理论。这样或那样的幻觉,帮助不同的幻觉理论家找到了解释[所有]人类迷恋[所有]电影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使得他们确信,由于电影是通过迫使观众向婴儿阶段退化来满足他们的本能欲望,因此电影是“邪恶的”,观众需要得到“拯救”。为电影观众“揭示”这些导致退化的幻觉“装置”和状态,就成了电影理论家、电影批评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对于意识形态电影理论家来说,要批判的是“主体性幻觉”,即构成主体的阶级身份、种族身份等一切意识形态主体性特征的幻觉,以及产生它的退化性机制如“询唤”等过程,最终追溯到“镜子阶段”和观影状态的类比。对于女权主义理论家来说,要批判的是煽动窥淫癖和恋物癖的机制,包括想象性认同和受虐狂。而对于视觉文化研究者来说,需要揭示的是一切关于“统一体”的幻觉,观众感到的任何统一、融贯的东西都是假象,而根本原因同样是向原初阶段的主体和对象浑然不分的“统一”状态的退化……你可以看到,对于形形色色的幻觉理论家来说,形形色色的退化性幻觉的存在,以及电影(连同它的“装置”)对观众的形形色色的“操纵”、“迫害”和“压制”,都建立在“观影状态”与“梦状态”、“洞穴状态”和“镜子阶段的婴儿状态”之间所谓的“惊人的相似”之上。
电影理论家并不只是依靠一些已经被一再证伪的精神分析学假说来“揭示”幻觉,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幻觉。一些电影理论家还利用相对新鲜的哲学资源来进一步创造关于幻觉的深刻理论,尽管往往是误用。例如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缸中之脑”这个思想实验要求我们想象如下可能性:试想象我们皆是“缸中之脑”(brains in a vat),这些大脑都被某个(某些)“邪恶”科学家放进一个盛有维持大脑存活的营养液的大钵中,而大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这台超级计算机使得所有“缸中之脑”经历着和常人一样的经验,但这些“缸中之脑”所经验到的“整个世界”,其实是这台超级计算机制造出来的集体幻觉。
一些善于联想的电影研究者立刻把这一设想与电影、虚拟技术、互联网等等真实世界中的现象联系起来:“电影,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在这样一部人类歇斯底里和自我毁灭的历史中充任了一个重要的阶段性和历史性的角色,它是一种幻觉论神话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影院机制、观影行为和体验就已在某种程序上带有了‘缸中之脑’的色彩。”
在这样的理论家眼里,“缸中之脑”正好具象化了他们对现代技术社会的构想:层层叠叠的幻觉、噩梦般地受欺骗、被操纵的处境、永无休止的谎言。于是,拥抱“幻觉论”的学者们像《黑客帝国》中的墨菲斯那样深沉地发问:你如何担保自己不是处于这样的境地之中?
《黑客帝国》只是一个虚构性作品,而电影理论和文化研究都宣称自己并不属于艺术性虚构的领域,而是在对“实在”——并且是最真实的“实在”——进行断言。这种“缸中之脑电影理论版”,也许会让普特南本人哑口无言。普特南恰恰认为,“缸中之脑”这种典型的怀疑论假设是荒谬的,必须予以驳斥。反过来,如果一个认识论不能够成功地驳斥这类假设,这个认识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在《理性、真理和历史》一书中,普特南提出“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是为了对“形而上学实在论”予以驳斥。在他看来,形而上学实在论之所以不可接受,正因为它无法有效地反驳“缸中之脑”这样的荒谬假说。普特南指出了导致这种怀疑论的一个原因——“神秘的指称论”,即错误地认为词语、思维符号或心灵表象与它们所指称的东西之间具有固有的、内在的联系。并且,他指出了“缸中之脑”假设不可能成功,除非它预设了错误的前提,否则它将会是“自我推翻的”。在“缸中之脑”的状态下,你根本无法有意义地指称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