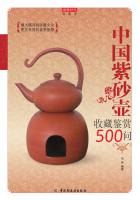·Erika Fischer-Lichte著
·种洁、周靖波译
戏剧:文学的抑或剧场的?
在西方,戏剧基本上是以书面戏剧与口头戏剧之间的张力为特征。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戏剧究竟应被视为文学领域的书面作品还是剧场领域的口头作品,一直众说纷纭。因为亚里士多德将文学作品的戏剧与其在剧场中的表演截然分开,所以当代戏剧理论家总是将戏剧视为“多媒体文本”。鉴于文学理论向来忽视表演维度,所以这种方法也是可行的;但是,基于这种方法而得出的某些结论则未必完全正确。
这是因为,从媒介和符号两方面看,戏剧的表演及其文学文本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戏剧及其固定的书面文本,属于单一媒介文本;而表演则至少是在两种媒介——舞台与演员——之间进行交流,属于多媒体文本。文学文本只包含性质相同的语言/书写符号,甚至于复杂符号(比如角色与情节)也只是在语言/书写符号的组合中产生;而表演则由多种性质相异的符号组成,既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非语言的(如摹仿、手势、空间关系、面具、服装、小道具、布景、音响、音乐等)。因此,戏剧的文学文本属于书面形态,戏剧的表演则属于口头形态。
戏剧及其表演在媒介及符号上的这些重要区别对于戏剧对白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戏剧对白——尽管它被置于固定的文学文本中——仍主要代表面对面的互动,从定义上来说,它应该属于口头形态的范围。其次,对白的语言构成可以相去甚远,其差异完全可以达到极端的地步,既可能是妙笔生花的华章,也可能是粗野无文的口语。因此,书面形态与口头形态之间的张力既有构成性,又有能产性,而且它在戏剧的文学文本及其表演的戏剧对白中都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的观点就是从戏剧对白的这个独有特性中产生的。戏剧对白是一个独特的意义生产系统,该系统是由书面形式与口述形式之间特殊的更迭关系构成的。
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提供更为有趣且更加多样性功能的恰恰是表演中的戏剧对白。但是,由于这种功能更多地是由书面形态的戏剧对白所产生,所以,有必要事先系统地介绍一下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的书面戏剧对话类型。
文学性戏剧对白
所有的书面戏剧对白(亦即完整的戏剧文本)都被编织进了“主文本”与“副文本”之中。副文本可能仅限于给出说话人的名字——从而在谁拥有发言权方面发生变化——或延伸到规定一些细节信息,如说话人和听者的声调、摹仿动作、手势、体位及动作。在某些地方,它也可以扩展为有相当篇幅的独立的描写性文本。因此,每个文学性戏剧对白都由两种不同的文本系统构成(它们之间的冲突可以产生特定的意义):一是构成角色话语的系统,一是表示人物实际对话以外的行为的系统。因此,我们必须根据两种文本系统在意义构成上所起作用的不同,对文学性戏剧对白做进一步的区分。鉴于这类的规则暗含的可能性无比复杂,我们必须对以下两种情况做出基本区分:一种是对话的次文本仅限于给出说话者的姓名,该处的意义只有通过角色的台词文本,通过归属于他们名下的动作才能产生;第二种是除了列举说话者的姓名外,对话中还包含了一个合理扩展的次文本,它提供了构成意义的台词里所缺失的信息,而这个信息中的意义只有通过台词文本与次文本之间各种具体的矛盾对立的方式才能产生(这已经超出了归属于说话者名下的台词的范围)。
台词文本的主导地位因戏剧类型的不同而各异。在莎士比亚戏剧、法国和德国古典戏剧以及18世纪末的感伤剧中,这一主导地位的表现形式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差异。
例如在18世纪末的感伤剧中,虽然也有面对面的互动,却没有指示口头形态的其他特征。其中,对于对话中的发话方、听者和情境都没有明确指示。但其对话模型乃是由不同的诗系统所建构的,在这些系统中,反映、去情境化、密集信息、精巧性都占据支配地位。直接交流的情境就是通过精巧的书面媒介展现出来的。
在德国古典戏剧中,台词文本的主导性所起到的作用明显不同。在这里,话轮转换系统得到了台词文本自身的承认。如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1787),虽然所有的对话伙伴都以同样的风格说话(亦即无法根据话语的个人风格区别彼此),但发话者与回应者的交互转换十分明显,远甚于台词文本中姓名的更换,所以每一处为了表示说话顺序和说明话轮转换系统而指示的姓名都可以省却。因为这些都很容易从文本当中看出来。
一方面,台词的特点可以从它们之间的相互牵连、对语境的依存关系、表达能力和情感特征表现出来。第二文本通常是用来描述直接交流情境中非常典型的各种非语言符号,然而,在第二文本缺失的情况下,对话仍然可以进行。不仅如此,这时的所有信息都由以信息丰富、简要、复杂、精巧为特征,以具体的诗体模式为基础的对话的话语文本所提供。
第二种对白类型的意义是通过台词文本与第二文本的相互干预建构的,它总是指向比第一种更强的直接交流情形,因为在对话过程中,它明白无误地强调着对话伙伴在第二文本中使用的副语言学的、模拟的、空间关系符号。因为此处的指向非语言符号的第二文本中的语言学符号,与台词文本中的语言学符号相关联,所以其意义也只能取决于对话。要实现这一点,其方式却不是仅仅让对白文本占据绝对优势。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确立一种切实有效的系统化方法,那么将我们的讨论限制在两极之间是明智的。要么台词文本在对白意义的建构中比第二文本作出更多的贡献,要么第二文本对台词文本的意义起到制约作用。两种状况都存在:或是受到台词文本的绝对主导性的制约,或是受到第二文本的绝对主导性的制约(正如贝克特的《无词的戏》和汉德克的《未成年人想当监护人》中的情形那样)。
在18世纪的德国市民悲剧中,第二文本是通过指涉人物行为的舞台指示,作为戏剧对白的有机组成部分系统地组合而成的。例如在莱辛的《爱米丽娅·迦洛蒂》(1772)中,台词文本与第二文本相互补充,通过这种交替式的相互参照建构起对白的意义。第二文本可以通过列举摹仿动作和手势来强化那些表现在选词造句当中的情感,还可以通过对蓄意的动作的描写来填补对白文本中的空白。即便如此,话语文本还是被认为远比第二文本更加重要,因为不仅最重要的信息都是由它传播的,而且人物的情感也主要是通过它具体而明确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的。
与前两个例子相比,书面文本与口头表达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降低,但还不能因此就说这里出现了直接交流情境的简单(书面)符号。这里的主要特征是自发性、参与性、情境的干扰、表现性、情感和过程的紧张感。这些特征主要都是通过台词文本和第二文本的相互干扰而形成的。它们实现了创造真实幻觉(亦即直接交流情境)的美学纲领。
另一方面,复杂性、缜密性和建构性等特点也不能被忽略。它们指向由人类的理性原则所决定的角色的思想,但角色的感情则属于自然现象,通过自然的身体表达出来。与法国和德国的古典主义戏剧相比,此处书面文本与口头文本之间的紧张程度大大降低,因此它将注意力明确引向了资产阶级价值观。
在自然主义戏剧中,这种紧张关系实际上被大大减弱,以至于人们可以谈及对直接交流情境的摹仿(以及相应的标记)。这里经常出现的是,第二文本中描写的角色行为与台词文本中角色表演的话语行动不相符。台词文本中的语言学符号与第二文本中所包含的非语言符号之间明显处于相互矛盾状态。例如,当角色语言表示“冷漠”或至少是“不感兴趣”时,角色的非语言行动却显得感情十分投入,因此就出现了第二文本的意义与台词文本相冲突的状况。
在18世纪德国市民悲剧中,第二文本的意义仅在于加强和补充主要文本,或使之具体化,它可以(在泛化或稀释的意义上)对主要文本的意义进行修正,甚至与之直接对立。人们可以将台词文本与第二文本之间的关系概括为互补、具体化、修饰(强化或淡化)或对立。在任何情况下,戏剧对白的意义都只能通过两个文本系统之间的具体关系所导致的结果加以建构。
第二文本所承载的意义制约着台词文本的意义。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前者指向在台词文本中未曾道破的角色的真实情感和内心想法。只有通过第二文本才能推断角色的对白策略,仅仅依据台词文本则不可能完全掌握这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