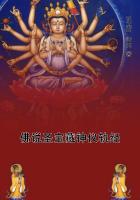四、建构完成后的隐忧:一元化初露端倪
总体来说,1930到1940年代的中国电影在动荡的时代、纷繁的社会文化、尖锐对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片企业艰难的商业生存交织争夺的复杂语境下,保持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态势,呈现出十分丰富的面貌和形态。除了我们所关注的现实主义电影、“软性电影”,还有大量的其他类型的商业电影。现实主义电影自身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的建构并始终呈现开放多元的风貌。即便在1936年5月提出“国防电影”口号后进行的创作方法讨论中也明确地强调了除了要在题材和内容上应强调反帝的任务外,在创作方法创作风格上要坚持现实主义与多种艺术方法并存,主张风格样式的多样化,要求创作者深入现实生活,避免创作的表面化和口号化。在艰难时世里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峰。但在这高峰背后,却已经潜藏着在不久之后便将中国电影引向“一元化”的封闭发展道路的致命因素。
这一因素,便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艺、对电影的强势介入和强力干预。
这一端倪,首先出现在1920年代末期“四·一二”事变导致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分裂并走向武装对抗的时候。文化上的“围剿”与对抗的深入以及由此而来的全社会的“政治化”,宣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启的思想解放和思想自由时期的结束。对此后的中国文艺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的“革命文学论争”就发生在此时。
这场发生在鲁迅、茅盾等人和部分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之间的新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涉及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形势的认识和估价,以及革命文学的建设等内容。尤其是在文学观念上,双方对题材、世界观与创作、文学与生活、文学与政治等重大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这场论争虽然以双方都摒弃意气用事的分歧而共同走向左翼文艺运动而结束。但在论争中,创造社和太阳社一方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对文学要更好适应无产阶级单独领导革命的时代的要求,以及他们忽视艺术技巧,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它只是宣传阶级意识的武器等观点却并未因论争的平息而退场,反而在此后的左翼文艺运动中进一步走向了极端化。在1932年,身为共产党文艺领导者的瞿秋白在他的《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更是竭力强调了文艺的阶级性和党派性,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甚至认为“文艺……都是煽动和宣传”,“永远的,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
在极为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政治背景下发生的左翼文艺运动形成了坚持作家与战士的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革命政党的组织领导,以及不断提高为人民群众和革命事业服务的自觉性的战斗传统。它将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将它的工具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对文艺的强力介入。
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分支,电影,尤其是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都遵从于左翼文艺的指引。所以在它来说,“精神”和“功能”仍然是它的主要目标,而艺术和其他因素,如果与这一目标发生冲突,都是必须加以批判和抛弃的。发生在1930年代的对“软性电影论”的斗争就是如此。
这场批判多过讨论的“斗争”涉及了电影的服务对象、题材选择、形式与内容、艺术与政治、艺术的倾向性等若干理论和创作问题。因为认定当时的中国电影“走错了路径”,认定“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决不是微弱新生的中国影业所能单独打倒消灭的”;不满于中国电影因“被利用”而“走入了一条新的歧途”,“放着纯正的艺术不理,而去采用什么主义,什么化,什么派”,“好端端的银幕,无端给这么多主义盘踞着,大家互相占取宣传的地方”;认为“影艺是沿着兴味而艺术,由艺术而技巧的途径走的”,刘呐鸥、黄嘉谟、穆时英等提出了“美的观照论”、“艺术快感论”、“形式内容统一论”、“纯粹电影题材论”等“软性”电影观点。客观地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下,他们的这种反对将电影当做政治工具,强调电影的艺术性,认定电影就应当是“软片”,“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的主张是十分的“不合时宜”。所以甫一露头便遭到左翼电影人的迎头痛击。但痛击过后,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刘呐鸥他们的主张中的合理内容。他们对电影的艺术性的思考和对电影艺术表现手法的研究也成了被和着脏水一起倒掉的婴儿。
在左翼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中虽然强调文艺要在革命政党的组织领导下,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但真正将这一点完全做到的,要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和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艺模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文艺整风运动。运动中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不符合革命要求的现象都进行了批判和清算。经过整风,“工农兵文艺”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主流甚至是唯一形态。
“延安文艺模式”下的解放区文艺有着完全不同于“五四”以来的各种文艺运动的鲜明历史特征。在这里,文艺作为整个革命运动的直接组成部分,是在革命政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创作的。“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和“革命战争”终于在实际中完全结合起来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都已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这一模式下的解放区文艺创作也有着不同于“国统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特色。在主题和题材内容上,“国统区”革命现实主义几乎都以揭露和批判现实社会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和挣扎为主。而解放区则以“主要写光明”的歌颂为主,出现了一大批表现工农兵的革命斗争和翻身做主的新生活,歌颂现实的伟大变革的“颂歌”型作品。在人物形象上,不同于“国统区”革命现实主义对市民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塑造,解放区文艺中大都是带着新时代精神风貌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和革命干部。在文艺的大众化道路上,解放区文艺也走得更远,更深。工农兵群众直接参与了文艺创作,在改造旧的民间形式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文艺形式不断涌现。在文艺评价标准和方式上,解放区明确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方式和在整风运动中已时有发生的用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代替文艺批评的作风也与“国统区”大有区别。
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影响的扩大和共产党在进步文艺运动中的控制力的逐步增强,“延安文艺模式”也开始对“国统区”文艺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其典型例证便是对胡风的批判。
19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得把“延安文艺模式”在全国范围推行的愿景逐步变成可行的现实。随着何其芳、刘白羽等人被中共中央派至重庆介绍与贯彻文艺座谈会及《讲话》的精神,随着延安文艺思想逐步成为左翼文艺人士分析文艺界形势、确立行动方向及安排工作步骤和方法的基准,左翼文艺界此时也意识到,在“长期抗日文艺统一战线运动中,我们忽略了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坚持”,“不自觉地削弱了我们自己的阶级立场”,“多少松懈了领导思想前进的责任,表现了软弱与无能”;现在,我们“再不应回避或缄默”,要“从思想问题出发”,来“澄清一切混乱的状态”。而在1949年之前,除了外部斗争,左翼文艺内部的话语分歧,主要便是以胡风为代表的一系列文艺观念,与以周扬为代表的“正统”的文艺思想间的冲突。在《讲话》成为左翼文艺界在国统区的行动纲领之后,彻底清除胡风派文艺思想这一“理论杂质”的内部影响,成了左翼文艺界建设“文艺新方向”的必然之举。
于是,对胡风关于“民族形式”的问题以及后来出现的“主观战斗精神”等问题的文艺论争开始演变为“延安式”的政治批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艺工作领导者们专门召开座谈会对他进行批判,将问题定性为对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胡风本人更被周恩来提出两个“忠告”:“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而在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的批判中更是第一次出现了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胡风小集团”的说法。虽然由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批判暂告一段落。但在这次批判中出现的政治运动式的文艺批判方式却清楚地标明了文艺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方向下,文艺,包括电影都将必然会走向“一元化”的封闭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