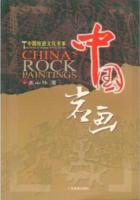人,是现实世界中最富有活态性的存在物。在叙述艺术中,以生命力为表现特征的“人物”则是最活跃的构成要素,占据着故事世界的中心位置。亨利·詹姆斯说:“除了事件的决定者,人物还能是什么?除了任务的说明者,事件还能是什么?”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犹如坐在一个跷跷板两端的游戏者,二者此起彼伏,相互作用,共同促使情节的运动和变化。可以这样认为:“唯有事件和存在者(人物)共同存在,才有故事可言。”人物是故事中的“行为者”或“行动者”,经常以一种积极主动或消极被动的运动状态出现,并且,他的运动变化能够构成或促进情节嬗变的过程。一般来说,人物是故事世界中“实在”或“确有”的人: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英雄、懦夫、朋友、敌人等等。但在某些作品中,则指“非人”的实体,是用拟人化手法塑造的,如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和魔鬼,寓言、童话中的动物和植物,现代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等。
动画电影的人物是丰富而灵动的,其中有人类,有动物,有植物,有高山,有河流……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汇聚在此担任角色发挥作用,例如动画影片《马达加斯加》中,就有四只企鹅扮演了坏角色,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情节的发展。又如在《幽灵公主》中,各种精灵、神灵作为非人类人物频频出现,给影片增添了神秘的色彩。本章将就动画电影中的人物类型、角色功能以及组合的方式进行基本阐述。
第一节动画电影人物类型
与真人电影比较而言,动画电影中人物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表现主体类型的广泛性,现实中的人类、自然中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虚幻中的神仙精灵……不论真人实体还是非人实体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像中国的《神笔马良》、《愚人买鞋》、《摔香炉》,日本的《再见萤火虫》、《攻克机动队——无罪》,韩国的《五岁庵》,美国的《半梦半醒的人生》、《弱智与丧门星玩转美国》等是以人类为表现主体的影片;而像《三十六个字》、《快乐数字》、《玩具总动员》等影片则是以非生命实体为表现主体的。由于在前一章中曾从动画电影故事表现内容的角度做过分类讨论,这里就不再对人物的表现主体类型做细分化论述,而是借鉴叙事学中对人物分析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根据动画电影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类型进行探讨。
“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是英国小说美学家福特斯论述小说人物形象的术语。“扁形人物”又译为“扁平人物”或“平面人物”,指性格单一的人物。文学理论家也称之为“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所谓类型,是指17世纪琼森提出的“某种特别突出的气质”;至于“漫画人物”,则是说其特点犹如漫画般易于被人观察和把握。“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被创造出来”。他们只具备一种气质,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表达”,“用一个简单句子描绘殆尽”,例如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密考伯太太,其标识语是“我永远不会遗弃密考伯先生”。福斯特对扁形人物褒贬参半,认为他们易于产生喜剧效果,适合表现喜剧性角色,但其性格简单,缺乏深度与生命力,不适宜表现严肃的或悲剧性的角色。大体说来,扁形人物易于辨认,易于记忆,不会离开固定的轨道以致失去控制;他们性格稳定,不受环境影响,周围的人事变动反而能显示出其性格的一成不变。所以,这是一种在整部作品中无大变化,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人物。
“圆形人物”又译为“浑圆人物”,是与扁形人物恰成对照的形象。他们远离类型性和漫画性,而给人以立体感和丰厚感。他们处于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外部环境常有变化,内在性情也有相应的发展历程,从而呈多侧面、多层次的复杂性格。关于复杂性格的构成原因,概括起来有大致三个方面:其一,多种多样的非对立性心理因素作用于同一个人物,造成其性格的复杂性;其二,内在对立性人格要素造成性格的复杂性;其三,人物性情的可变性、流动性或不确定性造成性格的复杂性。由此看来,圆形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性就成为以审美方式折射杂色多变的社会生活的需要。
如果按动画影片的历史时间来横向比较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在早期经典动画电影时期,动画电影故事中大多是扁平化的人物,“他们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他们的言行公式可以用一个句子描述殆尽”。在动画里,要么是王子与公主这样的正面角色,要么是巫婆之类的反面角色,还有小矮人这类的配角人物,并且这些角色类型化倾向非常明确:公主是善良美丽的,王子是英俊潇洒的,巫婆是丑陋邪恶的等等,他们都具备鲜明的性格特征,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且在各种突发事件和困难面前也绝少改变。像《白雪公主》中美丽的公主、《灰姑娘》中英俊的王子都属于这类人物。正如福斯特在他的书中所阐述的那样,这种扁平人物的“好处之一在于易于辨认,只要他一出现,即为读者的感情之眼所察觉……好处之二,他们易于为读者所记忆,他们的性格固定不为环境所动,一成不变,存留在读者心目中”。
从创作角度来看,早期动画对扁平人物的塑造主要受到童话与戏剧的影响。首先,早期动画影片的故事与情节很多是源于童话故事的,童话的特点也被潜移默化地移植到动画中,“情节简单,人物鲜明,人们一眼能分辨出好人与坏人”成为显著的特点。其次,传统的戏剧结构影响着动画影片的创作,传统戏剧讲究情节的起承转合,突出对矛盾冲突的设置,人物形象常常按照“正与邪”进行分配,所以,在早期的动画影片中,人们看到的主人公大多是拥有一成不变、单一性格的人物。
然而,随着审美文化的不断发展,现在的受众一般不喜欢那些绝对神化、被拔高的、完美无缺的“公主”或者“王子”、“英雄”。因为,后现代精神引发的解构意识,让人们更倾向于欣赏那些完全背离神圣价值,更具反叛精神,更可以被把玩的人物。由此,现代商业动画电影的主角身上加入了许多普通人的元素,使他们成为“圆形人物”,复杂而丰满,拥有人类所具有的一切优点与缺点:真诚、友善、勇敢、执著,虚荣、自私、贪婪、恶毒……正是这些完美与不完美的组合,才让动画电影更接近人类社会,更接近人类的日常生活,更接近人类的审美情趣。
就圆形人物的性格塑造而言,借用黑格尔在《美学》中对人物性格问题的探讨,他说:“人物性格必须把它的特殊性和它的主体性融合在一起,它必须是一个得到定性的形象,而在这种具有定性的状况里,必须具有一种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所谓“特殊性”是指某人物的性格不同于他者的特征;所谓“主体性”,则指该人物是一个自主存在的形象,有其自身的“定性”,即“一贯忠实于它自己的情致所显现的力量和坚定性”。对此,黑格尔解释道:“一个真正的人物性格须根据自己的意志发出动作,不能让外人插进来替他作决定。只有在根据自己的意志发出动作时,他才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任。”
综观现代动画电影,特别是商业动画电影,其中的圆形人物通常具有独立的个性,并且他们本身的存在意义超越其行为,其动机是行为的依据,通过行为揭示心理或性格。仍以《海底总动员》为例,影片讲述了儿子尼莫由于任性,在外面游逛时被人类带走了。一向谨小慎微的父亲不远万里寻找丢失的儿子,经历了千辛万苦重重磨难之后,最终找回了可爱的儿子。这个故事塑造了一个爱子心切的好父亲,甚至在爱的方面有些过了头。为了表现父亲谨小慎微的性格,在一开始就着重描绘了儿子尼莫的上学过程:上学的路上,父亲处处紧张担忧,一次次地阻拦儿子的“过激”行为。但是,当儿子突发意外被人类抓走的时候,父亲却显露出了惊人的勇敢。于是,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一条焦急的小丑鱼(父亲)在偌大的海洋深处飞快地穿行,追寻儿子的线索和踪迹……当人们看到昔日里处处小心翼翼的父亲义无反顾地游入渺茫的远方,当人们看到父亲充满了悔恨与担忧的神情,当人们看到父亲眼中包含泪水在海中不知所措地打转徘徊……人们被感动了,父亲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无私伟大的父爱。从这次寻子经历中,观众感受到的是一个生动而丰满的父亲形象,从最开始的懦弱胆小到最后的执著勇敢,处处散发着父亲真实情感的流露,这个人物也因此而变得可爱。
再比如,我们在《怪物史莱克》中看到的菲欧娜公主,她一改纤弱无助的女性弱者形象,以一种操持着“骇客帝国”般凌空踢腿绝技的女强人姿态站在观众面前。而且,那个营救她的人也不是英俊潇洒、勇敢无畏的王子,而是一个外表丑陋、自卑又自闭的绿毛怪物。总之,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圆形人物使影片更加容易进入观众的审美视野。
可见,我们不再能像评价早期动画里的人物那样简单地用几个甚至一个形容词就能完满地概括现代动画人物的性格以及形象包孕的内涵。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粗糙的类型象征,而是在拟人化幻想的前提下的一个典型化形象。他有相当的性格层次,精雕细琢的细节,他有丰满的共性和个性。……作者细致地刻画了人类复杂性格的多侧面,使形象有真实人性格所具有的容量和魅力”。
第二节动画电影中的“功能性”人物
“功能性人物”与“心理性人物”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在文学创作理论中,“心理性人物”是指那些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不依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而转移的人物;而“功能性人物”则是指作品中依附于情节而存在,并且推动情节的发展和演变的人物,读者所关注的只是这些人物做了些什么,在故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而非他们在心理、精神层面是怎样的人。人物不能离开特定的上下文,只能作为文学世界诸因素的一部分而存在;若离开情节或事件,他们就会不复存在。可以说,在这样的视野中,人物已失去自身的文学生命力,而仅仅是一种文本成分或语言现象。
在结构主义叙述学的视阈中,人物是一种功能性而非心理性的文学构成要素。其学派奠基人普洛普提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行为功能。他从童话人物中归纳出三十一种功能,进而将人物完成这些功能的情节概括为七个“行动范围”,认为从纷繁复杂的童话人物中可以区分出七类基本角色。在不同的故事中,充当同一类角色的人物可以身份互异,其经历可以千变万化,而功能是一致的。格雷马斯在语义学的基础上将人物归纳为六种“行动元”:主体与客体、发送者与帮助者、接收者与反对者。按他的解释,“行动元”是叙事作品的基本要素,指代共享某些特征的一类行为者。“行动元”与普洛普的“角色”概念既有重叠,又有区别:一个行动元可以由若干个角色体现;反之亦然,同一个角色有时又能分解出若干个行动元。
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提出,“功能性人物”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源于亚里士多德,继之由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加以论证,随后又由结构主义叙事学者深入探讨。亚里士多德的人物观有其复杂之处,可以说兼具“心理性”和“功能性”双重特征,下面这段话所论述的是其“功能性”:整个悲剧艺术包含“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
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因此悲剧艺术的目的在于组织情节(亦即布局),在一切事物中,目的是最关重要的。
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没有“性格”,仍不失为悲剧。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显然突出了行动,而将人物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情节,人物只有作为情节的构成者或行动的执行者,才有其实在的意义和价值。
尽管很难将上述理论生搬硬套地运用于动画电影的研究中,但是,“心理性”和“功能性”人物的概念仍能给研究者以重要启示,特别是在商业动画电影的研究中。一方面,由于商业动画电影艺术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或多或少受到现代文艺理论的浸润。另一方面,商业动画电影属于相对简单化的叙事性作品,其故事具有程式化特征,人物塑造难免显示出某些特定的“功能性”。特别是主人公身边的配角,其言行举止带有某种模式,所发挥的作用也大同小异,他们就像《堂吉珂德》里的桑丘·潘沙,不但能够为作品增添色彩,还能够衬托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又比如《怪物史莱克》中的驴子,《冰河世纪》中的希德,《狮子王》中的蓬蓬,《花木兰》中的木须龙等等。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次要角色在动画故事中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功能性,比如《冰河世纪》中的松鼠,不但给影片增加了笑点,而且还起到了控制影片节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