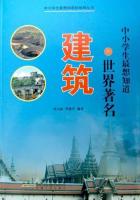当代帝国主义在今天已不再以领土征服和武装霸权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里摄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殖民主义活动,主要通过影视、动漫、游戏、音乐等大众文化商品,甚至通过文化刊物、旅行考察和学术讲座等方式征服后殖民地人民。
与之对应的后殖民理论就是如此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与后现代理论消解中心、消解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研究的潮流相契合,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政治学领域的批评具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阈和研究策略。
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在方法上,多采用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亟须弄清“非边缘化”和“重建中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仇外情绪的弥漫和传统流失的尴尬同时存在之处境,寻找自我的文化身份和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位置。
【杰姆逊】
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表明了其对全球文化后现代和后殖民处境中的第三世界文化的变革与前景之关注。他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做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正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
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
【赛义德】
爱德华·赛义德,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生于耶路撒冷,在开罗上小学,后移居黎巴嫩,并在欧洲流浪,1951年才定居美国。逆境中刻苦攻读,1964年拿下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
经历决定视角,体验主宰构思。这种独特的身世,使赛义德能够以东方人的眼光去看西方文化,以边缘话语去面对中心权力话语,从切身的流亡处境去看后殖民文化境遇。因之,赛义德的写作总是从社会、历史、政治、阶级、种族立场出发,去具体分析一切社会文本和文化文本。其影响最深的代表作品有《东方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文化与帝国主义》。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中强烈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使得其完全可视作一部文化政治学著作。他在这个世界“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东方主义”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与西方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够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研究中产生的异域文化的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甚至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据此,制造“帝国语境”的东方主义已不再是纯学术研究,而是帝国主义的帮凶、文化殖民的策略、强权政治的基础。因之,东方主义有可能在制造了西方摄取东方的好胃口的同时,又不惜通过编造神话的方式美化“东方”清白的受害者形象,制造出又一轮的“被看”方式。
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后成为一位灰姑娘,她只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说话。欧洲人赋予东方以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并以此作为东方对西方挑战的回报,这种现代的“胜利”,终于弥补了早年在东方辉煌时期的欧洲的惆怅悲哀心理。为了这种满足的持久和对“东方复兴”的警惕,东方主义自然有继续存在的必要。赛义德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东方主义者总是以改变东方主义的未来面目使其神秘化,力图创建“东方化是西方化了的东方化”这么一个现实境域,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是为其所信仰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后按西方的趣味和利益重组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因此,这种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其结果只能是创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方精神乌托邦。
关于对策,赛义德认为应当坚持个体的特殊性对学者的批判性思考的重要性,因为特殊性使得学者能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殖民文化。当然,这种对抗不是民族主义式的,而是超越东方或西方利益的人类主义或世界主义的。
【斯皮瓦克】
斯皮瓦克,美籍印度裔女学者,与赛义德的经历相似。大多第三世界学者在西方的生活及其与西方文化的碰撞,都会造成一种文化错位与身份认同的矛盾,这种矛盾,我们可以视之为后殖民理论的发展之源。
“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雨吹打后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而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打下了“臣属”(葛兰西语)的烙印。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看”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斯皮瓦克要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她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历史描述和将历史叙事虚构化的“策略”,而致力于建构第三世界自身历史的新的叙述逻辑。关于这一点,我们倒是可以在中国电影身上看到些许注解,因为这正是部分当代中国电影国际获奖的路径依赖,其本质就是一种迎合西方人前见的叙事策略。
和赛义德对美籍外裔学者身份所感受到的矛盾和焦虑一样,斯皮瓦克也谈到了第三世界学者融入第一世界时所容易出现的“学术招安”现象,她认为臣属阶级的学者打入第一世界学术圈后,成为西化了的东方人,他们能相当完备地运用“西学”武库中的最新武器,并用这种最新理论去反映自己处身的尴尬——她处于高层学术圈中,必然寻求自己应具有的特权地位,于是,她被整合进统治阶级的营垒,消隐了种族、阶级、性别的差异。也就是说,她在追求“主体同质性”的精英身份的同时,忘记了“主体异质性”的边缘文化身份。当她作为边缘化的“从属臣民”时,她没有话语权,当她挤入中心话语圈分享其话语权时,她又无力找回历史记忆中那沉默的话语,却只是满口喃喃这第一世界的言辞。
关于对策,最好的可能就是莫过于抛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在理论上建立其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同时,并非简单地创造出反历史、反霸权的激进话语,而是就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论战和观念的全新调整,以此方式修正“臣属”的历史记忆。
【亨廷顿】
人们大多不把亨廷顿作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加以论列,甚至将他看做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对立的“文明冲突论”的代表。因为在美国,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非中心的、东方主义的边缘性话语,其反主流文化倾向和维护第三世界自身利益倾向十分明显,故而可以称为东方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实质在于从西方中心论出发,维护西方中心话语和文化优势地位,并且为西方文化的“主流话语场”确立新的世界地图的坐标。
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相反的论点,说明他们恰好面对“同一个问题”,即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或“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后冷战”关系问题,而这正是后殖民主义确立的关键点。所以,亨廷顿理论是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相对应的重要部分,这种对应的两极,构成相反相成、互补互释的关系,成为非常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参照系。离开这个参照系,仅仅谈论作为边缘话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将是不清晰和不全面的。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亨廷顿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分析了当前纷纭复杂的国际风云和国际政治文化场景,却很少或未直接谈到关于后殖民主义文论的问题,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对后殖民主义文论没有影响,恰恰相反,他打破了过去从政治、经济、霸权的角度谈论国际文化的旧格局旧思路,而将“文明”作为自己论点的核心范畴,来界定当今世界后冷战新格局,于是,文明、文化、宗教、语言、意识形态,乃至于文学艺术,都成为国际政治和跨国文化影响一个民族思维、性格、精神禀赋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亨廷顿的理论不仅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而且对后殖民主义文论研究有着重要的调整视野和扭转方向的作用,起码,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角度看问题。
一、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是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的权威,具有著名学者和重要政治谋士的双重身份。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所倡导的“新权威主义”和《文明的冲突》所强调的当今“世界秩序重建”问题,都受到了各国首脑、政府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关注,并以他的论点为导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在1993年《外交》(夏季号)上,亨廷顿推出其“文明的冲突”的理论,其后又在《纽约时报》1993年6月16日专栏刊登其中心观点,并接受《新闻点季刊》的采访,大肆宣传自己的“文明冲突论”。其后,在《外交》(11-12月合期)上又发表《如果不是文明,又是什么?》的文章,回答各方面对他的批评和质疑。于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世界各国政界和知识界引起的巨大反响,成为近年来后殖民主义文化冲突理论论战中非常突出的文化景观。
亨廷顿的中心论旨是:世界政治在冷战局势结束后进入了“后冷战”的新阶段,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这使解释和观察世界政治的理论模式需要重新拟定。也就是说,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冲突已不如过去那样重要,不同的国家展开了新的对抗和协调方式,人们需要从新的理论框架来阐释现代世界的文化和政治现象。于是,亨廷顿用“文明的冲突模式”取代了过去的“冷战模式”,因为他坚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会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行,这使得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
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文化认同”对多数人来说成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所谓文化认同,其最重要的层面是文明的认同。文明之间那种势均力敌的僵持状态正在发生松动,其表现为西方的影响在逐渐降低,而亚洲文明正在扩展其经济基础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人口爆炸,非西方文明正要重新肯定和设立自己新的文化价值,因此以“文明”为基础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出现。在亨廷顿看来,在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明之间的交往是有限而间断的,进入现代时期,全球政治才开始出现了一种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互相影响和竞争,到了20世纪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成了三个世界。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了历史。
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里,人们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是:我是谁?我们的国家民族身份和我们的文化身份是什么?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在种族集团、宗教社群、民族身份,以及在最广泛的文化层次上认同文明。在这种新的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和普遍的冲突,不再是社会和阶级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强国和弱国之间以经济划分的层面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