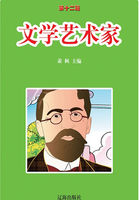审美本质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所写的现实是经过提炼的现实,是比带有偶然性的现象世界更高一层的真实。因之,艺术可以化自然丑为艺术美。亚里士多德当时已经对审美本质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
“事物本身原来使我们看到就起痛感的,在经过忠实描绘之后,在艺术作品中却可以使我们看到就起快感的。例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和死尸的形象。因此,摹仿的对象不限于已有的事和美好的事。”
“喜剧的摹仿对象是比一般人较差的人物。所谓‘较差’,并非指一般意义的‘坏’,而是指具有丑的一种形式,即可笑性(或滑稽)。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例如,喜剧面具虽是又怪又丑,但不至引起痛感。”
“悲剧本身是痛苦的,但却引起别人的恐惧与怜悯,使观众获得快感。”
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把“丑”作为一个审美范畴提出,喜剧里不但摹仿的对象丑(人物),而且摹仿的成品(面具)也丑。这种丑的存在却不妨碍人把喜剧作为艺术来欣赏。这事实就引起一些颇难解决的美学问题:丑能否化为美,丑在艺术中是否可以有地位?丑是否可以作为审美的对象?丑与美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些问题在后来美学中是经常争论的,这里当然不能详谈,只略提“丑”这个审美范畴提出的重要性。其次,“可笑的东西是一种对旁人无伤,不至引起痛感的丑陋或乖讹”这句定义是深刻的。后来许多关于喜剧和滑稽的理论都可以在这句话里找到萌芽(例如,康德的乖讹说,柏格森的机械动作说等)。最后,悲剧定义中着重行动情节,喜剧定义中却着重人物性格的丑陋乖讹,这种分别是正确的、重要的,一般戏剧作品都可以证明。
此外,艺术也可以使事物比原来形状更美,《诗学》第十五章里说悲剧诗人“应该仿效好的画像家的榜样,把人物原形的特点再现出来,一方面既逼真,另一方面又比他原来更美”。上面《诗学》第二十五章引文里所提到的希腊名画家宙克什斯就曾把希腊克罗通城邦里最美的美人召集在一起,把这许多美人的美点融会在一起,画成他的名画《海伦后》。这画既有现实的根据,又远比现实更美。
有机整体观
亚里士多德论诗与其他艺术,经常着重有机整体的观念。这也和他对文艺与现实关系的基本看法分不开的;形式上的有机整体其实就是内容上内在发展规律的反映。整体是部分的组合,组合所应根据的原则就是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他说:“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在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体。”
他认为,“一个整体就是有头有尾有中部的东西。头本身不是必然地要从另一件东西来,而在它以后却有另一件东西自然地跟着它来,尾是自然地跟着另一件东西来的,由于因果关系或是习惯的承续关系,尾之后就不再有什么东西。中部是跟着一件东西来的,后面还有东西要跟着它来。所以一个结构好的情节不能随意开头或收尾,必须按照这里所说的原则进行。”
就是根据这个观念,他断定悲剧是希腊文艺中的最高形式,因为它的结构比史诗更严密。也就是根据这个观念,他断定叙事诗和戏剧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情节结构而不是人物性格,因为以情节为纲,容易见出事迹发展的必然性;以人物性格为纲,或像历史以时代为纲,就难免有些偶然的不相关联的因素。在《诗学》第二十三章里他指出叙事诗与历史的区别:“它在结构上与历史不同。历史所写出的不只是某一个情节,而是某一个时期,那个时期中对某个人或某些人所发生的事,尽管这些事彼此可以不联贯。诗的结构却是要见出内在联系的单一完整的统一体。”这正是《诗学》第八章所要求的“动作或情节的整一”。亚里士多德只强调过动作的整一,后来新古典主义者加上时间与空间的整一,合成所谓“三一律”,他们把动作的整一看成每篇诗只能写一个情节,不穿插附带的情节,这是从形式上看整一,忽略了内容上的内在联系。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谈戏剧中的合唱队、音乐和语言等因素,也要求一切都要服从整体。谈到音乐时,他把一曲乐调比作一个城邦,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各称其分,各得其所。
同样,亚里士多德的有机整体观也就应用到其对于美的理解之上,他认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或是任何由各部分组成的整体,如果要显得美,就不仅要在各部分的安排上见出一种秩序,而且还须有一定的体积大小,因为美就在于体积大小和秩序。一个太小的动物不能美,因为小到无须转睛去看时,就无法把它看清楚;一个太大的东西,例如,一千里长的动物,也不能美,因为一眼看不到边,就看不出它的统一和完整。同理,戏剧的情节也应有一定的长度,最好是可以让记忆力把它作为整体来掌握。
这里指出了美的客观标准,同时也指出了这种客观标准与人的认识能力之间的密切联系。事物如果要显得美,一方面要靠它本身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靠观众的认识能力。
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在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中,和谐的概念是建立在有机整体的概念上的,各部分的安排见出大小比例和秩序,形成融贯的整体,才能见出和谐。后来许多美学家如康德等就把和谐、对称、比例之类因素看成单纯的形式因素,好像与内容无关。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就比他们高明得多。他把这些因素看成与内在逻辑和有机整体联系在一起的,即由内容决定的。
最能说明他的意思的是音乐,即他所认为“最富于摹仿性的艺术”。在《问题》篇第十九章里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节奏与乐调不过是些声音,为什么它们能表现道德品质而色香味却不能呢?”他的答案是:“因为节奏与乐调是些运动,而人的动作也是些运动。”这就是说,音乐的节奏与和谐(形式)之所以能反映人的道德品质(内容,见于动作),是因为两者同是运动。音乐的运动形式直接摹仿人的动作(包括内心情绪活动)的运动形式,例如高亢的音调直接摹仿激昂的心情,低沉的音调直接摹仿抑郁的心情,不像其他艺术要绕一个弯从意义或表象上间接去摹仿,所以说音乐是最富于摹仿性的艺术。因为音乐反映心情是最直接的,它打动心情也是最直接的,所以它的教育作用也比其他的艺术较深刻。
从此可见,音乐的节奏与和谐不能单从形式去看,而是要与它所表现的道德品质或心情联系在一起来看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内容形式统一的看法是深刻的。
艺术功能论
在艺术功能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有不一样的地方。柏拉图认为,理想的人格要能使理智处在绝对统治的地位,理智以外的一切心理功能例如本能、情感、欲望等,都被视为人性中“卑劣的部分”,都应该毫不留情地压抑下去。艺术正是要投合人性中这些“卑劣的部分”来产生快感,所以对于人的影响是坏的。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却与此相反。他的理想的人格是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格。本能、情感、欲望之类心理功能既是人性中所固有的,就有要求满足的权利;给它们以适当的满足,对性格就会发生健康的影响。就是从这种伦理思想出发,他对诗和艺术进行辩护:文艺满足人的一些自然要求,因而使人得到健康的发展,所以它对于社会是有益的。
从文艺功能上来看,柏拉图是片面强调教益而力图扼杀快感的。亚里士多德是最早的一个替快感辩护的哲学家。从《诗学》里许多提到快感的地方看,人们容易猜想亚里士多德好像肯定文艺的目的就是专门产生快感的,事实上有许多学者就采取这样的看法。例如《诗学》的英译者布乔尔就说:“亚里士多德对于诗的评断都根据审美的和逻辑的理由,并不直接考虑到伦理的目的或倾向。”“他是第一个设法把美学理论和伦理理论分开的人。他一贯地主张诗的目的就是一种文雅的快感。”阿特铿斯也说:“亚里士多德像是把美感的目的和道德的目的分开,认为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附带的。”“代替这一切,亚里士多德提供了一些更合理更有效的方法,特别指出审美的标准是唯一的标准,文学判断的真正基础就在于艺术的要求和标准。”“他的判断完全根据审美的理由。”
悲剧论
在讨论悲剧的时候,亚里士多德首先对它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个定义涉及到了悲剧摹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悲剧的功能等方面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是由六个要素构成的,即情节、性格、思想、台词、扮相和音乐。其中情节和性格是最为重要的。就情节安排而言,诗人应当遵循事件发展的可然律或必然律,应当使情节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就性格描绘而言,应当恰当、逼真、前后一致。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悲剧的主人公应当是一些并非十全十美,也非十恶不赦之辈,他们应当是好人,但又有一些缺陷和过失,由此而给自己招致了灾祸,这样悲剧才能激起我们的怜悯与恐惧之情,才能使我们的情感得以净化。
悲剧的过失说
悲剧的情节一般是好人由福转祸,结局一般是悲剧的。这种情节和结局,如果单从道德观点来看,是不易说得通的。希腊人自己的看法以及后来西方学者对于希腊悲剧的看法,都是归咎于命运。人们说,希腊悲剧所写的是人与命运的冲突,而近代戏剧所写的则是人与人的冲突,或是同一个人身上两种势力的冲突。
亚里士多德要求一切合理,在《诗学》里从来不提希腊人所常提的“命运”二字,并且明白地谴责希腊戏剧所常用的“机械降神”,即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境就请神来解决的办法。他怎样来解释好人由福转祸的情节呢?他的解释表面上好像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要求祸不完全咎由自取,他说,“不应遭殃而遭殃,才能引起哀怜”,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祸有几分由自取,他说,悲剧主角的遭殃并不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所以“在道德品质和正义上并不是好到极点”,也就是说,“和我们自己类似”,才能引起我们怕因小错而得大祸的恐惧。把这两点合在一起来看,亚里士多德像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来说明悲剧的合理。其实这正是他的辩证处。只有这种辩证的看法才能说明哀怜(须祸不由自取)和恐惧(须小过失引起大灾祸),因此,才能说明亚里士多德所了解的悲剧。他要求悲剧主角的性格有“和我们自己类似”之处,意义是极深刻的。只有这样,悲剧主角才能叫我们同情,也只有这样,悲剧作品才能成为社会的财富。这种考虑单是“道德的”呢?是“逻辑的”呢?还单是“审美的”呢?应该说,它是这三种考虑的辩证的统一。
悲剧的净化说
《诗学》第六章悲剧定义中最后一句话是悲剧“激起哀怜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绪的净化”。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恢复和保持住心理的健康。在《诗学》里提到的是悲剧净化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在《政治学》里提到的是宗教音乐净化过度的热情,这里同时还明白指出受“其他情绪影响的人”也都可以受到净化。从此可见艺术的种类性质不同,所激发的情绪不同,所生的“净化”也就不同。总之,人受到净化之后,就会“感到一种舒畅的松弛”,得到一种“无害的快感”。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净化”说正是针对着柏拉图对诗人的控诉。柏拉图说,情绪以及附带的快感都是人性中“卑劣的部分”,本应该压抑下去而诗却“滋养”了它们,所以不应留在理想国里。亚里士多德替诗人申辩说:诗对情绪起净化作用,有益于听众的心理健康,也就有益于社会,净化所产生的快感是“无害”的。
对于一般美学原理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里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他认为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文艺激发不同的情绪,产生不同的净化作用和不同的快感。例如悲剧所产生的快感只是哀怜和恐惧两种情绪净化后的那种特殊的快感,亚里士多德屡次把它叫“悲剧的快感”,并且指出它是悲剧所特有的,至于写善恶报应所生的快感以及写滑稽性格所生的快感就只宜于喜剧而不宜于悲剧。这种快感其实就涉及一般美学家所说的“美感”。历来美学家谈到“美感”,大半把它看做在一切审美事例中都相同的一种通套的快感。这是脱离产生美感的具体情境来看美感,把美感加以抽象化和套板化。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则是:产生美感的东西不同,所产生的美感也就不同。还不仅如此,情绪净化的快感只是美感来源之一,他还提到摹仿中认识事物所生的快感以及节奏与和谐所产生的快感。这几种快感在不同的文艺作品中分量配合不同,总的效果——即美感——也就不一致。这是一种带有辩证意味的看法,可惜历来美学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