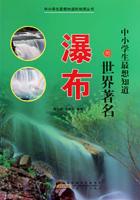李渔虽然认为戏剧艺术要典型化、要虚构,但历史剧却又不一样。他认为,历史剧不能允许虚构,甚至提出了“实则实到底”这种过于绝对的观点。相比之下,倒是明清小说家的“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更为确切。因为,其一,历史剧终究是艺术,而非历史教科书。既为艺术,就当然和其他艺术一样,要有典型化,要创造艺术典型,这就离不开虚构。事实上,在戏剧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实则实到底”的历史剧,李渔自己也没写过这样的历史剧。即使如孔尚任自说其《桃花扇》为真人真事,也被梁启超考证出其与历史事实不符的地方有几十处之多。其二,历史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性。它必须使广大观众感到熟悉和亲切,并且使观众易于了解和接受。因此它的表现形式就必须考虑到当时的语言和整个社会文化的状况,这也就离不开虚构。或许黑格尔在《美学》中那段话能够更好地做一个说明:“我们固然应该要求大体上的正确,但是不应剥夺艺术家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的权利。”
戏剧的通俗化
李渔对戏剧通俗化的要求,在剧本创作和舞台演出方面提出了两个重要的主张。一个主张就是少用方言,因为方言不利于广大群众对于戏剧的欣赏。再一个主张就是演出要尽量采用现代剧本,他把这一点列为选剧本的第一条原则,理由是人们总是对现代的艺术作品比较感兴趣。他说,“听古乐而思卧,听新乐而忘倦”,不是从来如此吗?戏既是演给现代人看的,现代剧本自然更能得到现代观众的欣赏和理解。古代剧本对于现代观众就显得比较生疏,“只可悦知音数人之耳,不能娱满座宾朋之目”,能够欣赏和理解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当然,古代剧本也并非完全不能用。但李渔认为,采用古代剧本,必须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修改,使之适应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和要求。因为社会变化了,人们的心理也变化了,戏剧观众的欣赏习惯和欣赏要求也变化了,上演古代剧本时就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清初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代表性著作有《姜斋诗话》。
情景说
首先,王夫之明确地把“诗”、“志”和“意”加以区别。“诗言志”,但“志”不等于“诗”。因为诗的本体是审美意象,而“志”“意”并不等于审美意象。“志”“意”与审美意象是两个东西。一首诗好不好,不在于“意”如何,而在于审美意象如何。这在美学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是人们往往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由此产生了种种弊病。王夫之把这种混乱彻底澄清了。他说:“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意。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诗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须赞《易》陈《书》,无待诗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岂有入微翻新、人所不到之意哉?”为什么诗之深远广大、舍旧趋新俱不在意?就因为诗的本体是审美意象,而不是意。如果诗的本体是意,那不如赞《易》陈《书》,根本用不着诗了。关关雎鸠所以好,是这首诗的审美意象好,并不是这首诗有什么“入微翻新、人所不到之意”。
其次,王夫之又明确地把诗和史加以区别。他认为,诗虽然也可以叙事叙语,但并不等于史。写诗要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也就是要创造意象,而写史虽然也要剪裁,却是从实著笔,所以二者有本质的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一个是审美的,另一个则不是审美的。在这里,王夫之和杨慎一样,也反对诗史之说。他认为杜甫的一些诗,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并不值得赞美。
总之,诗既不是志,也不是史。那么,诗是什么?是审美意象。但是,意象又是什么?王夫之认为,诗歌意象就是情与景的内在统一。情、景的统一乃是诗歌意象的基本结构。
王夫之指出,情与景是审美意象不可分离的因素。他称赞谢灵运的诗“言情则于往来缥缈有无之中,得灵蠁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在他看来,诗歌的审美意象不等于孤立的景。景不能脱离情,脱离了情,景就成了虚景,就不能构成审美意象。另一方面,审美意象也不等于孤立的情。情不能脱离于景。脱离了景,情就成了虚情,也不能构成审美意象。只有情景的统一,所谓“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虚景,景总含情”,才能构成审美意象。
但是,情、景不可分离,并不是像宋元以来有的诗论家说的那样,写诗必须一联情,一联景。王夫之反复说“景生情,情生景”,“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景中生情,情中含景”,都是在强调情与景的统一是内在的统一,而不是外在的拼合,不是机械的相加。
王夫之认为,情景的结合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态,只要它们是内在的统一,而不是外在的拼合,那么,它们都可以构成审美意象。“诗成珠玉在挥毫”,只有情语,但是情中显出了景,是为情中景。“长安一片月”“影静千官里”,只有景语,但是景中藏着情,是为景中情。文征明的《四月》诗:“春雨绿阴肥,雨晴春亦归。花残莺独啭,草长燕交飞。香箧青缯扇,筠窗白葛衣。抛书寻午枕,新暖梦依微。”王夫之认为这首诗的结语就是人中景。又如刘令娴《美人》诗:“花庭丽景斜,兰牖轻风度。落日更新妆,开帘对春树。”王夫之认为这首诗就是“景中有人,人中有景”。
【叶燮】
叶燮,字星期,号己畦,中国清代诗论家、美学家,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
叶燮在《原诗》内篇对艺术下了一个定义: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又在《赤霞楼诗集序》中从艺术中抽出诗和画两大类,他认为,诗和画作为客观世界的审美反映,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说“画者天地无声之诗,诗者天地无色之画”,“画与诗初无二道也”。另一方面,诗和画所反映的对象和方式有所不同,所以应该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诗和画的统一,情和形的统一,就能产生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来。
但叶燮并未就此而止,他进一步探讨了艺术创作中物与心的关系。
他说:“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胆、曰识、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无不待于此而为之发宣昭著;此举在我者而为言,而无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
在物的层面,具体分为理、事、情,在心的层面,具体为才、胆、识、力,叶燮主要说明了艺术创作是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的结合,是“以在我者四,衡在物者三”,然后合而为作者之文章。
理、事、情
在叶燮的论述中,理、事、情是指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他说:“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万汇之赜,日星河岳,赋物象形,兵刑礼乐,饮食男女,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之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可见此万事万物既可以指日月山川等自然现象,也包括兵刑礼乐等社会问题。诗歌或文章的任务就是:先揆乎理,次征诸事,终絜乎情,真实地反映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理、事、情。
至于理、事、情各自的含义,叶燮以比喻说明之,“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据此,理指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事指事物循其理而发生发展的过程,情则指事物所呈现的情状。三者有机统一,随其自然而发展。他说:“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叶燮认为,气是万事内在生命力的表现,也是诗与文章之生机和活力所在:“吾故曰:三者籍气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氤氲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在理、事、情三者中,叶燮对理给予特别的重视,认为“理者与道为体,事与情总贯乎其中。惟明其理,乃能出之而成文”。
叶燮认为,诗歌中的理、事、情有自己的特征,它不是生活中理、事、情的简单翻版。他说:“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此岂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则余之为此三语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锢也。得此意而通之,宁独学诗?无适而不可矣。”如果说名言之理、施见之事、径达之情这些都是生活中的理、事、情,那么这里所说的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便指的是被表现在诗歌中的理、事、情,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前者是实,后者是虚;前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后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倘恍以为情。于此,叶燮特别强调创作主体对于表现对象的深刻体验和独特感受,揭示了诗之所以为诗的审美特质。
才、胆、识、力
外在的理、事、情统之为物,内在的才、胆、识、力则总之为志。叶燮说:“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识、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於笔墨之外。”在他看来,诗是用以言志的,才、胆、识、力是志的具体化,只有通过才、胆、识、力四者,才能融主客观于一炉,在“遇物触景”之际产生创作的冲动,美妙的言辞在作者的笔下也就如贯珠般流溢而出。
何为才、胆、识、力?叶燮说:“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这说明才、胆、识、力是一种主体创造的能力,是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主观条件。
才,是指作者先天禀赋的才华,也指他驾驭创作法则的具体能力,叶燮说:“夫才者,诸法之蕴隆发现处也。”但才的发挥,一方面得以识为其铺垫,“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人,当先研精推求其识”;另一方面还得以胆去充实它,也即胆能生才,它能让才华横溢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打破陈规陋习,去以才御法,大胆地创新。
胆,是指作者的胆略和勇气,在艺术创作中就是指能摆脱前人藩篱,敢于独立思考,挥洒自如的创新精神。“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吾固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
识,是指作者对外在事物美丑是非的辨析能力,有了识力,就能明是非,辨美丑,定取舍,反之亦然。“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无识力,在文艺创作中的具体表现是,面对前人丰富的艺术遗产,会茫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人云亦云,众口同声。
力,是指作者表现其才思识见的能力,以及在创作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笔力。力是才的载体,是才的具体表现,才有大小,力也有大小。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在文学发展史上那些著名的文学家,不但有才,而且有力,是力使得他们特立独行,自成一家。他说:“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己力而成之耳;岂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为我之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