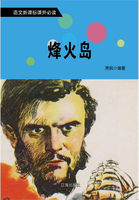他所说的“文质彬彬”也可以进一步表明这一点。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指人之朴实自然、毫无修饰,“文”是指人之文采修饰。孔子认为,一个人质朴多于文采,这个人就粗野了;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浮了。只有文采和质朴统一起来,才成为一个君子。这里,文和质的统一,也就是美和善的统一。孔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美学史上影响很大。历代的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的问题上,多数人都主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质和文的统一,而反对质胜文和文胜质这两种偏向。
当然,孔子的“美”这个字经常在指涉形式美和指涉内容善两个层面相互混用——如美玉之美就是说的外观美、形式美,而君子成人之美的美就是指内容的善、好。尽管孔子的“美”的概念缺乏明确的限定,但只要它肯定并强调了美有外观美丽、漂亮的意义,并不从属于善,那就等于确定了美的独立品格。
美的标准
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就是孔子的审美标准。他认为,艺术包含的情感必须是一种有节制的、有限度的情感。这样的情感符合“礼”的规范,是审美的情感。也正因此,他才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因为郑声的情感过分强烈,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变得淫了,不符合礼的规范,所以不是审美的情感。
孔子的这个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和”。他的重点不在于音调本身的和谐,而在于音乐表现的情感要受到礼的节制,要适度。
艺术功能论
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观、群、怨,就是谈的诗的社会功能。
兴,朱熹解释为“感发志意”“托物兴辞”,孔安国解释为“引譬连类”。通俗地说,就是诗歌可以使欣赏者的精神感动奋发。这种精神的感发,是和欣赏者的想象和联想活动不可分的,因而是和诗歌的审美形象不可分的。
观,郑玄解释为“观风俗之兴衰”,朱熹解释为“考见得失”。总之,是说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活动、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
群,孔安国解释为“群居相切磋”,朱熹解释为“和而不流”。也就是说,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交流思想情感,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
怨,孔安国解释为“怨刺上政”。其实怨并不限于怨刺上政,凡是对现实的社会生活表示一种带有否定性的情感都属于怨。可以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引起欣赏者对于社会生活的一种情感态度。
对于孔子关于“兴、观、群、怨”的论述,还可做如下分析:
第一,孔子看到了艺术欣赏活动的多种因素、多种内容,并且把这多种因素、多种内容统一了起来。这表明,在孔子看来,艺术欣赏活动不单纯是感性的活动,同时包含有理性的内容;它也不单纯是认识活动,同时也是情感活动;它也不单纯是被动的接受,同时是主动的抒发;它不单纯是个人的活动,它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活动。如此来看,孔子对艺术功能的这番理解是全面、深刻的。
第二,孔子强调诗歌对人的精神的感发作用,从而把握住了艺术欣赏活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孔子把“兴”放在第一位,说明他对“兴”的作用特别重视,这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思想家。比如王夫之就说:“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他把可不可以“兴”,作为区分诗与非诗的最根本的标准。为什么把“兴”放到这么重要的地位?王夫之说:“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又说:“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在这里,王夫之对“兴”做了进一步说明。所谓“兴”也就是诗歌对人的灵魂起一种净化的作用,也就是“荡涤其浊心”,也就是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起一种感发、激励、升华的作用,使人摆脱昏庸猥琐的境地,变为一个有志气、有见识、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人,从而上升到豪杰、圣贤的境界。这是“兴”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也是其社会功能。
孔子把兴放在第一位,说明在他看来,艺术欣赏作为一种美感活动,它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就在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一种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孔子的这个思想对后世文艺思想的影响很大,后世很多思想家在谈及艺术欣赏时,总是首先强调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的感发、激励、净化和升华,而不是首先强调某一局部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功能。这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比德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表面上,这是说的艺术欣赏的主体性问题。但缘何君子们会喜山乐水呢?这里,山水之所以成为君子的观照对象,是因为君子以山水比德。也就是说,山水的自然形象的某些特征可以象征人高尚的道德品质。
按照孔子的命题和“比德”的理论,自然山水之所以美,虽然同自然物本身的某些特性有关,但决定的还是在于审美主体把自然物的这些特性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构成自然界的美的是使我们想起来人或是预示人格的东西。自然界的美的事物,只有作为人的一种暗示才有美的意义。”按照这种看法,自然美就不是纯客观的东西,它包含有审美主体的思想、联想、想象的成分,也就是包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
这种“比德”的审美观在我国美学史上也有深远影响,人们习惯于按照比德的审美观来欣赏自然物,也习惯于按照这种比德的审美观来塑造自然物的艺术形象。屈原的《橘颂》,几乎句句都是比德。梅、兰、菊、竹被称为四君子,松、竹、梅被称为岁寒三友,这些都是比德。
【墨子】
墨子,名翟,鲁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著有《墨子》,主要内容有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这里主要说说墨子的非乐观。
墨子之所以非乐,是因为他认为统治者喜好音乐,必定会妨碍社会生产,浪费社会财富,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使劳动人民衣食不足,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和国家的灭亡。
墨子维护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却也有片面性。荀子就曾直接批评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吉联抗先生认为墨子的“片面性在于看不到人不是机械,人的活动必须有劳有逸,劳逸结合,而音乐活动则正是逸的一种方式”。蔡仲德先生认为:“墨子以利为判断标准,但似乎只见物质之利,而无视精神之利。既否定休息娱乐的积极意义,更是无视音乐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看不到生产、政治靠人,而音乐能影响人,也能影响生产、政治,因而否定了音乐的社会功用,否定了审美与艺术存在的价值。”这些都是切中要害的。
墨子在论证他的非乐主张时,提出了“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先质而后文”的命题。这个命题包含有审美和艺术活动要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的思想。这是有合理因素的。
【王充】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代表著作《论衡》。王充对于艺术作品,提出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真实,二是要有用。
艺术作品要真实
这个要求是为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决定的。他写《论衡》,总的指导思想是六个字:“疾虚妄,求实诚。”所谓“实诚”,一方面是指作品所记之事要真实可靠,要如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实事;另一方面是指作品中包含的道理必须是真理,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从而有助于人们分清真伪,明辨是非。简单来说,实诚,就是事要实,理要真。
王充对于艺术作品的这个要求,对先秦美学是一个发展。因为先秦美学家对艺术作品更多地是着眼于善,而较少着眼于真。王充则强调真之美,认为真才能美。这个发展,是王充在同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的斗争中作出来的,是很可贵的。
根据这个要求,在内容与形式的问题上,王充的观点是把内容的实诚放在第一位,在崇实的前提下,要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所谓“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据此,王充反对夸张。在他看来,夸张也属于“虚妄之言”,因为它不是实事,是不符合实诚的要求的。例如,古书上说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夸张失实的:“案高祖伐秦,还破项羽,战场流血,暴尸无数,失君亡众,几死一再,然后得天下,用兵苦,诛乱剧。独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实也。言其易,可也;言兵不血刃,增之也。”又如,古书说楚国养由基射杨叶,百发百中。他也认为是夸张失实:“夫言其时射一杨叶中之,可也;言其百发百中,增之也。”由此可见,王充从实诚的要求出发,在否定虚妄之言的时候,把艺术夸张也一起否定了。这说明他不了解艺术的真实和历史实录的区别。他强调真,却不了解艺术的真是何样的真。
艺术作品要有用
这其实说的就是对艺术作品的善的要求。从先秦以来,无论是肯定艺术的孔子和儒家学派,还是否定艺术的墨子和韩非,都强调艺术作品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王充受他们的影响,强调文章要为世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这里的为世用,一方面是指劝善惩恶的道德教化作用,以及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指它在认识方面的作用,使人们明白事理。这两个方面,先秦美学家都谈到过。但比较起来,王充对艺术作品的认识作用比先秦美学家强调的分量要更重一些。因此,王充讲的为世用,比起先秦美学来,它的含义要稍广阔一些,它的直接政治功利色彩要稍稍淡薄一些。
从王充的实诚和为世用这两个要求,可以看出,在王充那里,艺术的真善美是统一的。但王充的统一只是初级形态的统一,因为它还没有充分把握艺术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规律性,还没有把握艺术真善美的内在联系。而这种高级形态的统一,一直要到清初的王夫之、叶燮那里才得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