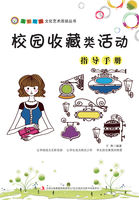毫无疑问对于文化的问题,鲍德里亚留恋着精英主义和文化的精英化,虽然他在消费问题上用力的呼唤真正的民主和平等。他认为,文化的媚俗现象有其美学功能,但是是一种“反美学”的功能,精英文化的特征是独创性,而大众文化则是“模拟”,媚俗提出的是“模拟美学”。在这里,可以见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传统,他们两个即是以模拟和复制作为文化工业的特点。鲍德里亚认为,“这种模拟美学是与社会赋予媚俗的功能深刻相关的,这一功能便是,表达阶级的社会预期和愿望以及对具有高等阶级形式、风尚和符号的某种文化的虚幻参与,这是一种导致了物品亚文化的文化适应美学。”
因为文化的媚俗,所以它才得以流行,而且由于消费的逻辑在于消费的符号性而非实用性。因此鲍德里亚认为艺术“沦落”了,并对此——如果它曾经高高在上的话——发出了批判的声音。换言之,对于鲍德里亚来说,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是一种掏空了内容的形式消费,因此晦涩高雅的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艺术才可以参加到大众文化的狂欢中来,成为众语喧哗的对象。在消费社会中,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被割裂了,表层影像与深层意蕴之间筑起了栅栏。如果说,精英文化和经典艺术是一种“象征”美学,那么大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就是反象征的美学。鲍德里亚认为,流行艺术的这种命运来自消费逻辑的控制。在他看来,消费逻辑即符号操纵,“其中缺乏创造物的象征价值和内在象征关系:它完全是外在的”。在这种逻辑的摆布下,艺术一步步趋向世俗化,逐渐停止对道德和心灵价值的参照,拒绝对灵魂的隐秘发问。所以消费逻辑取消了艺术表现的传统崇高地位。
具体来说,之所以说流行艺术是反象征的,是因为对艺术的消费和对其他物品的消费一样,成为一种符号的形式消费。如果“象征”表征了对深层意义的揭示,“符号”消费则将意义驱逐在消费之外。消费对象的本质或意义不再具有对形象的优先权了。流行不是以周遭世界的本来面貌来看待世界,而是首先将世界作为一个可操纵符号的人工场所,一个“彻底的文化伪迹”。我们对于艺术的消费方式也从以前逐词逐句的严密研究转为现在的泛泛浏览,这是书写艺术转为视觉传媒文化的同步过程,这种视觉影像文化是鲍德里亚在另一部著作里突出提到的“拟像”(类像)文化。因此,他认为,“流行强行进行的活动距离我们的‘美学感情’很远。流行是一门‘酷’的艺术:他并不苛求美学陶醉及情感或象征的参与(深层牵连),而要求某种‘抽象牵连’,某种有益的好奇心”。
这里所谓的“酷”,乃是指对艺术等的消费已经冷酷地离“意义”而去,而流连于形式的“好奇心”之中。鲍德里亚在分析电视这一主导传媒时指出,我们对于传媒信息的消费,是一种能指化而非所指化的消费。换言之,拿文化消费来说,我们消费的只是文化的形式,而非文化事件本身,是文化的画面而非文化本身的内涵。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所指并不在场。因为我们只是把文化作为时尚的代号或声誉、地位、身份和符码。鲍德里亚在《电子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也认为,电视图像不再表现什么,而仅仅是模拟,“有特权的食物不再存在……艺术作品创造了自身的空间”。“模拟指涉了一个没有参照物的世界,在此,所有的参照物都消失了。”还说,艺术或图像“给没有意义的东西以意义,给没有认同的东西以认同感”。对于模拟,他还说,“模拟不再与版图、参照物或实体有关。它是超真实的产物。版图不再先于地图,而且其寿命也没有后者长。因此,是地图先于版图,即是地图造成了版图。”
同时,鲍德里亚也指出,流行文化不是真正的平民艺术,不是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民间文化,而是经由大众传媒传递和制造的自上而下的通俗文化,是一种文化的,并最终是商业的设计。换言之,流行文化和大众传媒是商品社会的同谋,是消费逻辑的衍生物。鲍德里亚说,虽然我们会在电视等媒体前对着流行艺术不断微笑,但不管以什么逻辑来看,这种微笑都与那颠覆性的、侵略性的幽默无关,与超现实主义物品的碰撞无关。“不要忘记,‘某种微笑’是消费的必需符号之一,它不再构成一种幽默、一种批判性的距离,而是指构成了对那如今已被物化为一瞥的超验性批判价值的回忆。”“在这一‘酷’的微笑中,再也无法把幽默的微笑与商业同谋的微笑区分开来。”所以这种微笑体现了消费社会的全部暧昧,微笑“并非批判距离的微笑,而是勾结的微笑”。
因此流行文化具有意识形态性,这一点也表现了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性。鲍德里亚重点分析的是电视、广告等传媒这方面的性质。这种性质象征着一种文化霸权关系,象征着电视媒体所占据的一种权力地位。实际上,我们消费的信息,只是媒介技术性组合、剪辑、诠释过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事实,并不是现实真相,电视信息的编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编码,是一种文化权力的编码,但是,我们在一个全面依赖媒体的时代,在媒体的引导、诱惑之下,主要保留的是被动解码的权力,形成了观看世界的有限视角,即有所取舍的媒体画面视角。电视永远只给予一个传媒中的世界,而非一个全部的世界。“电视画面希望成为一个缺席世界的元语言。”“在画面消费的后面隐约显示着解读系统的帝国主义。”在对消费者主动塑造方面,广告也许是消费时代“最出色”的大众媒介。他以商业的伙伴关系,秘密参与社会分层的过程,又有恃无恐的制造时尚、亮出种种身份的名片,从而如麦克卢汉所说,达到使社会重新“部落化”。媒介所塑造的“新”现实相对于全部现实而言是一种伪现实,同时对于依赖媒体的大众来说,这种新现实恰恰是最直接的因而是最真的现实,从而媒介新现实反过来成为同化、对付现实的新力量。鲍德里亚说,广告“尤其意味着伪事件的统治”。它源源不断地利用我们被诱导的愿望,来操纵我们的消费和对于世界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