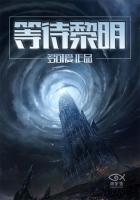由于漫长的历史文化心理积淀,中国人往往以家族利益为行为要义,价值倾向容易局限于家庭,思想上相对狭隘,行为上相对保守,常常安于家庭而不轻易接受社会变革。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小爱”就会向“大爱”发展,从维护家族利益转变为维护民族利益。如《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认为战争持续不了多久,一心想着自己的大寿庆典,但当他目睹日本人的侵略和家族的分崩离析后,认识到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小家,国家利益永远高于家族利益。《范府大院》中的彩三,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最初的时候,他仍考虑家族利益,但随着爱国救亡运动的深入,其观念逐步转变,他积极帮助蔡老板往延安方面运送电台、寻找军需用品。彩三的所作所为,正是由“小爱”上升到“大爱”的生动体现。
此外,家族剧还为现实中的人们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模板和方向。如吃苦耐劳、奋斗不息的精神:《上海一家人》的若男在旧中国历经艰辛成为民族实业家;《大染坊》的陈六子从叫花子成长为印染大亨。再如维护家庭和谐的乐于奉献精神:《四世同堂》的韵梅,虽识字不多,言谈也离不开油盐酱醋茶,但她善于化解家庭矛盾,平缓风波,任劳任怨地操持着全家十口人的衣食住行及与亲友的礼尚往来,维持着四世同堂的安宁和幸福;《大宅门》的二奶奶忍辱负重,将一个大家族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也给当今的人们维持家庭幸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率。这些家族剧在向我们展现家族变迁、世态变化的同时,也使人们重新反思自己的生活目标及家庭状况,帮助人们在继承中重建新的伦理道德标准。
三、家族文学的积淀传承
在中外文学史中,家族叙事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特别是在中国,家族叙事更是成为艺术家们极其热衷的一个叙事主题和难以释怀的文化情结。在18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在一步步走向没落,却激发出了《红楼梦》这部巨著。《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代表,再现了封建贵族四大家族没落的命运,也全面完善了文学作品中家族叙事类型的建构。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张爱玲的《金锁记》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春秋》,作品中无不蕴藏着家族的历史和家族的隐秘。家族叙事在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中更是大量涌现,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余华的《活着》、贾平凹的《秦腔》、陈忠实的《白鹿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李锐的《旧址》、莫言的《丰乳肥臀》、苏童的《罂粟之家》、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张炜的《家族》、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阿来的《尘埃落定》……家族叙事不仅由王宫、大院向乡镇扩展,更从有形的历史进程延伸至无形的精神苦旅。借助于“家族”这根扭结着历史和文化以及生命血脉的缆绳,中国作家的历史叙事增强了文学的个人体验性和深入各个文化层面的想象空间。
家族叙事不仅产生了脍炙人口的文学精品,进而成为戏剧与电影改编的极好素材,也催生了很多电视剧改编佳作,如《红楼梦》、《四世同堂》、《上海的早晨》、《家春秋》、《白银谷》、《橘子红了》、《金锁记》、《尘埃落定》、《中国往事》等等。可以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家族文学都为家族剧的创作繁盛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借鉴摹本,壮大着它的规模,促进着它的成长。
第二节家族剧的叙事特征
一、叙事结构的宏大性
家族作为一个以地域性、血缘性、人情性为纽带的历史文化复合体,其本身就含括着人物关系的复杂性、结构组织的多重性和叙述形式的多样性。因此,家族剧一般叙事纵向时间跨度大,横向空间涉及面广,内涵和外延伸缩自由,它可以作为一个表现重大事件、重大题材的叙事载体,蕴含着波澜壮阔的社会内容及历史意味。同时,家族剧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将个人心路历程、家族起落沉浮表现为国家命运与时代脉搏的变迁,在叙事结构上完成了由个体叙事到宏大叙事的转变。“李少红版”的电视剧《雷雨》打破了曹禺戏剧原著严格遵守“三一律”的规约,以影像的方式再现了30年间周家内外的恩怨情仇,在家族叙事中折射出工人运动、民族资本发展等社会现实生活的侧面。潘霞导演的《澳门的故事》是在世纪之交时回眸澳门百年沧桑,以编年体形式勾勒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澳门70多年间的历史征程,以许家家族风云为载体,在各个社会阶层以及葡萄牙、日本等广阔的社会时空中展开叙事。《乔家大院》时间跨度从咸丰年间到八国联军侵华,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以乔家为代表的晋商发展史及其生活风貌。
剧中乔致庸从挽救家族灭亡到一步步发展家族事业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晋商发展的历程。剧中通过乔家几代人的人物命运,折射出中国晚清末年和近代史上的一系列巨大社会变迁。《范府大院》更是一部涵盖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宏大制作,所反映的是从1900年清末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漫长时间段中范府的历史沧桑。张新建、孔笙导演的《闯关东》则表现了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家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闯关东的故事,以主人公朱开山复杂坎坷的一生为线索,穿插朱开山的三个性格、命运不同的儿子在闯关东路上遇到的种种磨难和考验。而张黎导演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则通过一种家族叙事方式,展现了1925年至1949年间中国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该剧把主要镜头对准了那些在滔滔洪流中蠕动挣扎的普通人,以平民英雄的立场重新解读革命,从而获得家族叙事的独特深度。其另一部电视剧《中国往事》以曹、郑两家作为深度解剖的历史文本,批判性地反思了几十年家庭波折与社会动荡中的社会痼疾和革新力量,重新解读了国族身份和文化属性。
此外,家族剧通过家族内外的重重矛盾展现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矛盾冲突,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如《大宅门》被称为一部气势恢弘、荡气回肠的家族史剧,从医药世家白家四代的家族矛盾和人物纷争揭示出腐朽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谷穗黄了》(又名《韩家大院》)展现韩家大院的特定地域文化特征以及人物命运历程,将韩家民族资本的兴衰与历史变迁结合起来,折射出民族资本发展的种种矛盾冲突。《尘埃落定》以一个傻儿子的视角去展现各个土司集团间、土司家族内部等矛盾,从而揭示土司制度必定走向衰亡。
我们认为,一定长度的时间构架为家族剧提供了充分言说的空间,所以,家族剧不仅可以包容丰富复杂的历史、时代、人性、文化,而且可以从容地结合家族生活描写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家族剧在宏大叙事中糅进个人的记忆,在大历史背景、大时代格局中保留些许私人情感空间,这充分展现了人性美与人情美,更好地传达人性含义、社会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这样的家族剧既是具有史学价值的,也是具有艺术价值的。
二、叙事色彩的悲剧性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将悲剧作为“一种特别的艺术”进行了深入阐述,之后悲剧理论与美学内涵被不断发展与丰富。而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表述,悲剧的产生在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在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之外更强调了社会悲剧。而家族剧中所呈现出来的悲剧主人公,无不是在三种悲剧模式中泥足深陷、欲罢不能,最终在多重挤压下的人生夹缝中走向自己的宿命结局。这种人物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色彩为家族叙事涂抹了一层浓郁的悲剧基调。电视剧《红楼梦》中,“作者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揭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家庭一步步走向败落的必然命运,另一方面也无限深情地为这一正在一步步走向败落的贵族家庭献上一曲无尽的挽歌”,透露出浓重的时代悲凉之气。《乔家大院》中江雪瑛因爱生恨,得不到的便想极力去毁灭,但是这毁灭又充满了不彻底,先是使重金将初恋情人乔致庸送入“死牢”,却又将他救出,在爱、恨交织中备受煎熬。在贴身丫鬟要离她而去嫁人之时,她更是痛苦到竟然想把丫鬟毒死。人生最美好的爱情和友情都化作绵绵无尽的恨和悲,在扭曲的心理和分裂的人格中经受炼狱般的折磨。
正是家族剧弥漫的这种悲剧气氛,所以观众在同情这些人物遭遇的同时,也体验到了抗争的激情,即使这抗争很有可能是徒劳与无望的。《橘子红了》中的主人公们在封建枷锁中痛苦不堪,最后大妈不得已,在无望的努力中终于觉醒,决定帮助秀禾寻找真爱。虽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那样的一个家庭,最终抗争的结果依然是命中注定的失败,是以淋漓的鲜血和青春的生命为代价的。《中国往事》中的玉楠,本是一个知书达理、有着开明思想的新女性,嫁给从瑞典留学归来的曹家二少爷曹光汉本来也算门当户对,称得上是一对新人,可这恰恰成为她悲剧命运的开始。曹光汉一心革命,备受冷落的玉楠却在和瑞典技师路卡斯的惺惺相惜中产生了爱情,最终,路卡斯被处死,玉楠则用投井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美丽但绝望无助的生命。在这里,悲剧表现为对现实苦难的无力对抗又希图努力超越,用近乎毁灭性的方式来抗争,最后使有价值的东西得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正如鲁迅所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也正因为有价值,才更让观众有了种痛心疾首、撕心裂肺般的痛感与清醒。
有意思的是,现有的家族剧在表现这些悲剧时,往往采用虚实相生的手法进行,同时还配以相应的大团圆为结局,具有悲中见喜、悲喜交融的审美情趣以及相信善必胜恶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这与中国人追求平静、淡雅、中和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所以,即使观众在家族剧中体验到了较为强烈的悲剧性冲突,但这种悲剧感受却又被赋予了某种诗意的色彩。如《乔家大院》中常常以诗化场景和象征手法来表现乔致庸。剧中乔致庸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线头却被抓在别人手里,暗喻他一生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片尾已是垂暮之年的乔致庸和江雪瑛再聚首,没有多余的语言,似乎是个团圆的结局,但一切又尽在淡淡的哀愁中,令人欷歔不已。《橘子红了》把人物的活动场景安排在宁静的江南小镇,烟雾缭绕的田野、层峦叠嶂的大山,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好似一幅幅国画。尤其是秀禾手中的风筝,既是她对自由、理想和爱情的向往,同时也是她悲剧命运的载体。剧中的风筝是自由的暗喻,秀禾让风筝飞起来表明她向往自由和幸福,但风筝突然断了线,借此暗喻她已失去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凄凉的音乐循环往复,虽加剧了悲剧的悲怆感和苍凉感,却又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应该说,其写实和写意紧密联系的镜头语言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审美境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家族剧的美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