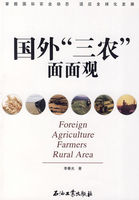由于集体建设土地流转的自发性和不公开性,交易中由于双方都要承担不同的风险,使得交易价格难以反映公开的市场状况,也使得价格难以起到对市场的信号和调控作用,不利于形成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集体土地价格的形成,目前主要是两种方式,一是政府征收或征用土地,按照政府制定的标准统一补偿的价格,这可以看作是购买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价格;另一种是集体土地所有者(集体组织或农民个人)私自将土地流转,双方达成的协议价格。无论哪种方式形成的价格,都不是健康市场自发形成的价格。前者价格的决定权在于政府,后者看起来是市场价格,但是由于存在风险(违反法律等),所以也在真正的市场价格的基础上打了很大的折扣。根据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城乡结合部土地价格课题研究小组所做的土地价格调查结果,集体土地出租的租金仅是土地市场租金的1/3或1/2;在地理位置相差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个案土地出租租金差别相当大,能够差到10倍,这是土地价格机制没有形成或不完善的直接结果。隐性交易带来了土地交易价格的随意性,也导致了不公平性,使一部分人侵占了另一部分人应得的利益,最后必然使市场出现混乱(吕萍等,2004)。
在市场经济中,土地作为财产如果属于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则其交换双方在经济和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双方通过谈判协商确定土地的交换价格;而多个购买者和多个出卖者的竞争,使土地价格达到均衡和合理的水平。农村土地在集体和国家之间的交易,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依法征用集体土地,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国家给集体土地确定的是补偿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即低价征用;而各地将征用的集体土地有偿出让工业、房地产、商业、金融和其他服务业时,高价出售。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财政和有关政府部门在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转变为国有土地时,从集体土地中转移了巨额的价值(冯尚春、江学俊,2005)。地方政府以“公益用地”名义进行征地后,按照农用地标准对农民进行补偿;然后以非农用地名义出售给经营性组织,按照土地市场价格获得回报。在较低的征地补偿标准和较高的土地市场价格之间,存在着巨额租金,地方政府获得的高额租金与农民得到的较低补偿形成鲜明对比,激化了农地征收征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城市过去农村被迫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向城市提供农业剩余,以积累工业资本,现在则被迫通过土地的不平等交易更多地向城市提供资源,以快速低成本地实现城市化。有的学者在分析产权不清造成的影响时指出,现在许多地方只要戴上国家建设用地的帽子,就可以“依法”征用集体土地,把土地当成一种无商品属性的自然资源,纳入到计划管理的轨道,这显然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据统计,1987—2002年,全国非农建设共占用耕地3689.4万亩,各地政府从农民手中获得的土地净价差收益在14204亿至30991亿元。190在农地非农化过程中,绝大部分收益被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拿走,农民和集体拿到的收益仅为15.66%。而且一些被不平等征用的土地并不是用来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发展公有企业,其中许多成了非公有企业,甚至私人资本的财产来源。这种利用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价格差来剥夺农民、发展城市的做法,与过去政府利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发展城市异曲同工,完全不符合“两个趋向”的精神,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规模化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价格还经常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土地所有权交易是典型的行政性垄断市场,国家既是土地产权市场的宏观管理者,又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市场的唯一需求者和城市土地市场的唯一供给者。根据现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农地征用的主要理由是“公共利益”,但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土地管理部门在法律条文和实践过程中都未进行明确界定。按照经济学基本理论,“公共利益”的经济内涵是“公共物品”,即使在经济学界对此也存在不同解释。在征地实践活动中,部分地方政府更是出于各种目的任意解释“公共利益”,以此作为农地征用和低补偿标准的政策依据,从而以较低经济成本取得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以公共利益为名多征多占农用土地,然后通过土地出让,获得了大量增殖收益,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这实质上是政府滥用征地权并构成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在农地非农流转过程中,通常没有进行公平公正合理的土地资产价值评估,而是由地方政府越俎代庖,根据每年的农业经营收入确定租金。由于地方政府“政治企业家”的特性,往往通过低估土地资产价值,以优惠价格来吸引外来投资,这类优惠和补贴造成了土地的粗放和低效利用。集体农民修建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土地租赁时往往没有纳入土地租金的计算之列,使外来投资商获得了土地附属物的免费使用权。实践中,许多投资商在获得土地使用权后,将耕地改为果园,或者农业生态观光园,将农业用地改为工业用地,获得由此产生的巨大增殖收益,变相造成了农民土地收益的流失。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廉价和方便占用农地之目的,将土地流转当作什么东西都装的筐,使集体土地流转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有的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甚至采取高压手段,以至动用国家机器强迫流转,严重侵犯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有的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甚至吃喝玩乐的小金库,不惜手段与民争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有的强行将农户的承包地长时间、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严重影响了农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有的为了大幅度地降低建设成本,并方便快捷地取得占用大量农地之目的,以不规范的集体土地流转机制或者入股制变相取代国家征地制;有的为了降低开发成本,更多地招商引资,借土地流转之名,随意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并强迫农民长时间、低价出让土地经营权。在农地使用权流转中,大多采取一次性流转,补偿费过低,安置简单,农民长期利益得不到切实保护(朱林兴,2002)。事实上,一些地区在征地实际操作中还存在多征少补,层层克扣安置补偿费等现象,致使本来已经微薄的补偿变得更加微不足道。集体土地流转的严重异化,严重违背了集体土地流转本来涵义和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本质上是对农民权益的一种侵犯,是对农民财产的一种剥夺。随着城镇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农用地的非农化使用规模越来越大,违法转让和剥夺土地承包者受偿权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土地向非农业用途转移过程中的行政性的隐性再分配及其腐败现象,由此而引发的干群矛盾甚至冲突相当严重(张翀,2004)。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土地产权市场化不充分、不规范的结果,既有政府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性根源,又有城乡二元格局所遗留的体制性根源,但归根结底还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的残缺。市场是产权明晰与否的试金石,行政化的交易说明土地市场发育不成熟、不统一,交易价格偏离市场价格说明集体产权的不完整,政府对交易的干预说明产权主体不到位,交易程序的不规范说明产权不稳定、强度低。而城市化则把市场发育的城市和行政控制的乡村拉扯到一起,使得含糊不清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立刻显示出层出不穷的矛盾和问题。这正如巴泽尔(1997)所指出的,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和新信息的获得,资产的各种潜在有用性被技能各异的人们发现,并且通过交换他们关于这些有用性的权利,实现其有用性的最大价值。随着人们拥有的商品的权利变得更有价值,如果不进行更加彻底的界定,人们必定会对置于公共领域的财富进行攫取和竞争。在农地用途改变,新的资产价值凸显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非农用地或建设用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使农村集体土地拥有在国家规划管理前提下,自主转变用途和直接进入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权利。农村和农民获得相应的资本,充分发挥农村集体土地的资产效益,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促进城乡人口有序流动。在我国广大农村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形成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增加集体和农民对土地权利的行使。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单一的“国家征地”模式难以统筹考虑农村土地非农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地方政府、社区集体、农民三方利益主体的博弈,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权利不对等,使农村社区集体和农民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获得土地增值的利益,不利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针对当前土地征用过程中大量侵犯农民土地权益和农地流转不规范的现象,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年度供给计划的前提下,应当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采取土地所有权交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等方式,让集体农民自主地通过土地用途变更实现经济利益,这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有效保护集体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制度安排。同时,允许农民用其土地产权作为抵押物或信贷的担保,充分地实现与土地权利相联的潜在经济机会,扩大土地产权权益交易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