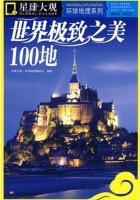第二,鼓励市场开发满足投资者多种行为需求的证券创新产品,改变投资者单一投资股票的市场结构。Bodie(2002)和Merton(2005)等人认为,证券创新产品为纠正投资者的行为偏差、减少市场的波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因此,证券监管者应该鼓励此类证券创新,而不是限制或者禁止。例如,为了满足中小投资者的投机心理,可以开发附加彩票的债券,即投资者在购买可以保本(甚至还支付利息)的债券的同时,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彩票;为了保证投资者未来的教育支出和养老支出,也可以设计附加教育保险或者养老保险的债券;为了满足投资者害怕风险、但又想赢利的心理,应该允许开发保本型理财产品(而在很多国家保本型是被严格禁止的);等等。
第三,改革“完全披露制度”,实施“实质披露制度”。实质披露不是追求尽可能多的信息,而是追求尽可能有价值的信息。实质披露一般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上市公司应该对重要的信息进行重点披露,而不是对信息不加区分地进行“平行”披露;第二,上市公司应该对上述重点信息进行解释和评述,以帮助投资者尽可能完整地理解该信息。实质披露的重点不是信息有多少,而是帮助投资者正确选择信息、正确处理信息(Troy Paredes,2003)。
第四,监管者的具体监管措施应该灵活地考虑投资者的系统偏差。例如,为了减少投资者的损失厌恶,政府可以考虑实施非对称性的税收政策,在牛市期间对买入征税、卖出免税,以减少投机性买入,在熊市期间可以考虑对卖出征税、买入免税,以减少恐慌性卖出(Camerer、Issacharoff、Loewenstein、Donoghue、Rabin,2003);为了改变投资者的框架效应,监管者应该特别注意监管措施的表达方式和出台时机,避免投资者将监管措施与特定市场背景联系在一起,政府应该避免在股市重大时刻出台重大监管措施,所有监管措施的出台都应该事前征求投资者的意见,并提前公布出台时间表(Cunningham,2001);与此同时,为了防止投资者对监管措施进行“有偏理解”(信息可得性偏差),所有重大监管措施必须详细说明其对市场带来的包括好的后果与坏的后果在内的所有可能后果(Kooreman、Prast,2007)。
第五,开展投资者教育活动(Investor Education Program,IVP)。长期来看,投资者教育是监管者纠正投资者非理性行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很多行为金融学家认为,投资者教育往往仅关注投资技巧和证券市场基本的法律法规,没有教育投资者深入了解投资的风险以及与风险相关的投资的复杂性,其错误正如汽车制造商只说明汽车的构造和汽车的速度,而不说明每一速度下操作的难度和相应的危险,因此,投资者教育的重点不是教育投资者知道买卖是什么,而是教育其知道买卖的结果是什么(Langevoort,2003)。另外,也有行为金融学家指出,很多投资者教育活动忽视了对投资者认识自己并勇于承担责任的教育,仅仅认识市场是不够的,还要认识自己,因此,投资者教育应该大力宣传行为金融学的知识(Greenfield,2001)。
四、当监管者非理性:基于行为金融的新反干预主义
(一)监管者的非理性行为梳理
投资者可能非理性,监管者也同样可能是非理性的。具体而言,监管者的非理性大致有:
1、过度自信。相比一般投资者,监管者更加容易过度自信。在判断市场的时候,监管者往往显得非常的武断和专横,这意味着监管者设置了过窄的置信区间,而这正是过度自信的典型表现。监管者过度自信的另一个表现是频繁干预市场,它可能下意识地认为它的每一次决定都是正确的,而且它有义务把正确的决定强加给市场。监管者的过度自信几乎总是导致监管者以居高临下的自负形象出现在市场上(Hill,2004)。
2、损失厌恶。为什么证券领域更容易出现“大而不倒”的现象呢(too big to fail)?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证券监管者存在严重的损失厌恶症。与一般的投资者急于扳平、结果持有一项亏损资产的时间过长、反而导致了更大的损失一样,证券监管者对那些已经产生严重问题的证券机构(例如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对冲基金),也难以下定决心在事发之初就关闭这些机构,结果也是损失越来越大,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引发金融危机(例如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金融危机)。相比而言,监管者在关闭小型证券机构时就果断得多,因为监管者更容易接受小型机构关闭出现的小额损失(Glaeser,2006)。
3、锚定效应。监管者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监管行为与某一特定目标或者某一特别判断挂钩,从而导致过度监管或者不当监管。例如,在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很多监管者都不自觉地将其监管行为与市场指数挂钩,将其政策措施锚定在某一具体的指数范围内。又如,监管者可能先入为主地认为曾经出现过危机的证券机构具有更大的风险,从而强化对这些曾经有风险的机构的监管、忽视对那些现在有风险的机构的监管,这种行为的实质也是将监管政策与发生过危机的机构可能风险更大的潜意识进行了锚定(Jolls,2006)。
4、信息可得性偏差。尽管绝大多数证券监管者自认为它拥有更多的信息(所有的证券机构和上市公司必须向其吴保留地报送信息),并处于中立地位,因此,监管者对信息的判断更加的准确和全面。但是,监管者在处理信息时同样不能避免可得性偏差的困扰(Jolls,2006)。例如,如果监管者认为某一监管行为没有风险的时候,监管者可能只会收集有利于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而忽视或者抗拒相反的证据(证实效应)。相反,如果监管者认为某一监管行为存在风险的时候,监管者则很可能只收集存在风险的证据,而忽视风险可控的证据(证伪效应)(Mitchell,2002)。
5、从众效应。在有些时候,例如市场发生重大转折时,监管者很可能不会明确表达与市场相反的观点,而是跟随市场主流意见,表达与媒体和受媒体影响的一般社会公众的意见一致的监管意见。监管者的从众效应可以帮助监管者逃避发表或者实施与市场主流声音不一致的监管政策可能带来的失败的风险,但是监管者的从众效应,却使得证券市场往往只存在一个声音,而这往往是市场处于极度危险的征兆(Choi、Pritchard,2003)。
6、推卸责任效应。与一般投资者一样,当面临监管失败的时候,监管者也可能责备他人、推卸责任。Kane(1997)总结了监管者四种推卸责任的方法,并将其称为监管反射,包括:①“蒙蔽反射”(blindfold refelex),监管者声称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②“掩盖反射”(Cover-up reflex),监管者拒绝披露事实的真相,极力掩盖真相;③“分散注意力反射”(distraction reflex),监管者将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从而逃避指责;④“替罪羊反射”(scapegoat reflex),监管者将罪责推给替罪羊,从而大事化小。不难理解,如果监管者一味责备他人、推卸责任,监管者同样不能从已有的监管失败中学习到有价值的东西,难以真正提高监管能力。
(二)新反干预主义下证券监管的对策
对政府非理性的研究,似乎会强化古典自由主义“政府不得干预市场”的结论。但是,绝大多数行为金融学家反对将上述逻辑简单化,而是认为,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政府非理性的程度可以减轻,有些非理性行为甚至可以完全消除。因此,不是反对政府干预市场,而是反对政府“武断、想当然和情绪化”地干预市场,以“(政府)非理性对抗(投资者)非理性”(Choi、Pritchard,2003)。Jolls(2006)将政府非理性下的证券监管理论称为“新反干预主义”。具体而言,针对政府非理性,行为金融学家提出了如下的对策建议:
第一,监管目标唯一化。任何国家的证券监管者都不应该对证券市场进行价值判断,即监管者不能代替投资者对市场涨跌进行定位(过度自信+锚定)。减少政府价值判断的一个最好办法是将监管者的目标唯一化,监管者只负责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即充当证券市场的警察(Shiller,2001)。
第二,减少干预的次数。Choi、Pritchard(2003)认为,尽管监管目标唯一化是一个克服诸多政府非理性行为最为理想的办法,但是很多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本身就是证券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者,应该尽量减少干预的次数,因为干预的次数越多,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越大;而且如果频繁干预带来的后果是一错再错的话,这些错误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纠正。
第三,提高监管透明度。任何一项重大监管措施的出台,都应该事先广泛征求包括行业、投资者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多方面的意见,最终的决策也应该综合考虑上述多方面的意见。提高监管透明度,是减轻监管者监管责任的一个有效办法,同时也是提高监管者声誉的良好办法(Bainbridge,2000)。提高监管透明度已经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用,例如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我国香港地区,任何监管规则的出台或者修改,都必须事先公布其预案,公开征求意见,并对最终方案进行详细的说明。
第四,建立有弹性的监管纠错制度。Langevoort(2003)提出应该从三个方面建立有弹性的监管纠错制度。首先,建立证券监管的质询制度,政府其他部门(例如财政部)或者国会应该对所有重大监管制度进行事前的听政或者质询;其次,监管者在实施监管行为时应该留有足够的伸缩余地和变更空间(例如应尽量避免采取僵硬的税收、货币政策干预市场,多采用改变市场预期、调整市场信心的市场化措施);最后,监管者在出错以后,应该勇于公开承认错误,并纠正错误,而不是以种种理由(特别是所谓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拒绝作出政策调整。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行为金融学家还给出了其他的建议。例如,Prentice(2001)提出应该在投资者教育活动中公开说明证券监管的局限性,说明监管者也可能是非理性的,与此同时,监管者也不应该把自己打扮成超越于证券市场的理性人;Croley(1998)则提出监管决策应该采用集体决策制度,而不是象当前美国证监会(SEC)那样由下属的部门分别制定并决策的制度;等等。由于篇幅的原因,其他更多的建议此处不再详述。
五、小结
将非理性纳入到证券监管的研究,至今不过10余年的历史,是当前证券监管最为前沿的课题之一。行为金融学为重新审视证券监管提供了多个崭新的视角和革命性的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指出了“非理性”是证券监管的内生条件,这既包括了投资者非理性,同样也包括了监管者自身的非理性;而在15年前所有正统的监管理论都还建立在“法玛虚幻的理性世界”之上(Shiller,2002)。正是基于上述意义,Langevoort(2003)将基于行为金融学的证券监管理论定义为“非理性博弈非理性”的研究。
当然,通过行为金融学的视角研究证券监管还处于初步探索的阶段。在很多时候,行为金融学只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法;而在其他时候,行为金融学甚至给出了完全对立的解决方法。行为金融学没有给出一套系统的对策体系,被有些行为金融学家认为是当前证券监管引入行为金融学的一个重大障碍或者缺陷(例如Mitchell,2002),不管是新干预主义者还是新反干预主义者,他们的主张基本上都是个案的、具体的,不具有广泛性。因此,越来越多的行为金融学家认识到,未来的研究应该朝向建立系统化、整体化、逻辑化的方向发展,即从整体化、系统化层面为证券监管给出行为对策和行为解决方案。
相比而言,我国当前的证券监管还很少涉及对投资者的行为研究,对监管者的行为研究更是罕见。这种缺乏行为视角的监管理论,依然属于以有效市场理论和市场理性为立论基础的传统监管理论。但是,我国证券市场远不是有效市场,规模庞大的投资者也远不是能够充分认识投资复杂性、并愿意自负投资责任的理性人。这意味着,如果要建立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初级发展特征的证券监管体制,证券监管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当前及其后一段时间市场的非理性、投资者的非理性(包括机构投资者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