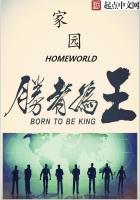“我想知道你的名字哦!”眼前的女孩子穿着和我一样破烂而又肮脏的衣服。褴褛的衣裳耷拉在她的身上,耀眼的霞光和火光照亮了她白皙的脸庞和杂乱的头发。
真对不起啊,我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可以用来说话的舌头呢。
女孩子熠熠发光的双眼盯着我,嘴角咧着欢快的微笑:“你也是从那座燃烧着的巨塔里逃出来的吗?
“我们,一起回家吧!”女孩子自说自话地牵起了我的手,我们在村庄荒无一人的小道上奔跑。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手上也有着与我一样的手环扣着,她也是拼命挣扎着才脱出这捆缚着她的锁链吗?她,也是鬼的孩子吗?
我和她一起奔跑在夕阳燃烧着的村庄中。既没有目的地,也不知疲倦,身后是燃烧着的村庄和在大火中挣扎呻吟的人们,混杂着木材燃烧发出的噼啪声被我们远远地抛开,我们就这么被吸入晚霞中不知所踪。
我什么都不知道,但仅仅是与你在一起的话就好了。如果这个世界除了我与你之外的人类都不存在就好了啊。
多年以前的故事:
木制的车轮在黄色的土地上碾过,留下深深的车轮印。车厢里,鸩安看着身旁靠在自己肩上熟睡的女子,女子姣好的面容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安静地车厢里只有女子安稳而又韵长的呼吸声。他想起多年以前,是同样幼小的她牵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出这大山深处,去面对外面的风风雨雨。那时她曾笑着问他,“以后到了大山外面,我保护不了你了怎么办?”
“那就换了我来保护你。”他昂起小小的头,坚定的目光看着她。
无论多少次,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来保护你。
过去的记忆一丝一痕地在脑海里划过,他认真地看着女子熟睡的面庞,认真地回忆着。马车突然在岔道前停了下来,车夫恭敬地站在一旁,将他的行李从车厢里静静地提了出来,并且准备将他搀扶下马车。
我会一直保护你,只是这一次,我必须要离开了。你,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他紧张地理了理身上的白衣,叹了口气,慢慢地踏上岔道的一端,不紧不慢的布履,一如这些年一直以来的样子,无论是当初离开大山,还是后来为她逃离而共同浪迹天涯,又抑或是现在被整个家族流放。他似乎总是那么从容,好像没有什么能够真正困恼到他。头也不回,他白色的身影消失在漫漫群山之中。
岔道的另一端,马车又开始轱辘辘地向前走着,扬起漫道的黄沙。车内原本熟睡的女子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她本来就是十分聪慧的女子,先前鸩安的离开她又怎么会不知道。她只是在害怕,害怕鸩安真的会像以前那样,什么都不责怪她,只是用安详的眼神定定地望着她,包容她所犯下地所有错误。一滴,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的脸庞划过。掀起车帘,她看着鸩安的身影消失在漫漫黄沙道的另一端。她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因为她,他又怎么会被家族虐待至此。她原本期冀自己承担下所有的罪责,家宅前他的一跪却打碎了她的期望。她不想,她又怎么忍心,让她最爱的人替她受最重的伤?
但是,他又怎么忍心,就这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从此与君别。
此去经年,但见天边孤鹜独飞,独不见君白裳猎猎。
最后的的故事:
风尘仆仆,鸩一个人慢慢走到了熟悉的岔道口,连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他想起这是很多年前一安带着他逃走时路过的岔口,也是鸩安带着他离开时走过的岔口,他好像记得当时鸩安在这里站了许久,神情悲伤。以前他总是会对此感到疑惑,现在他知道了一切,却没有了疑惑得解的欣慰,只是感到无限的悲凉。偶尔有风吹过,扬起满地的尘沙。
自那以后,一安最终在他怀里死去的情形总会浮现在他的脑海,这犹如有人在他的脑海里一直不停地用着一把大锤捶打着他,时刻警醒着他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害死了她。
时近黄昏,天边开始出现一抹抹红霞,仿佛是要将这苍穹点燃一般。
哦,是她回来了。鸩这么兀自想道。他仿佛看见,一安绯红着的脸,重新扑进他的怀里。在这空无一人的旷野中,鸩被吸入无名晚霞中不知所踪,就好像没有人曾出现在这荒山之中一般,就好像这么多年的恩恩怨怨从来都没有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