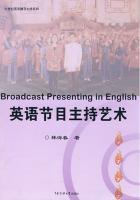因为自愈能力,吕薄冰的伤痛很快复原,心却是无比的疼痛,正黯然失神间,忽听见身后有动静,知是姐姐来了,忙扭头看了一眼。
吕能静身材高挑,气质出众,一脸疼爱的看着弟弟,柔声道:“你还好吗?”
人面桃花里,浅笑如酒,她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理解弟弟,心疼弟弟,感同身受。
终于,心痛,心碎,心成灰,吕薄冰哭了:“姐姐,呜呜呜,我错了……”
流年的转角中,总有许多镜中花,水中月,美丽而虚幻。
“没事的,冰儿。”吕能静静静坐下,拥他入怀,掏出锦帕替他拭去泪水,安慰道:“这不是你的错,一切有姐姐,明天你回乡下,好好歇歇吧。”
“那姐姐怎么办?”吕薄冰把头靠在两座隆起的山峰里,仰望着姐姐,那张少年老城的脸一阵抽蓄,甚是不安。
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前他是姐姐的骄傲,从今日开始,他就是姐姐的耻辱。每个人下意识里都愿意作为亲人的骄傲,而不愿作为亲人的耻辱,这是天性。
吕家一门三兄弟,俱在教中任要职,除了吕父已驾鹤仙去,两个叔叔都是长老,而姐姐吕能静更是副教主,别人虽不敢明面上说,但背地里却不知如何嚼舌头。所谓人言可畏,莫不如此。
一个人想要做好自己,那是很难,更多的时候是在别人的口水和质疑声中成长。有时候,我们必须闭上嘴巴,放下骄傲,承认是自己错了。这不是认输,而是成长,那些打不到你的,最终都会成为你的垫脚石。
其实,严格来说,吕能静并不算吕薄冰的亲姐姐。吕父原是紫月教第三分坛的一个副坛主,与妻子相敬如宾,然与两个弟弟子孙满堂不同,竟无一儿半女。无奈之下,吕父只得从一远房亲戚那抱了一女儿。
说也奇怪,在女儿九岁的时候,年近五十的吕母竟然怀胎,十月之后生下吕薄冰,人人都说他是一朵奇葩,要么是天纵异才,要么是一痴呆儿。
吕能静从小聪慧,十几岁便顿悟浩气,入教供职,八年之后脱颖而出做了副教主,而吕薄冰却差了很多。虽长相俊朗,也颇有豪情壮志,但除了读读诗书,研究医药,在武功修为方面倒是没什么长进。
以至于到了十四岁,虽然医药成就惊人,但还是默默无闻,而那时父母已双双去世。
人说长兄如父,吕能静却是长姐如母,她见吕薄冰很忧伤,笑了笑:“傻冰儿,姐姐是大人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亲吻了他额头一下,“虽然不知道你这是怎么了,但你永远是姐姐的好弟弟。”
吕薄冰愧疚不安,哭得更大声,吕能静轻拍他肩膀,疼爱有加:“好冰儿,姐姐知道你委屈,既然伤心,就好好痛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哭出来你会好一点。”吕薄冰把头埋在她怀里,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不管昨夜经历了怎样的泣不成声,早上醒来这里依然是空气清新。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吕能静便起身送吕薄冰到乡下。那是一个三百里外的小乡村,吕氏老宅在那,很多年以来,吕家都在紫月教总坛居住,很少有人回那里。
这次,因为迫不得已,吕薄冰已经无法在总坛待下去,也无法再面对其他教众,最好的方式是去乡下,从此躬耕苦读,期待有朝一日能不能出现奇迹。即便没有,也可以远离非议,毕竟那里的人是淳朴的村民,并不知江湖事。
姐弟二人骑马出发,马蹄踩在结满薄冰的路面上,吱吱脆响。如若能安然回去,那大约也是极好的。但,天有不测风云,出总坛还没五里,迎面遇见五个人。
五位少年!
领头的正是李天龙,其他四位也是聂凤的爱慕者。李天龙料到吕薄冰会一早离开总坛,昨天就鼓动其他少年拦截,意图羞辱吕薄冰一番,更要让他退了婚约。
只要退了婚约,聂凤还是他的,少年们心知肚明,聪明一些的,不愿意掺合。只有这四人,实在被单相思蒙蔽了双眼,十分不甘,在李天龙的鼓动之下,一早便来了。其中一人,还是吕薄冰堂弟。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五人一见吕薄冰,眼睛唰地红了,特别是李天龙,杀机浓郁。
吕薄冰并没把这些人当仇人,或者说,以前根本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但,五人拦路,自己又没有战力,只得看向姐姐。
心如薄冰,随时会碎裂。
深秋的黎明,霜雾正浓,落叶萧萧,寒意直透人心。秋霜打着人的脸,深灰色的迷雾充斥着天地,无情的秋天剥下一排排树木美丽的衣裳,它们枯秃着,阴郁地站着。
湿气在蔓延,人心在冰冷。
吕能静面色一沉,目光如电,扫过五人,轻叱道:“你们要干什么?”
吕能静之威,紫月教皆知,其他人有些心慌,纷纷避开眼芒,唯有李天龙,并不躲避,冷笑道:“吕副教主,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好像不干你的事。”
“大胆!”吕能静面色阴沉,喝道:“李天龙,以下犯上,你是在找死吗?”
“不敢。”李天龙不为所动,苍白的脸色因激动红得有些不正常,阴阳怪气地道:“吕副教主,我再强调一遍,我们的目标不是你,你可别仗势欺人。”
“你!”吕能静语塞,干生气,却不好发作。李天龙言语虽不敬,但没动手,她还真不好先行出手。
“李天龙,你想干嘛?”吕薄冰面色清冷,不能不出声了。
“吕薄冰,你也有今天。是个男人,就别靠女人保护,与我打一场。”李天龙故意刺激吕薄冰,挑衅地道:“输了嘛,跪在地上给我们磕三个响头,说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配不上聂凤,然后在这上面按个手印。”
李天龙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了不少字,看样子是悔婚书之类,这是逼吕薄冰与聂凤断绝干系。
“李天龙,别欺人太甚!”别人如此欺负弟弟,吕能静忍无可忍,顾不得身份,怒声道:“有种冲我来!”
“你可是堂堂副教主大人,我李天龙自视不敢冒犯。”李天龙把纸张收起来,摆了摆食指,阴笑道:“有人愿意做缩头乌龟,躲在女人的庇护下,那也随他。”
“找死!”紫光闪烁,吕能静脸色铁青一掌挥出。若是旁人,她早一掌把对方拍死,但这涉及男女之事,又是本教中人,出手还是留了分寸。
哪知李天龙不躲不闪,任由紫气击中,仰面倒了下去。其他四人吓得面如土色,人人后退,惹恼了吕能静,即便四人一起上,被杀也是片刻之间,他们怕了。
但李天龙却站了起来,抹了抹嘴角的鲜血,狞笑道:“吕能静,有种你打死我!看看我是不是个男人!”
“好了,李天龙,你别嚣张,我跟你打!”经年,流殇漠漠。侮辱男人的自尊,再不出面,实在说不过去,吕薄冰翻身下马,沉声道:“姐姐,让我来。”
“这?”清殇如水,流逝的痕迹深深入骨,吕能静情知不好出头,强忍着冲动,暗暗盘算着:“就让冰儿吃点苦头吧,对他而言,也许并非坏事。少年成名,一鸣惊人,也需要磨砺一下,将来还不知道要吃什么苦,只要李天龙不下死手,干脆静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