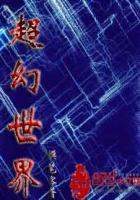我运起纯阳归一功,按八爪舅的指示,一头撞向旱魃。把旱魃撞在大厅石壁之上,成了一滩杂碎。八爪舅抡起胳膊,扬言要让旱魃永不翻身。
八爪舅的胳膊越抡越快,抡得风起尘扬,他说:“各位退后,小心伤着。”我们退在后面。
我眼睁睁看着八爪舅的胳膊化为一圈残影,周围开始飞沙走石,小石子打在我脸上隐隐生痛。我再瞅瞅其他人,都衣袂飘飘的,脸上清一色大写的惊诧。
继续抡。又过一会儿,我已经退出好几丈远,模模糊糊看到墙上旱魃的碎块就要凝聚成型了。
只听八爪舅喝一声:“着!”
“咚”一声闷闷的大响,有如洪钟大吕近在咫尺,震得我气血上涌。紧接着一股遒劲的狂风,“呜”,吹得我连连退却。周围的大灯都被掀在半空,一阵乱耀。等到风平息了,半空的灯一个个掉下来,摔碎不少。我定睛一看,大厅的墙壁大半都在剥落,以八爪舅面前的为中心,越往外剥落的越慢。
我跑到八爪舅跟前,只见墙壁上有个拳头大小的窟窿。我伸伸舌头说:“舅,你用拳头捅的?”
八爪舅点点头。
“你这一拳威力好大。”我边叹边观,剥落的石壁掉在地下立刻腾起细烟,碎得像面粉一样。再看本来在墙上的旱魃,早已混在面粉一样的石末中,没得不能再没了。我说:“刚才我撞向旱魃,他身周阴煞火突然被驱散,是不是你出拳打得?”
八爪舅点点头。
师傅、周门他们都过来了。师傅说:“徒弟他舅,你这一拳真有排山倒海之势。老朽走遍东南西北,天下的武功各门各派都有见识。能打出像你这一拳的,北有雪山派,可他们是大范围的冻伤。南有万普寺的大金刚般若拳,但刚猛有余,不似你这样暗含阴劲。恕我眼拙,实在看不出这拳的出处。”
我说:“俺舅无门无派,全是靠自己琢磨。”
师傅等人哑然失语,半晌,眼里都露出敬服之色,连说:“奇才奇才。”
那黄戍人更加夸张,对着八爪舅噗通跪下,嘴里说道:“祖师在上请受后辈一拜。”然后咚咚磕头,“今日得见祖师大显神威,实在是三生有幸,四生福气,五生沾光,六六大顺……”他又是拜又是讲,行无方寸,语无伦次。师傅拽住他说:“老黄,你搞什么鬼?谁是你祖师?你不是自学成才,走得能掐会算的路子吗?”
黄戍人唯唯诺诺站起来道:“不要说不要说。我这两下子比起天……”他小心翼翼看看八爪舅,“比起这位真是小巫见大巫。”
八爪舅也不吱声,从刚才起他就一直在沉思,估计是又在盘算什么。
我把食指竖在嘴上,对黄戍人说:“嘘,黄师叔,我舅在想东西呢。”
没想到黄戍人双膝一软,噗咚又给我也跪下了,说道:“剑祖教训的是。一通话语简直醍醐灌顶,让小可诚惶诚恐。望乞见谅。”嘭嘭嘭给我来仨响头。
要说这黄戍人,满脸都是鱼尾纹,头发七分花白,二分半白,剩下一分黑里透白。怎么看吧,年纪只在我师傅之上,不在我师傅之下,五六个我加起来,岁数恐怕才和他有的一拼。他这对我一跪,折我寿不说,我骨子里的尊老观念不可遏制地警钟大作。我吓得噗咚也给他跪下了,不叫师叔,张口就叫爷爷。“黄爷爷,使不得使不得,你这不是埋汰我吗。我哪里不对你直接说就是。你这样,我心里那叫一个胆战心惊、惊慌失措、措手不及……”
师傅连拉带扯把黄戍人拽起来,“老黄你没发烧吧。这是我徒弟,你给他下跪,让我如何处之。辈分乱啦!”
黄戍人只知点头,还不住说:“见谅见谅。”
周门对八爪舅说:“这一拳真真有惊神骇鬼之威。谁能想到旱魃之祸竟被一拳扫除。呃……贵姓?”八爪舅犹在走神,周门把头转向我。我说:“俺舅姓姜。”
“姜老师真是慕安的救星!”
周门又说:“这地方不易久待了,咱们出去再说。”带头领着大家出去。
原来这地下的古墓大厅被八爪舅一拳轰得,不论上下左右全都外软内酥。四周和顶上“啪嗒啪嗒”往下掉皮子和杂碎,粉末扬得到处都是,再待一会恐怕就要糊个满头满脸。
我看八爪舅没动弹的意思,想等着他。丙乌拉都走出去两步,又回来拉我。“走啊,等着天上掉钱吗?”
“我不走。我舅不走我也不走。”
丙乌拉都大刀一扛,去拉八爪舅,“大叔,快走吧。”看得我眼皮直跳,心想这闺女够彪。
我把丙乌拉都推到一边,“你别打扰我舅,没看我舅正在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为民绞尽脑汁吗。”
丙乌拉都一口大气差点没喷出来,“得得,你厉害。你走不走吧。”
“不走!”
丙乌拉都俏脸一青,在仅有的灯光下显出可怕的狰狞,举起刀来说:“信由尔,别把别人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快走!”
我一缩脖子刚要答话,没想卜彩瓶也回来了,说:“信由尔你还没走呢。”丙乌拉都立刻把刀放下说:“切,爱走不走,不管你了。”白我和卜彩瓶一眼,自顾自走了。
卜彩瓶问我:“你还不走啊。”
我指指八爪舅说:“等俺舅。”
卜彩瓶点点头说:“那我也等你们。”
这时大厅里扬得到处是灰,视线越来越差。卜彩瓶拿出一个瓶子,里面是刚收的阴煞火,她说:“阴煞火在火单上排名九十八,是进到前百名内的奇火,可遇而不可求。不如我来试试看,是否妙用无穷。”说完她拔开瓶塞一抖,把一条黑呼呼的黑河抖了出来,划在空中。黑河所过之处,扬尘一扫而空。卜彩瓶说:“阴煞火形如水浪,烧起来有滔天之势,乃是大恶之人修炼出来的心火,能将所触之物化为同质。一旦沾身,融肉蚀骨,歹毒阴损的很。”说话间阴煞火被卜彩瓶操控着,浮空连旋,好像是甩起来的一条超大号的黑毛巾。我看杂技一样,就差拍手叫好了。
卜彩瓶将瓶儿甩了几下,把阴煞火收回。“火单前百名的家伙果然不好控制。况且这味道实在不敢恭维。”
原来她把阴煞火一召出来,一股酸涩的味道就弥漫开来,直呛得我连打了几个喷嚏。卜彩瓶自己也不好受,手掩着鼻子,眼泪都流出来啦。
我说:“岂只是不敢恭维,简直需要退避三舍。用这阴煞火,熏也能把对手熏死。以后啊,卜大小姐你无敌了。干脆给你起个绰号,叫熏臭三里地。”卜彩瓶边笑边斜眼看我,也不说话,把瓶子收好。
阴煞火一消失,大厅里又开始石土飞扬。我看八爪舅还没走的意思,突然醒悟道:“不好!俺舅八成是又变傻子啦,得赶快把他扛走。”
我赶紧运起纯阳归一功,气运后背,走上前去搂住八爪舅往背上放。谁想八爪舅根本没傻,反手拍我脑壳一巴掌,说道:“好小子!我说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你在这儿坏我事!”
我马上呆立当场,摸不着头脑。“什么?舅你说什么?”
八爪舅看看大厅里糟糕的环境说:“先出去,等会再和你算账。走。”
出大厅,离开慕安地下工事,上得地面,当头看见丙乌拉都正烦躁地用刀点地。瞅我们出来,她把大刀一扛,眼睛对我一翻,“哼”了一声,扭头就走去巷子口。巷子口那里。周门和师傅他们都等着我们呢。
八爪舅走在我和卜彩瓶前面,我忍不住又问:“舅,你刚才说什么我坏事?”
八爪舅站住身形,仰天叹一声说:“旱魃并未被消灭。”
我心里暗惊。“舅,这话从何说起。我刚才明明看到旱魃已被你一拳打得渣都不剩。难不成那样了他还能修复?这样的话他就太逆天。”
八爪舅回转身对着我说:“他虽能重新恢复身躯,却不是在慕安。”
“咦?”我虽十分愿意相信八爪舅,但他说的话实在让人怀疑,我试探着问:“舅,一加一等于几?”
八爪舅骂一句说:“我清醒着。你个小兔崽子不盼着我好是吧。”
我脸一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卜彩瓶好像也笑了笑。
八爪舅继续说:“刚才我一拳捣出,满以为旱魃会彻底玩完,谁知他的一条胳膊鬼使神差地被崩了出去,从长平公古墓上面的大口子飞出去啦。”
我大吃一惊。“那赶快把那条胳膊找回来啊!”
八爪舅摇摇头。“唉,崩走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找不回来了。”
“为什么找不回来?”
八爪舅突然生气道:“还问为什么!我来问你,我给你的锦囊让你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拆开。你做到了吗?”
我搔着头说:“那没关系吧,怎么拆不是拆啊。”
“冥冥之中有万事相互牵扯。我本来已经演算的万无一失,谁知你提前打开锦囊,坏了环环相扣的步子,最终导致旱魃逃脱。”
八爪舅越说越气,抬起巴掌拍过来。我闪开,大喊冤枉:“你这不是让我背黑锅吗!你这是宿命论,想蒙小孩!”
八爪舅啐一口说:“呸,你铸成大错,我算出这旱魃将来还会倒打一耙。你瞧好吧!”说完忿忿地走了。
我们走出巷子,周门等在那里,对八爪舅说:“姜老师,不如去我办公的地方,咱们盘恒盘恒。”
我却先蹦起来大叫:“周大叔,长平公古墓上面的大窟窿开在哪里了?俺舅说旱魃的一条胳膊飞出去了,会再生的。”
周门一哆嗦,“什么!那赶快去找!”他赶紧安排人手去找。
八爪舅说:“不用找了,已经被人抢走。”
周门瞪着眼睛说道:“被谁抢走?”
八爪舅一指东边,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隔一重洋,双娇同煞。”然后眼睛一迷瞪,“小尔,背我回家。”就此迷糊过去。
……
经过这番折腾,政府下通知,让糊黑街搞个大拆迁,街上的住户无不欢欣雀跃,摩拳擦掌,准备狠狠捞他一把,好一夜暴富。
周门派人去找旱魃的那条胳膊。原来古墓本体在山根里,它上面便是五星级的慕山大酒店。这大酒店档次高,经常有外国客人来住。我用雷殛出的大洞正好在大酒店的院子里。找胳膊的人无功而返。
师傅临走前嘱咐我勤加练剑,还说乘血宝剑本就秉性难以捉摸,没了它安知非福呢。
八爪舅醒来和我说,黄戍人也是天星下凡,不过不在十二大辰之列,连小辰也不是,而是星。是北天斗量星群中的一员。上一次八爪舅察觉有人窥探天筹、天燧、天昙三星,从而摆下“迷踪幻影假身转格大阵”以防不测,就是这黄戍人搞鬼。八爪舅还说斗量星群以天昙为尊,所以黄戍人一见天昙星君,便吓得够呛,又是磕头又是赎罪的。
我问八爪舅那天为什么提天燧、描困二星,他却神秘一笑,埋头大睡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