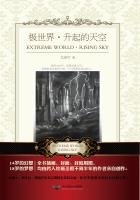浪涛中的第七道浪头一般被认为是最恶劣的,足以在海上强风中毁灭一切。但现代的海洋学家认为这不过是对大海的盲目恐惧,他们甚至可以用复杂的海浪理论和海浪力学来证明他们的看法。但是人们对第七道浪的戒慎依然持续,在大西洋暴风雨下滚滚浪头中的无盖小船上掌舵时,很少人能不聚精会神地数着浪头。每一次船头被巨浪掀高时,每个人都在心里预料着可能随之而来的毁灭。令人惊骇的灰沉海水延伸到地平线,滔天的浪头一座压过一座,每一道浪都带着吞没、翻覆和摧毁的力道。在船身陡降到浪谷的那一刹那,不论是真实或想像的第七道浪头,人们无不盯着这些怪物般的海浪带着令人丧胆的威胁,一波高过一波,操兵似的整队成列,甚至连地平线的形状都随之改变,然后潜沉,准备突击。
皮革船“布伦丹号”
在1976年5月下旬那被强风刮得残败不堪的晚上,对于我那颗疲惫的心灵来说,海浪的队形不断在改变:那不是第七道浪头,而是随机整合成一组组的三座浪头。每一组的先峰浪头朝我们滚滚冲压而来,并一路尽其力道抬升到极点,在失去了支撑之际,才猛然如崩倒之山,带着随之孕生的厚实白沫和全身力量漫天盖下。船身受到排山倒海的巨浪撞击时,无法自已地不断震颤和踉跄。舵桨在我的手中狂乱扭动,然后失去控制,我们连人带船被掀高,并急急地冲入湍急的猛浪之中。就在那危急时刻,强风也跟着抓向我们,扭拧着船身两侧,想要强使船身和浪峰平行。要是船身真的向左边或右边转九十度,我们必然葬身大海。紧接着,第二道或第三道浪头横扫脆弱的船身,每回我都惧怕这会是我们最后目睹的一道浪峰。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该如何驾驶这条船,也没有哪条船像这种船只一样,已经在水面航行了有将近千年的历史。在一般人眼中,她看来像一根浮在水面的香蕉:长而单薄,细瘦的船头和船尾以奇特的尖锥状微微上翘。惟有仔细观察她的人才会见到她的特别之处:这艘船是皮革做的。船身使用了四十九张牛皮如缝缀被面一样缝在一起,并用木架撑住。厚度大约仅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牛皮,在船只移动的时候,一如搭在人肋上的皮肤,在我们和暴烈的大西洋之间收缩移动。望着波浪,我想起了我们出航之前,一位世界皮革权威严峻的警告:
“牛皮的蛋白质成分非常高。”他以具有学理的严谨口吻说,“你可以这样想,它就有如一块牛排,依据不同的因素,例如温度、鞣成皮革的精细程度,以及外来的拉力,迟早都会分解腐烂。”
“皮革长久浸泡在海水里会怎样?”我问他。
“啊,这我就不敢说了。”他回答,“从来没有人要我们测试。但皮革受潮后通常更易破裂,而海水中的盐分可能有腌蚀的作用。我实在说不准??”
“最后的结果呢?”
“就像你把盛放在盘子里的牛排暴露在空气中,时间一久就会腐败糊烂,发出讨人厌的熏臭味。和腐烂的生牛皮没有两样。”
船身变得糊烂还不是现在的问题。强风逐渐加烈,浪头益形庞大。它们以更暴猛的力量向我们袭来,若是皮革船身不够坚固,我们马上要面临的就是缝线由牛皮最脆弱的地方裂开,就像我们拉开厚纸袋上的缝口线那么容易,然后,牛皮将会像花瓣散落,而其下的木架则将在瞬间怒放如花。不过我心里倒不真觉得会如此,反而是翻船沉没的几率较大。我们的船底没有龙骨可以保持平稳,所以一个滔天浪头打下来,她将会被搅得肚皮朝天,而船员则翻落入海——两者幸存的希望都很渺茫。
那我们何苦驾驶这么一艘极不合适的船和逐渐强劲的大风交手?答案就在我们这艘奇特船只的名字:“布伦丹号”(Brendan),用以纪念6世纪伟大的爱尔兰修士圣布伦丹。传说,圣布伦丹曾经驾驶船只前往美洲。这可不是神话狂想,而是据考证至少完成于公元800年的拉丁文文献所得到的重现话题。这些文字也说明了圣布伦丹等修士如何乘坐一艘皮革船横渡大海到达远方的大陆。当然,如果这些说法都是真实的,圣布伦丹必然比哥伦布早一千年,也比维京人早四百年就到过美洲大陆。质疑者认为这样的主张根本是过于轻率。乘坐用兽皮做的船横渡大西洋,简直不可置信,有如幻想,而且用皮革造船的说法本身就很荒谬。但是,那些拉丁文文献对于使用皮革造船一事却很肯定,甚至清楚地指出圣布伦丹这群修士曾经建造了这么一艘船。很显然,要证实这个非凡的故事,只有仿造一艘样式相近的皮革船,看看是否能够渡过大西洋。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了。我和一群伙伴正在海上实验,想要知道圣布伦丹和那些爱尔兰修士是否真能以皮革船远渡重洋。
再也没有比这时候遭逢强风更糟糕的事了。我们的探险才刚开始,“布伦丹号”还没有经过实际的测试,航离圣布伦丹那崎岖的爱尔兰大西洋岸故土也才三十英里。三十英里可真令人汗颜。对于航海家来说,这是一处必须崇敬以对的海岸。西南风终年袭掠,许多帆船在这里失事,它们在横渡大西洋后船身黏生了海草,和“布伦丹号”一样无法逆风出海,只能无望地撞向岸边。这座海岸至少摧毁了二十艘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大帆船,而和西班牙舰队的巨大帆船相比,小而单薄的“布伦丹号”简直是所有水手的梦魇。我们毫无可能逆风而行,而且如果强风往西扫掠,我们将会像树叶般航向坚硬如铁的断崖和半隐没的礁岩,而那些一路漫天盖地扫过大西洋的巨浪,狂肆袭掠过我们之后正碎毁在这礁岩上。即使是现代化的船只,也不敢在如此强烈的风力和航道上挺身对抗气候。对于我们这些在中世纪皮革船上的人,除了在大风扫噬前仓皇转向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像平底雪橇般在波浪上滑行的“布伦丹号”,惟一能做的也仅是将四角形单帆降到最低,减缓冲向海岸的速度。
我看着我的伙伴,心里想着不知道他们对现况有何感想。我知道乔治很清楚目前的险境。他是我认识的水手中最好的一个,我们过去曾乘坐小船航行到过不少地方。就因为这样,我请他担任“布伦丹号”的大副,负责在航行时将船保持在最佳状态。我想洛夫也知道我们面临的险境。他是挪威人,在夏季时常沿着他的家乡海岸驾驶一艘造于19世纪末的巨大帆船。但是随船的摄影师彼得可就令我担心了。不久之前,他曾单独驾自己的帆船由英国前往希腊,对于海洋当然不陌生。但他现在看来却一脸忧郁。我猜想一部分是因为他担心眼前的状况,但更有可能是两天前划“布伦丹号”时的肌肉损伤再度复发。他的脸色阴沉沉的,看得出来他在被巨浪不断上下抛掷的船上感到极端不适。
亚瑟是我们这群人里最年轻的一个,现在正因为晕船躺在那儿,对于险境一无所知。我很少见到像他这么痛苦不堪的人。“布伦丹号”的律动极为特殊,她像艘救生艇,而非传统的船只。她上掷、摇晃,然后快速摆动,接着又上掷。亚瑟蜷曲在那儿承受痛苦,他的眼睛紧闭,无力地躺在舷缘,海浪不时冲上船来泼击在他身上,然后顺着他的脸和防水衣流淌。只有轮到他值班时,他才会放眼观望四周的环境。我见到他竭力让自己坐直,抓着安全索,然后拖着沉重的身体到驾驶台。我不禁在心中暗暗为他的意志力喝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强风袭击我们,五人之中仅有三人处于健康状态,可以操作“布伦丹号”。
最痛苦的一件事是无法在轮替值班之间稍事休息。“布伦丹号”是一艘无顶盖的船只,海水和海风不时刮打进来。在短秃的主桅后面有个像帐篷似的小船舱,后面的空间可以同时让三个人头尾反向像沙丁鱼似的躺着。我们没有空间可以置放备用的衣服、照相机、睡袋以及所有的航海设备。而且不论浪头什么时候溅袭船身,总会扫过船舷,将大量的海水倾注到我们的休息区。不远处的较短前桅杆边还有一方不及狗舍大小的小帐舱,是另外两个人睡觉的地方。那里漏水的情形更严重。每次浪头击中“布伦丹号”的船头时,冰冷的海水即涌入帐盖下,使得在里面休息的人全身湿透。
我在值班掌舵结束时,爬入主桅边的船舱,把自己挤入那一小点空间,躺在那儿开始烦恼起来。我们的航行才开始不到一周,却已经开始面临严重的打击,我可不敢确定我们的船能承受得住。我躺在睡袋里,脚和头部顶着船梁下的舱壁,船身随着浪头上下起伏时,我可以感觉到舱壁也跟着松动。最令我担心的是两边舱壁正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那感觉很诡异。“布伦丹号”像一只动物,也许是鲸鱼,而我则像圣经中的约拿(Jonah)一样躺在它的肋骨里,感觉到船只正改变自己的形状以适应巨大的海水压力。我可以听到四周木头和皮革传来的咯吱声和闷吟声。压力和张力一样大,“布伦丹号”的船体有如呼吸一般,随着海浪收缩和鼓胀。我试着理性地思考,想着维京人的船只也是以同样的架构建造出来的说法。据说他们的船只同样在海洋中具有伸缩的特性,因此航速比较快。然而维京人的船是用木头建造的,没有人知道皮革是否能够经得起同样的考验。“布伦丹号”的架构能坚持多久?我一点头绪也没有。但想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驾驶“布伦丹号”出海,希望能以实际的试验发现真相时,心里似乎好过了一点。
我合上眼睛,平衡感即刻告诉我海面的情况更恶劣了。我可以感觉到“布伦丹号”被三道浪头缠上了。第一道浪往上涌涨的时间似乎很长,“布伦丹号”随着被拱上浪峰,并不断升高,像慢动作般,似乎永远无法越过浪头。她在峰缘摇晃,紧接着一阵搐动,然后停止,她仿佛要在那一霎时啪地一声断折。终于,她自浪头上滑下,无助地被翻滚的浪峰控制,舵手用尽办法维持船体平稳,“布伦丹号”开始顺风行驶,测程仪狂乱地指向每小时十二海里{1},那已是船的极速。又似乎过了漫长的时间,主浪往前扫荡而去,“布伦丹号”脱困,并轻缓地掉落到主浪的浪谷里;然后继续面对第二道及第三道浪头,像饱受折磨的玩物般一再被抛掷。
有一回,乔治正在掌驶舵桨,一道浪头打中“布伦丹号”,并在瞬间将她头尾倒转。“老天!快来!我们正倒着往回走!”乔治大吼。彼得和我急忙冲出小船舱。我们穿得很单薄,海水一下子浸透我们全身,但我们必须把艏斜帆保持在适当位置。我们艰难地走到帆边。艏斜帆正被强风刮得顶在桅杆上,并强劲地拍打着桅杆。带着湿透的闷声,船帆突然鼓胀,开始将“布伦丹号”拖出险境。慢慢地,“布伦丹号”以非常慢的速度转向顺风前进,在经过两道惊心动魄的大浪时,我们胆颤地体会到“布伦丹号”的船身是如何暴露在巨浪之中。幸好这两道浪穿越船底而过,没有造成损害,于是我们继续斜着船身摇摇晃晃地前进。
暗夜中的隐形侏儒
夜晚来临!气候恶劣而幽暗的夜晚,在滂沱大雨里我们仅有几码的视野,惟有浪峰上白色的碎波和远处闪烁的灯塔光线为这样的夜晚带来一些光点。我回到休息的地方时,轮到掌舵的彼得说他似乎瞥见船只的光线,应该是离开港口很远的船只发出来的微光。我含糊地回话要他留神,要是那些光点向我们靠近就叫醒我。接着我钻入睡袋中闭起眼睛,只觉得全身软弱无力。
“我的老天!那鬼东西到底打哪儿来的!”彼得喘着气大叫的声音让我立即睡意全消。必然出事了!我仓促地跌跌撞撞出了小船舱,见到彼得正无助地紧抓着舵柄。洛夫目瞪口呆地望着黑夜的海面,雨水在他的眼镜上流淌。就在离我们仅数百码外,一艘渔业公司的大型拖网渔船正闪着所有的灯光笔直地往我们冲来。她的船头在海浪上猛然前进,激起强烈的水花,同时船身诡异地前后颠簸,发出轰然巨响。在黑暗中,她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其后我才明白我们的金属雷达反应器被厚实的海水阻隔,其他船只上的雷达几乎扫描不到“布伦丹号”的皮革船身,“布伦丹号”形同隐形。
“燃放照明弹!”我对彼得大叫,“放照明弹!”
“用手电筒照射船帆行不行?”洛夫问。
“行不通,”我在飒飒作响的风中大叫,“我们的帆太小,不够当光线反射器。而且那是皮革做的,反射不了多少光线。”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迟了。我们之中一人由紧急救生装备中找出一颗照明弹,但是天气太冷,他的手指头僵硬,无法在那艘渔船冲撞向我们之前及时拆开包装点燃。彼得仍努力地想要掌控舵柄,试着转向,但是强风把我们锁在势必要相撞的航线上。拖网渔船流线型的黑色船身急速向我们滑行而来,距离近到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她高耸的钢铁船壳上的焊接线。在能见度仅有数码的黑暗中,她的舷窗照射出来的光线在我们的惊骇注目下快速扫掠而过,“布伦丹号”与拖网渔船的船尾同高,近得仿佛就要被卷入那收放渔网的滑道。在她面前,“布伦丹号”有如侏儒。
“撑住!我们马上要进入她的螺旋桨卷流里了。”我们四周的海面全是渔船螺旋桨搅起的白浪。她在强风中扬长而去,全然不知她几乎撞毁我们。多么讽刺,我暗忖,我们的险境竟然不是来自大自然,而是人为的,这可是从前的圣布伦丹不需要面对的。我怀疑渔船上没有任何人见到我们。他们要是知道的话,瞭望员会对船长怎么说?说他见到了一艘来自另一个世纪的船只,挂着上面有猩红色塞尔特(Celt)十字的方帆,疯狂地顶着强风而行;船上有五个衣服湿透、一脸绝望的男人?任何瞭望员在这样的一个大西洋暗夜,若真的向船长这么报告,要不是以值勤酗酒的罪名解职,就是被送到精神科。
破晓时,强风达到最恶劣的程度,不断地在浪头上扯扬起碎浪,几乎和暴风雨没有太大差别。横向吹袭的雨水和浪花令我们不得不在轮值时不断将打入船上的海水舀到船外。我们舀了五百多次,才免于船底的积水使“布伦丹号”在海面动弹不得。船上的绳索都是仿圣布伦丹时代的亚麻绞成,现在看来已经有些不对劲了。两条绳索相碰时即相互切割,这样磨损几秒钟后,冷不防地就断掉了。一次又一次,通常是洛夫不得不艰难地攀爬到上下晃动的船头,重新替船帆装上新索具,好让船只继续航行。我的海图匣先是被强风撕裂,几秒钟后冲撞而来的碎浪则把海图打成碎片。虽然强风把我们吹离了航海图中的险恶范围,令人稍感安心,但“布伦丹号”却颠晃着往外海急急驶去,那对我们并没有太多帮助。为了减速,我们在船尾挂了一捆厚重的绳索,让它在水中拖行,权充刹车器,并期盼能借此缓和恶浪。我们也在船尾挂了一个金属桶,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我们还用它料理了一顿美味的爱尔兰蟹。现在,海浪正沉重地击涌到它身上,令它发出哀鸣似的声响。亚瑟这个可怜的家伙,现在看来像只死羊包覆在风吹雨淋的衣服里。他的连衣帽已经被狂风吹走,他的头发往下覆盖住头皮。主船舱里散置着相机镜头、航海指南、湿透的衣服和其他泡了水的器材。彼得累得不得不进去休息。他的手臂在避开渔船时再度肌肉扭伤,看来正哆嗦着。乔治和洛夫的情形看来稍好一点。乔治经历过比这还严厉的强风;洛夫则摘下了眼镜,暂时眼不见恶浪心不烦。
然后,就像通常情况下一样,第二天的天气转好了很多。强风开始减弱,我们的精神也跟着稍微好一些。火柴全被海水泡湿了。我们在紧急设备中搜寻了一阵后,找到一盒防水火柴,点燃了普赖默斯牌(Primus)煤油炉子。我们炖煮了蔬菜加意大利面,并享受了热腾腾的咖啡。“布伦丹号”的组员开始对于周遭环境稍稍有了兴致。乔治高兴地发现,如果掌舵的人反向站立,面对船尾并看着海浪,就比较容易操控船只。这是个奇怪的见解,但我们倒是开始欣赏所有“布伦丹号”上的事物,它们不再那么格格不入。海鸟是经过一夜强风恶浪之后最早现身和我们同享劫后余生的家伙。它们大多是普通的海鸥和黑脊鸥,偶尔也见到单飞的海鹦急急掠过,一路努力地上下挥动短而粗壮的翅膀。它那张有着鲜艳嘴喙的小丑脸孔,使它看来有如儿童的发条玩具。黄头塘鹅这种此地最大的海鸟也气气派派地出来巡逻觅食。它们在俯冲向猎物之前,张开宽达六英尺的翼幅平稳地滑翔;或者急速降低,在大风掀起浪头的海洋上方,乘着上升气流自由飞行。海鸥降落在海面上,毫不惊慌地随波沉浮,它们的冷静让激烈的海水看来不再那么具有威胁。
这些感觉让我觉得“布伦丹号”会克服海洋险恶的环境。也许这是圣布伦丹启航前往西方时就已经知道的秘密之一。我们的眼前仍有三千多英里的航程,必须穿过世界上最诡异的水域,但我平心满足于我们通过了第一次的强风考验,并往目的地迈近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