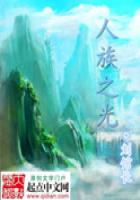吉景贤这几天晚上睡觉老做梦,梦中老是见到自己被一只凶猛的怪兽追逐,追着追着,走投无路之下忽然见到渔船就在眼前,情急之下一个跨步跃过船舷,船只载着自己只管逃命,然而后头的怪物也已应声入水,变成巨无霸,扑将过来,张开血盆大口就要连人带船一齐囫囵吞下。看见深不见底的巨口,锯齿般交错锐利的犬牙,吉景贤周身一个痉挛,顿时惊醒过来,他虽然意识到刚刚是在做梦,但尽管是梦,也被吓得浑身冷汗直流,喉咙发干。
没想到身边的太太徐淑珍醒了,虽然语似啽呓,其实十分关心丈夫有什么不妥,吉景贤抱歉地说道:“你看,又把你吵醒了。我没事,你睡你的吧。”
“老吉,说实话,最近你睡觉老不安稳,叫人觉得不踏实。以前这头一搁枕头,不出五分钟就鼾声大作,现在变了,变得不出声了,搞得我也睡不安宁。”
徐淑珍有着天底下当妻子最难能可贵的优点,睡觉的时候,当身边的丈夫在枕边拉风箱似的一声高一声低地打着呼噜的时候,她早已习惯,更会随着丈夫的节奏,呼吸吐纳,怡然入梦,睡得稳稳当当的。相反,如果这一晚上那熟悉的呼噜声没有了,或者起伏不定,一改常态,徐淑珍反倒不踏实,半夜还会起身点亮床头灯查看一下丈夫的睡觉情形。有朋友戏称,说吉老板的呼噜声对徐淑珍来说那是最好的催眠曲。
“哎,人若改常,不病即亡。”吉景贤在黑暗中叹了口气。
“半夜三更发什么神经,什么死呀活的,也不忌讳。”
“你说我都快退休的人了,却偏偏摊上这么件事儿。豆腐掺沙,吹又吹不掉,打又打不得,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嘛?”
徐淑珍当然清楚“这么件事儿”指的是什么,就在最近短短一段时间里,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断开会,关于秘鲁项目的进展情况也不断汇报,一时间整个公司沸沸扬扬,小道消息满天飞,老头子压力很大。为了应付对各部门的汇报、月报、旬报,把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的人支使得团团转。写完报告,也不是就完事了,上级单位或有指示、建议,又要贯彻执行,又要回馈报告,干好了,倒也罢了;要干不好了,责任是自己的,其余的话你还不能多说。这种情况,作为吉景贤的妻子,她知道得比谁都清楚。然而,她实在不愿意三更半夜与丈夫讨论这么严肃的事情,于是柔声说道:“工作的事留待明天再说吧,你也忒放心不下,车到山前必有路,你不睡觉,明天哪来精力操心?”
“我这也是心里憋得慌,总感到自己吊在半空中,迟早要出事呢。把耳机给我,想不到睡觉也这样成问题,真是岂有此理。”吉景贤最近找到了对付失眠的办法,就是听音乐。只要旋律舒缓,听着听着,就能平抑自己激烈的心绪,使心情逐渐平和以至入睡。为了不影响身边的老伴,他只能用耳机听,这一招果然奏效。
第二天,吉景贤刚在自己办公室的大班椅上坐下,秘书小王即呈上刘进益的传真。吉景贤顾不上往自己的茶杯里加茶倒水,扶了扶眼镜就认真地读了起来。
呈吉景贤董事长:
违教许久了。由于过去都是向金富总部康于两位总裁汇报情况,直接得到您的指示的机会反而少了。今天我想破个例,将近来困扰我的一些问题向您汇报,也盼能得到您的指示。
康总裁这次到利马来,有一天找了我们几个人到他住的希尔顿酒店开会,宣布了几项决定,一是将八条渔船抵押银行,套出资金,说是用于渔船的维修;二是金富秘鲁公司成立由刘进益、周启荣、归泓业三人组成的执行小组,对公司重大决策和日常业务进行集体领导。
这样事关全局的重大决定,应该有董事会决议作为依据。如果这就是董事会的决定,您作为董事长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说成立三人小组你们领导觉得没有必要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且不待言;但将船只抵押这样重大的经营决策,你们事先也应该听听我们这些处在一线工作的同志的意见吧?这种做法似乎有悖于我们过去一贯的行事作风。
现在三人执行小组已经成立,为了顾全大局,不使工作停顿,我仍然合作,但由此而引起的可能混乱或失误,我不负这个责任,也请你们领导能够以董事会文件的形式,就此做出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本人将无条件执行。
敬礼!
刘进益
吉景贤看完这份传真,对文中所述之事,实在摸不着头脑,心里直怨刘进益,姜桂之性,老而弥坚,你要这时候撒手不干,叫我靠谁?又想于成龙再糊涂,这种事情也不会瞒着自己呀。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关头可不是犯糊涂的时候。
吉景贤脑子里一急,右手随即伸向电话,用对讲机通知房间外的秘书,立即请于成龙到自己的办公室,他要马上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金富公司香港总部设在湾仔会展中心。于成龙正在银行办事,接到通知,一时抽不开身,等办完事搭上的士,气喘吁吁地赶到吉景贤办公室的时候,吉景贤面露不悦,点点头算是招呼,随即递过刘进益写来的传真件,说:“坐下看,然后告诉我怎么回事?”
于成龙神色凝重地接过传真,站在那儿一目十行地飞速看完,然后认真地对吉景贤道:“董事长,这事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停了一会儿,吉景贤才问:“那你怎么看这事?”
“董事长,”于成龙慢慢地在大班桌前的靠背椅上坐了下来,“有件事一直埋在我心里不少时间了,但由于顾虑我都未说,我觉得现在很有必要跟您说。”
吉景贤静静地注视着于成龙一会儿,张口说道:“什么事,说出来听听。”
“以前常听说康文彬与我们上头关系不凡,不论是真是假,对我们这些公派人员心里都有影响。”
“是这样,说下去。”上回程铭森到香港访问时,康文彬可以同程副省长关在房间里两个小时,其他已获安排见面的客人都要往后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可有一次我发现这上头不只是省里,而是更高一级的。那回康文彬要到省里,叫我到他办公室里交办一些工作,我站在办公桌前,听他一件件地吩咐,可眼睛却不由自主地被一件东西吸引着,您猜是什么?一封已经封好的信,那封信就这么孤零零地摆在写字台中间,信封是用毛笔写的,您知道,康文彬在办公室里摆有文房四宝,闲时用毛笔写写字是他的嗜好。信的落款人居然是我们的一位高层领导。康文彬见我注意到这封信,就很随意地对我说,他第二天到省里,要托人带到北京去,还说他和这位领导是世交,老朋友了。我当时并没有特别说些什么。”
“可是前两天,又发生了一件事。他不是刚从秘鲁回来吗?上班的时候,我正在公司的小会议室里和国内一家公司商讨如何合作进口秘鲁鱼粉事宜。这小会议室就在他办公室边上,除了有正门通向过道外,还开有一扇小门与总裁办公室相通,是专供他使用的。也不知什么原因,那天那门是打开的,康文彬正在讲电话,开始时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后来听到他在电话里先是称对方的官衔,后来就一口一个‘哥’地叫起来,末了又说这两天可能上趟北京,想顺道登门拜访。这简直就是扯淡,这位领导人前几天还在深圳,这两天又转到上海,这中央电视台都播着呢,啥时候回的北京啦?”
“你不会记错吧?”
“电话不会听错,电视没有看错,明天星期六下午,内派人员还要集中学习这位领导在深圳的讲话精神,这更不会错吧?”
“或许他的电话是打往深圳也不定啊。”
“这不可能。我也是太好奇的缘故,不怕你骂,当天我就亲自查询了电话公司,不说深圳,就连打到北京的电话都没有一个。”
“难道这是在做戏给我们看?这也太掉价了。堂堂一个总裁,干这种下三流的勾当,你信吗?我实在难以置信。哎,以前反映他的诚信问题,看来草灰蛇线,不为无因啊。”
“我对他的看法一直是很好的,就是省里发生‘评估’事件,我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变,毕竟在这项目上人家是花了心血的。不说远的,就上回跟英国人打官司的事,也就是他啦,照样三下五除二地把问题圆满解决了,省去我们多少麻烦。那可是在反映他诚信问题发生之后,他可是大将风度啊,就没受到一点儿影响。”
“你不知道,他后来又给省里领导写了封信,洋洋洒洒,妙笔生花,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了秘鲁国丰富的渔业资源,引用秘鲁人戏称,他们国家海里的鱼是老死而不是被捕致死的;随之而来的是渔船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鱼粉贸易大有可为。金富公司毫无疑问可以在渔船出口和鱼粉贸易中,获取丰厚的回报。总之前景十分诱人。毫无疑问,这样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当然获得上面的欢心,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变人们对他的看法。尤其是当他不失时机地指出,捕鱼项目的投资,有别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出了问题撤不走,搬不回,必要时船可以开回来,因此风险极小;鱼粉等于世界通货,金富公司投资得到的渔获或加工成的鱼粉,均享有国家进口免税待遇,得益将是以人民币千万元计。省里领导阅后是怎样一种心情我们可想而知,至少让读它的人感到一种憧憬、一种信心、一种希望,加上官司胜了,不能不觉得他就是一位能人。”
“那中行总行的通报就一点儿也不管用了?”
“也不尽然,但那种官样文章,说服力岂能与康文彬这种情文并茂的文章相比?再说了,他现在不也在拼命工作吗?何况这里还有与上头私交等因素,这些都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不管怎样,评估的风波算是过去了。”
“这样一来,我真的没主意啦!你说刘进益这份传真所提到的问题,是深究还是睁只眼闭只眼算啦?我真的不懂。我就算有意见,最多也就是到您这儿诉诉苦发发牢骚。人家的能耐大得很,那可是通天的。”
“那也不能发现问题装聋作哑吧。现在看起来,那个‘评估风波’确实不是空穴来风。此人这样装神弄鬼,行事诡异,居心叵测,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传真里说的这两项决定,你我都蒙在鼓里,这后边还有什么名堂没有?”
“我最恶心那种搞阴谋诡计的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些事不由得我不改变对他的看法。”
“改变是对的。”吉景贤摇摇头,不无忧虑地说道,“不叫的狗,咬人最狠。我们不得不有所提防。我在想抵押的事,那是在拼死吃河豚。三人小组的事,权力也不在他总裁一人身上,公司早有规定,对下属公司总经理一级的任命,职权在董事会,由董事长签发,总裁任命。他这样做,叫扫帚颠倒竖——乱了规矩!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董事长?”
吉景贤越说越气,拿起杯子想喝口水,却发现里边是空的,一怒之下,重重地将杯子往桌上一掼,大声道:“立即通知有关人员召开董事会,这些事不搞清楚,出了事谁负责?”
平静下来以后,吉景贤又对于成龙道:“对康文彬的行为,我们要提防,该抵制时要抵制。但沉疴不用急药,要防止将矛盾激化。既然项目已经上马了,全力以赴抓捕鱼,抓回收,这才是根本。我想省里也是这么个意见,否则你说怎么办?撤又撤不走,硬撤,人家就眼睁睁地看你把船开回来?开玩笑!再说啦,船工都是当地人。说到这点,当时康文彬跟省里报告,每条渔船要全部使用中国的船工,说是劳务输出的一大突破,可后来又说,为了避免与当地渔民的矛盾激化,谈判时又将此提议全部撤了回来。你想就算那些船工听我们的,这中间还隔着个太平洋,能开得回来吗?不现实啊!所以还是要客观一点地面对这个问题啊!”
吉景贤拍了拍自己的额头,又随手看了看表,这才说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不合适,反正也不急在这一刻。这样吧,你回去后给刘进益打个电话,让他继续安心工作,继续抓总。再告诉他,我很重视他的这份传真,叫他把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写个报告给我。”
“可是,董事会无法马上召开。”于成龙皱着眉头说道。
“为什么?”
“因为,康文彬到省里去了,就今天走,何时回来我也不清楚。”
吉景贤又是一愣,他在心里问道:康文彬到省里干什么去了呢?
康文彬从利马回来,稍事休息,旋即又风尘仆仆地飞往省里。这次他带着他的助理菲力,行前人们都以为他们是到省里出差,其实,他们奔的是离省城仅三十公里远的松江造船厂,他们是为签约之事而来的。
菲力是康文彬的心腹,高高个儿,戴一宽边近视镜,个性好静,说话慢条斯理,对康文彬忠心耿耿,深受康的信赖。康文彬将自己在金富公司30%的股份中让出3%,转由菲力持有,这当然也有进一步借重的意思。
菲力对此行并不像康文彬那样乐观,虽然是去下订单,自然颇受欢迎,但想以不到5%的定金,让厂里投产生产几百万美元的渔船,工厂方面会答应吗?
看到康文彬竟似一点担心也没有,菲力倒向他请教。康文彬笑着说:“我这个人向来是不怕内地当官的,大官小官都好,我都不怕,我怕的是他们没有嗜好,但没有嗜好的官我好像还未见过,总之我可以搞掂,你不必担心。”
当晚七点,松江造船厂的谭捷时厂长,率副厂长、技术科长等在省城龙宫大酒店设宴欢迎康文彬两人。
当他们二人来到包厢的时候,谭捷时跨上一步,紧紧地握住康文彬的手,热情地说道:“欢迎欢迎,康先生,感谢你们对我们松江厂的大力支持,我们是第二次握手、第二次合作。”
康文彬接过话道:“希望很快会有第三次、第四次,就这么一直合作下去,哈哈哈。”
满屋的人神情笑嘻嘻,喜滋滋,乐个不停。这样乱过一阵,望着陆续端上来的水陆丰馔,康文彬道:“我说谭厂长,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众口品美食,这也太多了,你们也太客气了。”
谭捷时道:“哪的话哪的话,你们给我们厂带来这么大的订单,这点子东西算得上什么?”
“可不是这话,我们厂长说了,这次你们的订单,与上回的要求基本一致,一切都是现成的,这事就更好办了。只要资金能够按时到位,我保证生产一定按质按量,多快好省。”
副厂长的话音刚落,谭捷时说道:“康老板,我们是搞造船的,没那么多花花肠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您别见怪。他说的是大实话,造船这行业一家伙下去就是成百上千万的,资金确实非常重要。不过,我们有上回的合作基础,康老板财大气粗,我们用不着担心太多,对不对,康老板?”
康文彬不曾想对方见面不到五分钟即开门见山地与自己谈起钱这个问题,心说如果不明确表态一下,今晚这顿饭怕是别想吃好,以后的事也甭想做得顺畅。于是故作轻松地说:“我这人最爱同直脾气的人打交道,因为胜在够爽。至于资金问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跟各位说一句,放心,一定步步按时到位。说实在话,这兜兜里要没装上几个子儿,就敢上豪华馆子吃饭?你们别笑,真的,我今儿敢在各位面前说这种话,就不怕你们笑话我蛤蟆打呵欠——口气不小。这事要不是落实得七七八八,我敢上这儿签约?”
“有您这句话,就什么都有啦!”谭捷时酒还未喝,脸色早已兴奋得光彩照人,“谁敢笑话您?您是财神爷,何况咱们又不是初次合作,是梅开二度,然后逢二进三,无三不成礼,以后的合作路子还长着呢。来来来,大家一起把这杯酒干了。”
“对对,干!天大的公事,地大的银子,有钱好办事。来来来,干干干!”副厂长也大声说道。
康文彬矫情镇物的功夫实在了得,三言两语说得大家开开心心,一时房间里佳肴醇醪,糟香四溢,杯觥交错,逸兴遄飞。双方的目的既已达到,心无挂碍,这顿酒自然喝得轰轰烈烈,不醉无归。
翌日,在松江厂厂部小会议室里,双方正式签约。
坐在沙发上的康文彬对身旁的谭捷时说道:“谭厂长,合同我都看过了,没有问题。但有一个小小的修改,即买方名称,不用金富公司,用的是旺顺投资有限公司,就是这个。”康文彬递过一张纸,上头用中英文写着这家公司的资料,接着道:“公司老板是我。不过生意与金富全没关系。我这人公私分明,不沾金富公司这块金字招牌,事情呢,放心,照样同上次一样干得漂亮。没问题吧?”
谭捷时听了,对这突然的变故表现冷静。实际上,他从归泓业处得到的报告,对这单生意的来龙去脉已经有所了解,因此笑着说:“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打开大门做生意,谁来都一样,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理由有生意不做,对吧?”说完,转过身去,将手里的纸张交给一名下属,吩咐道:“叫他们改一下,重新打印。”
双方在改过的合同上签字以后,谭捷时说:“康老板,这就算定了。有事多通气,找不着我,找副厂长也行。”
“谭厂长办事果然干脆。回去后,第一笔钱说话就到。做买卖讲究一个信字,当然,买卖有买卖的规矩,咱们之间的事,咱们热线联系。我是满世界跑的,找不着我,可以找我的助理菲力,您看行吧?”
谭捷时一点即明:“行,我心中有数,到底还有商业机密这一说吧!”
康文彬办完与松江厂的事后,原想搭晚班机连夜返港,因为他实在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碰到水产厅的人。不想一回到酒店,柜台小姐随即递上一份留言,说是让康先生回来后,立即给香港公司打一电话,署名是于成龙。
康文彬接过留言,怔了好一会儿,然后对菲力说:“于成龙追到这里来了,你打个电话回去,问问他究竟什么事?”
菲力打完电话后,告诉康文彬,吉景贤、于成龙搭明日早班机回省城,明日下午三点半在向裕集团驻省城办事处的会议室召开金富公司股东碰头会,还说已经通知省水产厅的万世铨厅长,让康文彬届时出席。
“老板,什么叫股东碰头会?”菲力问道。
望着菲力一脸茫然的样子,康文彬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大陆开会的名堂特别多,反正就是让你开会,你管它是什么碰头会、碰尾会,去了就知道了。”
“‘察一叶之落而知秋之将至’,来得好快啊!”一贯以儒商自诩的康文彬在心里念了句文言,“我看他们这样急匆匆地忙着开会,无非是冲我而来,不是刘进益又汇报了什么,就是刚签下来的合同的缘故。否则吉老头子还能这么心急火燎地赶到这儿,在香港开个会岂不省事?”
“也许,这样也可以迁就一下水产厅的人?”菲力问。
“不管怎样,来者不善。”
窗外早已是万家灯火,几家欢乐几家愁。原本开开心心的康文彬被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影响了情绪,一直到街深巷暗,云遮月隐,已是钟漏将歇的子夜时分,他还在那儿苦苦地思索着如何面对明天的会议。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