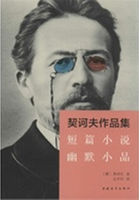“昀姐姐,梁国公的小儿子我见过几次,心地倒是不错的呢。”
“你认得萧钊?”我问。
“嗯,他这回也去江都。”
“好啊,连他都能去江都!”我鼻子又酸起来。
“姐姐待嫁自然是不能离开大兴宫的,”季子说,“可不要紧,要是一路上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我都命人给姐姐送来,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我也写信来给姐姐说,可好?”
我哼了一声:“你说的啊,灯笼纸鸢可别忘了我的份,还有琼花和干丝,我都爱的。”
他笑着应道:“我自然记得,季子还会给姐姐准备大婚贺礼呢。”
我脸上“腾”地一热,害起臊来。
春天的大兴城向来少雨。去江都前,父皇率宗亲大臣去太庙求雨。有传言说,关中平原内大旱,闹得人心惶惶、民心凋敝。
我和季子躺在草地上看着宫人们晒花,天上的云朵一会儿一个花样,日头晒得大兴宫暖洋洋的。
我随手捡起一朵蔷薇,放在鼻前嗅了嗅。
季子悄声说:“我听人说,现在很多地方都乱了。”
“因为大旱?”
“不知道。”季子摇头,“父皇挺愁的,但我母亲不许我问,说父皇自有主张。”
我点头:“是哪,父皇在,没什么事儿的。赶明儿下场大雨把关中都浇得透透的就没事儿了。”
他不吭声,我扭头看他面上忧色浓重,推他一把:“傻子,担心什么哪!要是天下真不安,父皇还会去江都吗?”
我将手边的花瓣都聚在一块儿,装在锦帕里,兜头将它们一齐洒在脸上。
季子瞅着我的怪样,笑道:“你又做什么怪呀?”
我闭着眼躺在花瓣下,答:“要是哪年我死了,你就这样埋我,春天用蔷薇,夏天用荷花,秋天用桂子,冬天用水仙。将我埋在花里,不用封土和陪葬,就让我随它们一起化了。”
季子咯咯笑:“果然姑娘越大越古怪,还没出阁呢就想着死了。”
我睁眼看着他:“你别笑,你看太子哥哥不也好好的就突然没了吗?”
他戛然沉默下来。
我用手指戳戳他:“哎,你想过没?你若死了,想怎么样?”
他漆黑的眼珠定在一处一动也不动,过了一会儿说:“我想留在大兴宫里,陪着你们,陪着这春花秋月、玉树琼枝。”
我们这回谁都不说话了,躺下来看云朵和东风捉迷藏。远处有燕雀婉转,和宫人们的低声笑语绕在一起,在大兴宫里飘飘扬扬。
父皇在求雨时遇刺的消息顷刻间传遍内宫。
我和季子在王氏那儿玩耍时,恰巧听到她和宫女们窃窃私语。我们傻了,连忙扔下手里的花草,奔回母亲的寝殿,抓着母亲问:“父皇受伤了吗?贼人抓住了没有?”
母亲正在和萧嫔说话,听见这话忙掩住我们的嘴巴,轻声道:“别说了!”
季子问萧嫔:“母亲,到底怎么回事?”
萧嫔为难地看母亲一眼,叹口气:“你们父皇没事儿,贼人也抓住了。这话你们别再提了,免得皇上不高兴。”
母亲点头:“你们记清楚了,见到父皇照旧问安。谁都不准再提一个字儿,知道吗?”
“为什么?”我问道。
母亲瞪我一眼:“听着吩咐就好了,别打破沙锅问到底。这可不是玩儿的事儿。”
我闭上嘴将一肚子疑问勉强吞了下去。
季子的脸色变得难看极了,半晌后他问萧嫔:“那,江都还去吗?”
母亲和萧嫔面面相觑,竟一时间没人开口,只听见炉鼎内的香一寸一寸烧成灰。
当夜母亲和萧嫔被皇后召去商量事情,三更过了才回来。我和衣盘腿坐在榻上,胡乱翻着母亲的经书,强撑着不肯睡。好不容易等到母亲回来,却见她进屋时满面愁容。
我忙问道:“母亲,怎么了?不去江都了吗?”
母亲摇头,将金钗卸下,坐在镜前,神色凄然。
我心里七上八下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到母亲身后,用热乎乎的脸依偎上她冰凉的颈项,喃喃撒娇道:“母亲。”
她伸手拍拍我的面颊,说:“你父皇决定江都之行照旧,不仅如此,后天宫内还要举行宴会。”
“为什么?”我愕然,“又有谁生日了吗?”
“为了颂扬我大隋国威,祝祷国运昌隆。”母亲的笑看上去像是哀伤,浅浅地挂在唇边刻在眼角。
父皇平日里最喜欢大摆筵席,碰上萧皇后或者后宫哪位的生日,又或者像上回父皇三征高句丽凯旋,那就分外热闹了。当时父皇为了颂扬国威还特命高句丽的歌姬们奏异族乐曲,舞姬们也跳起异邦舞蹈,比平日里听惯的九部乐还要旖旎新鲜,那一晚乐声通宵达旦,声动九霄。
这天一大早宫人们就扛着大卷大卷的绸缎将大兴殿乌油油的大梁用明黄和大红的绸缎裹住,窗棂和高台上挂满了银质的烛台灯盏,连御花园里都被成串的红灯笼点缀成红海。大殿正中的铜鼎被烧得红彤彤的,百合香气一直飘到内宫里来。
我一整天都在和鸿雁闹脾气,她怎么都找不到我最喜欢的那件绣着仙鹤的襦裙,直到母亲派人送来一条大红绣着金线的石榴裙,看上去倒比我那件更加明艳,配上明月珰,竟将我面上的一团孩子气减去好几分,我这才破涕为笑,欢欢喜喜地盘髻梳妆。
天刚晚,宾客齐聚,身着绣着霓彩华云的华丽裙裳的宫人们忙着将腌制过的玫瑰花瓣盛在水晶盘里,和羊羔肉、红鲤、数百道河鲜蔬果一起分到每个人面前的小桌上。我和季子挨着母亲坐,南阳姐姐带着小禅师坐在我们对面,萧后伴着父皇坐在高高的御榻上。除了皇室宗亲外,三品以上官员皆携眷出席,殿内百人之众,顿时热闹喧哗鼎沸一时。
开宴的舞曲奏毕,所有人举杯共祝父皇万岁千秋。我端起盛满西域进贡的葡萄汁的琉璃杯,随众人一起下拜。
父皇身着衮冕,从御座上缓缓起身。他面色郑重地左右四顾一番,说:“我大隋如今四海一统,国祚稳固,正是千秋盛世之兆。朕半月后将由东都巡幸江都,到时江南河通,又一千古幸事,必将有助于大隋国运!近日来,朕听闻京城内一些妄言社稷的流言甚嚣尘上,更有奸佞小人意图以此愚弄百姓,以天灾为由攻击朝廷,实乃大逆不道!朕素来最恶以攻击君上而博个人雅名之所谓谏言,如有查实,朕必当杀一儆百!今日朕与诸卿同乐,须得开怀,来,满饮此杯,祝我大隋国运昌隆!”
殿下百余人一齐山呼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大隋万岁万岁万万岁!”
父皇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愈发显得俊朗神秀。
父皇命人取来闻名遐迩的“焦尾”,放在膝上开始弹奏,一曲《阳春白雪》清新明快,和着殿内熏笼里正燃着的清甜甘爽的百合香,直教人意兴勃发。
一曲未终,我高兴地拍起手来,母亲嗔怪地看我一眼。父皇循声望来,笑眯眯地对我招手:“兰因,到父皇这儿来。”
我起身走上御座,父皇揽着我的肩,和蔼地问:“兰因最近和师傅们学了什么曲子?”
“近来师傅正在教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兰因刚刚练熟。”
“来试练一番怎样?”父皇问。
我面上发热,有点胆怯,可又心想着前日都当着母亲面练过了,算是拿得出手吧,于是壮着胆子问道:“兰因若是弹得好,父皇可有赏赐?”
父皇和萧后闻言大笑,父皇说:“兰因若是弹得好,这把‘焦尾’就送给你了!”
我趁势说道:“父皇金口玉言不可反悔!”
“绝不反悔!”
宫人们安置好琴榻,我在玉盆里洗净手,整理罢衣冠,端然在琴边坐下。殿下此刻阒寂无声,大家都等着我一展身手。
我缓缓将手指搭在弦上,一边右手挑托抹钩、左手吟揉,一边凝神运气,将那洋洋水声、巍巍山色都纳在十指间。
此曲开篇庄严处似群山巍峨、高耸入云,清脆处如水滴石穿般柔和流畅。逗人趣致的三两声后曲调转入酣处,时而水波细密流淌,时而群峦隽永瑰丽,时而流水撞击孤山,时而山河共鸣跌宕激越、扬扬悠悠绕梁而行。末了,又似高山之巅、汪洋之上、松根之下、鱼跃之间有万云赴壑、轻舟渡海。
我沉一口气在丹田处,闭上眼不管今夕何夕此刻何地,只管将十指当作开山之斧、拨水之桨,心弦一同随之震荡飘游。曲子既终,我犹未回过神来,只听得父皇在耳畔鼓起掌来。
“好兰因,不愧是朕的公主!”父皇红光满面、喜上眉梢,“这‘焦尾’配你,才是宝剑赠英雄,红粉送佳人!”他转头对宫人道,“再去预备打赏教公主琴艺的师傅,教出如此得意之徒,更该重赏才是!”
殿下诸人也纷纷凑趣附和父皇,满耳的颂扬之声让我顿时觉得面上生光,飘飘然起来。
我得意扬扬地抱着“焦尾”端坐在父皇身边,只见季子露出又赞又羡的神色,唯有母亲神情似高兴又似嗔怪地瞅着我。我明白她是在嘲笑我爱出风头,可今夜这样高兴,谁顾得上这许多?赶明儿再装什么喜怒不行于色的淑女好了。
萧皇后笑吟吟地对父皇说:“今夜这般热闹,臣妾也斗胆献丑。”说罢取来笙,命乐师用箫合奏。笙箫两调一问一答,在殿内追逐缠绕。不一会儿,母亲也到殿前跳舞,她的细腰像被风吹拂的柳条,石榴裙随着她的旋转忽开忽闭,她惯用的玉兰熏香慢慢地像潮水般蔓延到每个人的鼻下。
我盯着合目安详调笙的萧后看,满心艳羡她的端庄高雅。她穿着月白的长裙配石榴红的短襦,长发高盘,凤钗耀目。那是和母亲曼舞窈窕全然不同的魅力。平日里的那些飞短流长丝毫不能折损她的高贵气质,我趴在父皇耳边对他悄悄耳语:“母后真美。”
父皇笑着转头对萧后说:“兰因羡慕你的美貌呢。”
萧皇后明媚一笑,白皙的手指抚过我的脸颊:“兰因长大了也是个美人。瞧这双眼睛,和陈贵人一个模子。”
可父皇的后宫中哪一个不是美人呢?萧皇后、我母亲、萧嫔,还有传说中的宣华夫人,就连颇受冷落的王氏,都颇有样貌。
这座宫殿的欢乐瞬间冲到了波峰,我依偎在父皇身旁,傻呵呵地在乐声中飘着,盼着这夜永不结束。
几日后,父皇和母亲就出发去了东都,再从东都经通济渠去江都。
前一夜我跟着母亲睡。我和季子斗草回来,母亲正倚着美人靠出神。
“母亲。”我喊她。
她闻声抬眼一看:“兰因,你去哪儿了?”
我说:“去找了季子弟弟,他明天就要起身了,我想着得去送个行。”
母亲点头:“这才像个姐姐。都快出阁的人了,以后可别那么任性了。在这宫里,人家当你是公主宠着,在外面你可得替你父皇长点脸,拿出公主的样子来,像你南阳姐姐似的,明白吗?”
“明白了。”我挨着母亲坐下,她轻轻抚着我散了的发髻,叹口气:“母亲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归为臣虏了,婚嫁琐事统统由不得自己,不比你现在父皇疼你,诸事随心,可将来,好景未必常在,你不得不仔细啊。”
“母亲,”我想起那个故事,问道,“是父皇灭了你的故国,杀了你的母亲吗?”
母亲顿住,摇摇头:“兰因,以后这话不可再提。”
“为什么?”
“因为……”母亲欲语又迟,“因为你是你父皇的女儿,大隋的公主。你只需记得你姓杨。”
我默然。
母亲语重心长地说:“兰因,即便是公主,也不是谁都能平顺安乐的,你要惜福。”
我颔首,又问:“母亲,那你当年嫁给父皇,心里是什么滋味儿啊?”
她笑了:“亡国恨、新婚喜,千般滋味。欲哭无泪,欲笑还颦,怎么一言说得尽?”
第二天清晨我在城楼上送走父皇、母亲和季子,转身孤零零地走回冷冷清清的宫苑。
园子里的鸟雀还在争食鸣唱,嗡嗡哼着小曲儿的蜜蜂正围着桃树、梨树们忙个不停,可在我眼里,这个春天已经到头了,四周的景致就像是未着色的山水画,褪去生机,显得冷漠遥远。
3
偌大的宫城,现在空了一大半。我数着日子,从春末熬到秋天,再等到第一场瑞雪,过了新年父皇就该御驾回宫了吧?
季子和母亲常有信来,母亲总是不忘嘱咐我好好练习女红和乐理,不许胡闹。季子告诉我看了些什么戏听了些什么曲又吃了些什么新鲜东西。可怜我整日除了看书写字,就是埋首调琴,自打记事起,就从未如此寂寞过。
说起寂寞,我陡然想起一个人来,这宫中哪有人比她更寂寞呢?
每次我打王氏的门前过,她的小院子都阒寂无声,从来不见谁去找她聊天或是从园子里摘一朵花去看看她,就连婢女宫人们对她都是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
我和季子因好奇去找她玩耍时,她皆是一副惊慌失措的模样。
萧嫔说这是因为她不受宠的缘故。
我纳闷,这王氏也是好端端的样貌,装扮起来不比其他美人差啊,只是那怯生生的样子,看上去太可怜。
萧嫔叹气:“可惜一个美人,偏偏生在那样的家庭。她的舅舅是唐国公李渊,素为陛下所忌惮。有一次她难得奉见陛下,陛下竟然开口便问她,你舅舅怎么还没死呢?”
我们悚然一惊。
父皇不喜欢她,难道宫人都要疏远她?这便是宫墙内世态炎凉的永恒定律。
我和季子觉得她可怜,于是有时候捉到叫声响亮的蟋蟀就装在小陶罐里放在她窗下,园子里若是花开了,像牡丹、芍药、海棠,我们也摘一些,盛在水晶盆里给她送去。虽然知道父皇不喜欢我们亲近她,但想到她畏惧瑟缩的可怜样子,我们又心生不忍,常偷偷去看她。
一日在屋里实在憋坏了,我索性扔下琴谱,吩咐鸿雁带上父皇去年赐的西域葡萄美酒,跟我去王氏僻静的小院子。
父皇出巡,她素来都是没有资格伴驾的。年前我来过几次,可都不巧,不是她身上不畅快就是正赶上她念佛。
王氏住的小院子,在宫城的西边,小小的几间房,平时看不到什么人出入,所以更显得冷清。
雪洋洋洒洒像棉絮似的扯了几天,这才刚刚停下歇口气,路上的积雪已经被宫人们扫得干干净净,我特意从园子里绕过去,只见几棵红梅已经绽出花苞,甚至还有些零星花朵正吐露艳红,我高兴地叫正在给花枝打雪的宫人们剪下两枝,一枝送回房插在青釉瓷瓶里供在案上,一枝送给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