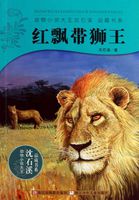“好极了。如果现在我站起身走三步,走进丛林,那么就没有人能找到我,包括先生您,除非我自己想出来。就像我不愿意这么做,同样我也不愿意现在告诉你。耐心点,先生,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一切,因为,如果你愿意,总有一天我们会一起赶大羚羊的。不管怎样,并不关魔鬼什么事。只是……我了解丛林就像一个人了解自家的厨房一样。”
毛格利说着,就像在对一个不耐烦的孩子解释。吉斯伯恩一头雾水,又非常生气,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盯着地上若有所思。当他抬起头时,森林之子已经走了。
“这样不好,”灌木丛里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 “朋友之间吵架不好。天黑之后再见,先生,等凉快一些再见。”
“他是伊甸园里的亚当,现在就缺一个夏娃了!”
吉斯伯恩被独自丢在丛林中央,他咒骂着,接着又大笑起来,重新上马前行。他拜访了一个护林员的家,查看了两处新的种植园,下命令烧掉了一块干草地,然后出发到他自己挑选的露营地,那是在离坎叶河岸不远处的一个碎石堆,上面随意地覆盖着一些树枝和树叶。
小山上闪烁着篝火,风中弥漫着一股晚餐的香味。
“唔,”吉斯伯恩说, “这总比冷肉来得好,这个时候在这里的只可能是穆勒,他正视察切格曼加丛林,于是就跑到我的地方来了。”
穆勒是个高大的德国人,是全印度的林木部长,也是从缅甸到孟买的森林最高长官,他习惯像蝙蝠一样在各个丛林飞来飞去而不事先通知当地长官,还常常出现在那些人烟罕至的地方。他的理论是:突然访问、发现问题,口头批评下级,比起慢吞吞的信笺往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后者往往以一份官方的书面批评告终——可能过了好几年,这份东西还记录在某个森林官员的档案里。他解释道:“如果我像荷兰叔叔一样和下属们交谈,他们会说:‘那只不过是该死的老穆勒。’下次他们就会做得好些。但是如果我的笨办事员写些什么穆勒对此很不理解,非常生气的话,首先因为我不在场,所以一点用处也没有,其次,接替我的傻瓜会对我最棒的小伙子们说:‘看看,你们这群被前任长官臭骂过的家伙。’我告诉你,光戴顶官帽是不能让树木茁壮成长的。”
从火光背后的黑暗中传来了穆勒低沉的嗓音,他正弯腰站在他心爱的厨子身后。 “少加点沙司,你这个小妖怪!伍斯特沙司是调料,不是汤。啊,吉斯伯恩,你来得真不巧,今晚的饭菜很糟糕。你的帐篷在哪里?”他走上前,和吉斯伯恩握了握手。
“我就是帐篷,先生。”吉斯伯恩说,“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穆勒看了看年轻人整洁的外表。 “很好!非常好!一匹马加上一些干粮,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野营。现在和我一起吃饭吧。上个月我去了总部,拼凑了一份报告。我只写了一半——嘿嘿——余下的交给了办事员,然后自己跑出来了。政府搞这种报告真是有病——我在西姆拉就是这么跟总督说的。”
吉斯伯恩暗自笑了,想起了很多有关穆勒冲撞最高政府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甚广。穆勒是所有部门特许的自由思想者,因为作为森林官员,没有人能比他干得更出色。
“吉斯伯恩,如果我看到你坐在长廊里吭哧吭哧地埋头写林木报告,而不是在森林里巡游,我就调你到比卡内尔沙漠中部去植树造林。我厌恶报告,厌恶死板的文件,它们只会占用我们干正事的时间。”
“别为我担心,我不会浪费时间在年度报告上的。我和你一样讨厌它们,先生。”
接着,他们谈论起业务。穆勒提了些问题,并给吉斯伯恩下达了一些命令,作了一些指示。然后他们一起吃晚饭。这是几个月来吉斯伯恩吃的最文明的一餐。虽然远离生活用品供应点,虽然餐桌铺在荒野上,但丝毫不影响穆勒的厨子发挥厨艺,这顿晚餐以撒了芥末的河鱼为头道菜,最末则是咖啡和白兰地酒。
“啊!”饱餐一顿之后,穆勒满意地叹了一声,点上一根雪茄,躺在他那破旧的折叠椅上, “当我在写报告时,我是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但是在这儿,在丛林里,我既是忠实的基督徒,又是异教徒。”他舒服地在舌头下卷动着雪茄,双手搭在膝盖上,凝视着前方,那里,晦暗不明、变换多端的丛林深处充满了神秘的声响。小树枝断落的咔嚓声仿若他身后火堆的毕噗声;白天被太阳烤得弯了腰的树干,在凉爽的夜晚重新伸直,发出沙沙的声音。坎叶河日日夜夜汩汩低语,越过小山,在看不到的远方,住满人家的青草地传来低沉的呼唤。他吐出一口烟,朗诵起海涅的诗。
“是的,很好,非常好。 ‘是的,我创造了奇迹,就像上帝实现了它们。’我还记得,以前,从这里一直到农田那边,树林只有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在旱季,牲口们走来走去,吃着死去的牲口的尸骨。现在,树林又回来了。是一个自由思想者种的,因为他知道,纸上谈兵是不会创造出绿色的。但是这些树木是古老的神灵的信徒——‘基督教的神灵呜呜呼号。’它们不能在丛林里存活,吉斯伯恩。”
这时,跑马道上闪过一个黑影,接着,一个人走了出来,浮现在星光之下。
“我说得没错。啊哈!瞧啊,畜牧农林神福纳斯亲自来看督察官了。嘿,他就是神哪!”
那是毛格利,头戴着白色花环,手里拿着一根剥了一半树皮的枝条走过来,他紧张地看着火光,警觉地防备着,打算一有危险就闪回灌木丛中。
“这是我的朋友,”吉斯伯恩说,“他来找我。嗨,毛格利!”
穆勒还没来得及缓口气,那个人已经站到吉斯伯恩身边,大声说道:“我错了,我不该走。我错了,但是我不知道你在河边杀死的那只老虎的妻子已经醒了,她正在找你。我要知道我一定不会走。她一直在后面跟踪你,先生。”
“他有些疯疯癫癫,”吉斯伯恩说, “他说起这里所有的动物来,都好像是他的老朋友一样。”
“当然,当然。如果连福纳斯都不了解,还有谁了解?”穆勒严肃地说, “他刚才说什么老虎?这个神和你很熟嘛。”
吉斯伯恩又点燃了一根雪茄,开始说起毛格利和他的英雄事迹,等他说完,雪茄烟都快烧到胡子了。穆勒耐心地听着。
“这不是疯癫,”最后,当吉斯伯恩说完毛格利如何驱赶阿布多·加福,穆勒说道, “这根本不是疯癫。”
“那是什么?今天早上,他把我气坏了,因为他不肯告诉我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猜这家伙是着了魔了。”
“不,不是着魔,只是太神奇了。通常这类人会死得很早。
你刚才说,你那偷了东西的仆人说不出是什么在赶着马儿跑,当然大羚羊更不会说了。”
“是的,更可恶的是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仔细听了,要知道我分辨得出大部分的声响,但那头大羚羊和那个人只是一个劲地向前冲,都害怕得发了狂。”
听到这些话,穆勒的反应是把毛格利从头到脚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招呼他走近一点。毛格利像头雄鹿踩着一条臭烘烘的路一样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别怕,不会伤害你的,”穆勒用土语说道,“来,伸出手。”
他顺着毛格利的手臂往上摸了摸,感觉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和我想的一样。再让我摸摸你的膝盖。”吉斯伯恩看着他碰碰毛格利的膝盖骨,笑了起来。他注意到毛格利脚踝上有两三条白色的伤疤。
“小时候留下的吗?”他说。
“啊,”毛格利微笑着回答, “是小动物咬的,是爱的记号。”他的目光越过穆勒投向了吉斯伯恩, “这个先生知道一切。他是谁?”
“等会告诉你,朋友。现在他们在哪里?”
毛格利用手绕着他的头画了一个圈。
“这样啊!你能驱赶大羚羊?看!那是我的母马。你能不能赶她过来,但不惊吓她?”
“我能不能把她赶到先生前面而不惊吓她!”毛格利重复了一遍,稍稍提高了一下嗓门, “只要松开她脚上的绳子,不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么?”
“拔掉拴着马头和马脚的木桩。”穆勒冲着马夫喊了一句。
木桩刚刚离开地面,那匹高大黝黑的澳大利亚母马就昂起头,竖起了耳朵。
“小心点!我可不想她被赶到森林里去。”穆勒说。
毛格利依然站在火光前面—一就像小说里常常描述的希腊神一样伫立着。马嘶叫了一声,抬了抬后腿,觉察到腿上的绳子已经松开了,便飞快地跑向主人,把头凑到他的怀里,微微有些出汗。
“她自己跑过来的!我的马也会这样。”吉斯伯恩叫了起来。
“看看她有没有出汗。”毛格利说。
吉斯伯恩把一只手放在马身上,那上面湿湿的。
“够了。”穆勒说。
“够了。”毛格利重复道,他身后的岩石又把这句话传了回来。
“不可思议吧?”吉斯伯恩说。
“不,只是很神奇——太神奇了。你还不明白吗,吉斯伯恩?”
“我承认,我还是不懂。”
“那好吧,我就不说了。他说过总有一天会告诉你真相的。
我要说了就一点意思也没有啦。不过,他竟然没有死,让人难以理解。现在,听我说,”穆勒对着毛格利,又说起土话来,“我是印度以及黑河沿岸所有丛林的总督。我不清楚我手下到底有多少人——也许有五千吧,也许一万。而你要做的——不是在丛林里穿来穿去,为了好玩或是显摆而追逐野兽,而是在我手下服务,我是政府派来掌管森林的,是驻守在丛林里的长官。
如果没有接到命令让村民的牲口在丛林里吃食,你就把闯进来的牛啊羊啊赶回去;如果上面发了命令呢,要让它们进来;尽可能地控制好野猪和大羚羊的数量;通知吉斯伯恩先生老虎在哪里出没,怎么出没,森林里还有些什么猎物;准确预报所有的森林火灾,因为你能比任何人都更早发觉。做这些工作每月都会有白花花的银子,最后,等你有了老婆,养了牲口,也许还有了孩子,就会有一笔养老金。怎么样?”
“这些正是我——”吉斯伯恩开口说。
“今天早上我的先生跟我提过这个活。我一个人独自走了一整天,一直在考虑这事,我想好了,如果只在丛林里干事的话,我就干。而且只和吉斯伯恩先生一起干。”
“当然。一个星期后会有关于养老金的书面协议寄过来。然后你就住进吉斯伯恩先生给你安排的屋子。”
“我正要和你说这事。”吉斯伯恩说。
“我一看到这个人,就用不着听别人说啦。没有谁能比他更合适当森林看守的了。他是一个奇迹。相信我,吉斯伯恩,总有一天你会发现的。听哪,他是森林里所有野兽的好兄弟!”
“我要是能理解他,我就不会那么烦了。”
“你会明白的。我告诉你,我工作了三十年,只遇到过一个和他一样的男孩,但他死了。有时候人口普查报告里提到这类人,但是他们都死了。而这个人还活着,他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应该活在铁器时代和石器时代之前。他是人类历史的源头——他是伊甸园里的亚当,现在就缺一个夏娃了!不!他比神话还要古老,就像丛林比上帝还要悠久一样。吉斯伯恩,我现在是个异教徒了,仅此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