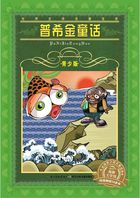维根加河峡谷布满裂缝、风雨剥蚀的岩石,自从有丛林以来就被岩石上的小东西利用了——这是些忙忙碌碌、容易发怒的印度黑野蜂。毛格利很清楚,其实在他们到达峡谷之前半英里的地方,所有通向这里的路都是封锁的。几百年来,从这个裂缝到那个裂缝,小东西成群地飞进去聚居,又成群地分离出来,这样不断地成群分离下去,白色的大理石都沾满了陈年的蜂蜜,在里面的石洞里,他们的蜂房筑得又高又深,不论是人是野兽还是火或者水,从来就碰不到它们。峡谷两边,从上到下好像是垂挂着黑色天鹅绒帷幕,微微泛着亮光,毛格利一看,连忙沉下水去,因为那上面聚集了几百万只野蜂在睡觉。一堆堆像花饰又像腐朽的树干一样的东西密布在岩石表面,那是过去的旧蜂房,或者是在峡谷避风的地方建造的新巢,大团大团海绵状腐烂的垃圾滚落下来,粘在紧贴山岩生长的树木和藤蔓上。他侧耳细听,不止一次听见装满蜂蜜的蜂房沙沙地往下滑,翻转过来,掉进某些黑暗的洞眼里;接着就有愤怒的翅膀扇动I叶J嗡嗡声,浪费掉的蜂蜜一滴一滴沉闷地滴下来,从一些突出出来的岩石上流过,又慢慢地滴落到下面的树枝上。这里河的一边有块小小的河滩,不到五英尺宽,上面高高地堆着无数年月的垃圾。死蜜蜂,雄蜂,废物,旧蜂房,来劫掠蜂蜜的飞蛾昏了头被粘住的翅膀,全都化为优质的黑色尘土,形成表面平滑的一堆堆陈积物。单单是这些垃圾刺鼻的味道,就足以吓跑任何没长翅膀的东西,让他们知道小东西可不是好惹的。
卡又往上游去,到了峡谷头上的一片沙洲上。
“这是今年杀死的,”他说,“瞧!”
岸上躺着两只小鹿和一头水牛的骸骨。毛格利看得出不管是狼还是豺都没有碰过这些骨头,它们很自然地躺在那里。
“他们越过了界线;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法律,”毛格利轻声说, “是小东西杀了他们。趁小东西还没醒,我们走吧。”
“他们在黎明前不会醒来,”卡说, “现在我来告诉你,很多很多个雨季以前,一只公鹿受到追赶,从南边跑来,他不熟悉这里的丛林,后面又有一群家伙紧追不放。恐惧蒙住了他的眼睛,他就从上面跳了下来,那群家伙看见了,也奔过来,他们太急切了,顾不上到了什么地方。太阳升得很高,小东西非常多而目.非常愤怒。那群家伙当中也有很多往维根加河里跳,可是没等他们碰到水面就死了;那些没有跳的也死在岩石上。
然而那只公鹿却活着。”
“怎么会呢?”
“因为他是最先闯进来的,是在逃命,在小东西觉察到之前就跳了下去,还没等他们聚集起来追杀就已经到了河水里。那群跟在后面的家伙,在小东西的威力之下,全都丧了命。”
“那只公鹿却活着?”毛格利慢慢地重复道。
“至少那时他没死,尽管那时没有谁在下面等着他跳下来,用强壮的身体接住他,让他安全入水;可是一个又老又胖又聋的黄扁头会在下面等着人的小孩子——尽管所有的德坎野狗都在后面追。你认为怎么样?”卡的脑袋贴着毛格利的耳朵;过了一小会儿,男孩才回答。
“这是去拔死神的胡子,不过——卡,你是,确实是,整个丛林里最聪明的。”
“这话我可听多啦。你看,如果野狗追赶你——”
“他们肯定会追赶。噢!噢!我舌头底下有很多小小的尖刺,要刺进他们的皮里。”
“如果他们不要命地追赶你,留神点你的肩膀,那些没死在上面的家伙会在这里或者再往下一点的地方落水,小东西就会飞过来,罩住他们。现在维根加河河水很急,他们可没有卡在下面接住,如果还活着,也会冲到下游西奥尼狼窝附近的浅水滩那儿,你的狼群可以在那里对付他们的喉咙。”
“啊哈!哎哇哇!再好也没有了,就像干旱季节落下的雨。
现在只剩下跑和跳的小问题了。我要让野狗见识一下我,好让他们紧追不舍。”
“你看见过上面的岩石吗?从陆地那边看过没有?”
“还真没有。这点我倒忘记了。”
“去看看。上面那片岩石经风沐雨,千疮百孔。你脚下一不留神就会毁了这场狩猎。你留在这里好好看看,我去传话给狼群,让他们知道在哪里等待野狗。这只是因为你,至于我自己,跟任何一只狼都没有什么交情。”
跟不喜欢的动物打交道,卡往往表现得比丛林里所有的动物——也许只有巴赫拉除外——都更加不高兴。他向下游游去,来到法奥和阿克拉坐的岩石上,他们正在听夜里的动静。
“哈咝!狗们,”他快活地说,“野狗会沿着河下来,如果你们不害怕的话,就在浅水滩这里杀死他们。”
“他们什么时候来?”法奥问。 “我的那个小孩子呢?”阿克拉问。
“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卡说, “等着看吧。说到你的那个小孩子嘛,你们已经听到过他立下的誓言,就这样让他去面对死亡。你的小孩子和我在一起,要是他现在还没死掉的话,也不是你这只褪了色的狗的过错!在这里等待野狗吧,人的小孩子和我一起站在你们这一边战斗,你们应该高兴。”
卡闪动着身子又往上游游去.在峡谷中间停住,抬头仰望峭壁。不一会儿看见毛格利的脑袋在星光下移动,接着空中嗖的一声,一个清晰的身影落下来,脚先着水,转眼间男孩已经靠在了卡盘起的身体里。
“夜里不用再跳了,”毛格利平静地说, “我已经试跳过两次了。但那上面真是个凶险的地方——低低的灌木丛上,深深的沟壑里,密密麻麻都是小东西。我在三条沟壑的边上垒了一些大石头,到时候我一边奔跑一边用脚把它们踢下去,小东西就会在我后面飞起来,肯定个个怒气冲冲。”
“这是人说的话,是人的机智,”卡说, “你很聪明,不过小东西总是怒气冲冲的。”
“不,黄昏的时候远远近近有翅膀的家伙都会休息一会儿。
我就在黄昏的时候逗引那些野狗,因为野狗最善于在白天打猎。
现在他们正在循着独行者的血迹追踪呢。”
“奇尔不会放过死牛,野狗也不会放过血迹。”卡说。
“到时候我给他们留下一条新的血迹,用他们自己的血,如果能够的话,再给他们些脏东西尝尝。你会留在这里吧,卡,等着我和追赶我的野狗来到?”
“哎。不过如果他们在丛林里就把你杀死了,或者在你还没跳进河里之前小东西就把你杀死了,怎么办?”
“明天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为明天打猎,”毛格利引用了一句丛林俗话,接着又说道, “我死了的时候就唱死亡之歌。打猎好运,卡!”
“拿着你的尾巴,来追吧。”
他松开搂着卡的脖子的胳膊,像泛滥河水中的一根圆木头一样顺着峡谷而下,向远处的岸边划去,他在那里发现水流平缓,开心地放声大笑。毛格利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拔死神的胡子”,使整个丛林居民都感觉到他是他们的主人。他经常在巴鲁的帮助下劫掠单棵树上的蜂窝,知道这些小尔西不喜欢野蒜的气味。因此他采集了一小捆野蒜,川树皮绑起来,然后沿着独行者从南方狼窝一路奔来洒下的血迹,走了“英里左右。他头扭向一边,望着树木,一边望一边咯咯地笑。
“青蛙毛格利我已经做过了,”他对自己说, “野狼毛格利我也已经说过我现在就是。我得做做猿猴毛格利了,之后我再做公鹿毛格利。最后我才成为人毛格利。噢!”他的拇指从刀口卜轻轻滑过,试了试他那把十八英寸长的刀。
独行者走过的路上,洒着斑斑点点暗红色的血,血迹在一片密林里穿行,其间树木一棵紧挨着一棵;树林向东北延伸,在距离野蜂岩不到两英里的地方,渐渐变得稀疏起来。从树林最后的一棵树到野蜂岩的矮树丛之间,是一片开阔地,几乎连一只狼也藏不住。毛格利在树下小跑,判断着树枝和树枝之间的距离,偶尔爬到树上,试一试从这棵树跳到另一棵树。最后他来到开阔地,在那里非常仔细地研究了一个小时。然后他又转过身,回到他刚才离开的有独行者踪迹的地方,在一棵树上安顿下来。那棵树长着一根伸出来的树枝,离地八英尺高,他安安静静地坐在上面,在脚底板上磨着那把刀,还独自哼唱着什么。
快到中午了,太阳火辣辣的,他听见嗒嗒的脚步声,闻到了野狗群散发出来的可恶的味道,他们一路小跑着过来,冷酷无情地追踪独行者的足迹。从上面看下去,红狗还没有狼的一半大,可是毛格利知道他们的脚和牙齿有多么厉害。他看到领头的那只野狗栗色的脑袋沿着踪迹嗅来嗅去,就招呼了一声:“打猎好运!”
那只畜生抬起头,他的伙伴们在他后面停下来。一时难以计数的红狗都低垂着尾巴,宽肩细腿,长着血红的嘴巴。这种野狗通常是沉默寡言的一族,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丛林里,也很不讲究礼貌。足足有两百只红狗聚集在他下面,他看得出那些领头的饥饿地嗅着独行者的踪迹,努力想拉野狗群继续向前。
这绝不能成,要不天还大亮着他们就赶到狼窝那里了。毛格利打算拖住他们,让他们在树下呆到黄昏。
“谁允许你们到这里来的?”毛格利问。
“所有的丛林都是我们的丛林。”这就是回答,野狗张口时露出了白牙。毛格利微笑着往下看了看,惟妙惟肖地模仿起基凯尖尖的叽叽喳喳声来,基凯是德坎的跳鼠,毛格利想让野狗明白,他认为他们不比跳鼠好多少。野狗群围住那棵树,领头的那只凶狠地吠叫起来,骂毛格利是树上的猴子。毛格利的回答是,向下伸出一条赤裸的腿,就在那个头领的头上扭了扭他光滑的脚指头。
这就足够了,大大的足够了,足够唤起野狗群愚蠢的愤怒。那些脚趾之间长毛的家伙最忌讳提到这一点。那个头领跳起来时,毛格利就把脚拿开,并且柔声说道:“狗,红狗!回到德坎去吃蜥蜴吧。回到你们的兄弟基凯那里去——狗,狗——
红红的狗!脚趾之间长毛的红狗!”他第二次扭动起他的脚指头来。
“趁我们还没把你饿死,快下来,没长毛的猴子!”野狗群吼叫起来,而这正是毛格利想达到的效果。他顺着树枝躺着,脸贴着树皮,有手自由自在地比比画画,骂野狗群,骂他想得到和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他们的举止,他们的习惯,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小崽子。世界上没有什么话像丛林居民表示蔑视的语言那样充满仇恨,那样满是尖刺。如果你来好好想想,你就会明白这些话有多么厉害了。正像毛格利告诉卡的那样,他舌头底下有很多小小的尖刺,他慢慢地、沉着地把野狗从沉默逼到咆哮,从咆哮逼到狂吠,从狂吠逼到声音嘶哑、唾液四溅、语无伦次。他们想对他的辱骂进行还击,可是这个小孩子可能也试过怎样还击愤怒中的卡。毛格利的右手弯曲着,贴在身子的一边,时刻准备采取行动,他的脚牢牢钩住树枝。栗色脑袋的头领往空中跳起了好多次,但毛格利怕失手不敢随便冒险。终于,狂怒给了他超出自然的力量,他一下子蹿到离地七八英尺高的空中。毛格利的手像一条树蛇的头一样飞快地伸出去,一把抓住他背颈上的皮,树枝突然承受了野狗的重量,压得嘎嘎摇动,毛格利差点被晃荡到地上。然而他绝不松手,一点一点地把这只畜生拽上来,让他像一只淹死的豺一样,吊在树枝上。他左手拿出刀,割掉了野狗那根毛茸茸的红色尾巴,然后又把他扔回地上。
这正是他所需要的。野狗群不会再向前去追踪独行者的踪迹了,除非他们杀死毛格利或者毛格利把他们杀死,决不肯罢休。他看见他们抖抖索索地蹲下来,围成一圈,这表示他们要呆在这里,于是他就爬到更高的一个树权上去,背靠着树,舒舒服服地睡起觉来。
三四个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数了数野狗。他们都还在这里,沉默,强壮,冰冷,眼睛闪出钢一样的光。太阳开始落山了,半个小时后岩石上的小东西就要结束劳作了。你知道,野狗在黄昏的时候搏斗,不是处在最好的状态。
“我不需要这样忠诚的看守,”他温和地说着,在树枝上站了起来, “不过我会记住这一点的。你们是真正的野狗,但是在我看来你们这个品种数目太多了,为了这个原因我不想把尾巴还给这个吃蜥蜴的大家伙。你很不高兴吧,红狗?”
“我要亲自撕开你的肚皮!”那个头领吼叫道,在树根上猛抓。
“不,还是考虑考虑吧,聪明的德坎老鼠。不久就会有很多窝没有尾巴的小红狗了,啊,剩下光秃秃的红尾巴根碰着滚烫的沙子,那滋味可不好受。回家吧,红狗,一只猴子干了这样的好事,你们哭去吧。你们还不走吗?那就跟我来,我会让你们变得非常聪明!”
他像猴子一样,从一棵树荡到下一棵树,再荡到下下一棵树,再荡到下下下一棵树,野狗群抬着头干着急,只好在下面紧追不舍。他还不时地装出要掉下来的样子,野狗群急于结果他的性命,争先恐后地跑过来,不惜互相践踏。这真是一幅奇妙的景象——男孩拿着刀,西斜太阳的光线从树枝问透过来,映照得尖刀闪闪发亮,下面是一群紧追不舍的狗,挤作一堆,沉默不语,红色的毛皮像燃烧着似的。当他跳到最后一棵树上的时候,他拿起野蒜仔细地擦遍全身,野狗很瞧不起地叫起来。
“说狼话的猴子,你想掩盖身上的气味吗?”他们说, “我们要把你追到死。”
“拿着你的尾巴,”毛格利说着,向后把尾巴朝过来的路上一扔,野狗群本能地冲过去, “来追吧——追到死。”
他溜下树干,野狗还没看见他要干什么,就像风一般赤脚向野蜂岩奔去。
狼群和红狗的生死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