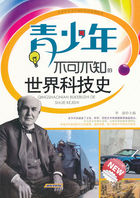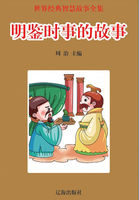就在这时,唯一被允许参加狼群大会的异类动物——巴鲁,后脚直立起来,嘟嘟囔囔说话了。巴鲁是只褐色熊,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他教给狼崽子们丛林法律。老巴鲁可以随处自由走动,因为他只吃坚果、根块和蜂蜜。
“人的小孩子——人的小孩子?”他说道, “我为人的小孩子说话。人的小孩子没有什么危害。我没有说话的天赋,可是我说的是真话。让他和狼群一块奔跑,让他和其他狼崽子一块加入狼群。我自己来教他。”
“还有谁?”阿克拉问, “巴鲁已经说过了,而且他是小狼崽子的教师。还有谁说话?”
一条黑影跳进圈子里,是黑豹巴赫拉。他全身墨黑,可是在月光下就显出水纹绸一般的豹斑。没有哪个动物不认识巴赫拉,也没有哪个动物愿意招惹他。他像塔巴克一样精明,像野水牛一样凶猛,像受伤的大象一样不管死活。但是他的声音像从树上滴下来的野蜂蜜那样软绵绵的,他的皮肤比羽毛还要柔软。
“噢,阿克拉,还要自由的兽民们,”他以愉快的声调说道,“我没有权利参加你们的集会;但是丛林法律说,对于处理一个新崽子,如果有r疑问,又不到把他杀了的地步,就可以出个价买下他的性命。法律并没有说谁可以买,谁不可以买。我说的对吧?”
“对!对!”那些总是饿着肚子的年轻的狼说道, “听巴赫拉说吧。这个小崽子是可以出一个价买下的。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我知道我在这里没有说话的权利,所有我请求你们允许。”
“说吧。”二十只狼同声喊道。
“杀死一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子是可耻的。而且,等他长大的时候,他还会给你们捕到更多的猎物。巴鲁刚才已经为他说了话。现在在巴鲁的话之上,我再加上一头公牛,一头刚刚杀死的肥公牛,就在离这儿不到半里的地方,只要你们按照法律规定接受这个人的小孩子。这样做有什么困难吗?”
立即响起了一片闹哄哄的声音:“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会被冬天的雨淋死,会被太阳考焦。这样一只光着身子的青蛙能给我们造成什么危害呢?就让他和狼群一起奔跑吧。公牛在哪里,巴赫拉?我们就接受他吧。”这时阿克拉发出了低沉的喊声:“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吧,狼们!”
毛格利仍然沉浸在对鹅卵石的兴趣里,根本就没注意到一只接一只的狼走过来端量他。最后,他们全都下山去找那头死公牛了,只剩下阿克拉、巴赫拉、巴鲁和毛格利自己这一家的狼。谢尔可汗仍然在黑夜里不停地咆哮,毛格利没有交给他,他恼怒透顶。
“哼,你就好好吼叫吧,”巴赫拉的嘴在胡子底下动着,“总有一天,这个光身子的小家伙会让你的吼叫变个调的,如果不是这样,就算我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
“这件事这样做是对的,”阿克拉说道, “人和他们的孩子是非常聪明的。到时候说不准他就成了我们的帮手。”
“确实是这样,需要时候的一个帮手;因为没有谁能够永远领导狼群。”巴赫拉说。
阿克拉默不作声。他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个狼群的每一个头领都会渐渐耗尽力气,越来越衰弱不堪,直到最终被狼群杀死,出现一个新的头领一一然后,又轮到这个新的头领被杀死。
“把他带回去吧,”他对狼爸爸说, “可要把他训练成一个合格的自由兽民。”
毛格利就是这样进入了西奥尼的狼群,凭着一头公牛和巴鲁善良的话。
毛格利被赶出了狼群
现在,你必须跳过整整十年或者十一年的时间,而不要觉得有什么遗憾,你自己可以猜想毛格利在狼群中度过的美好生活,要是把这段生活都写出来的话,非得写满好几本书不可。
他和狼崽子们一起成长,当然,当他还仍然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成年狼了。狼爸爸教给他各种各样的本领,告诉他丛林里许多事物的含义,直到草叶的每一声微小响动,温暖夜空的每一阵呼吸,头顶上猫头鹰的每一声啼叫,树枝上栖息片刻的蝙蝠脚爪的每一下抓挠,水塘里小鱼跳跃时的每一下溅水声,这一切对他都意味丰富,熟悉亲切,就像商人对他办公室里的工作一样。在不学习本领的时候,他就在太阳下睡觉,然后吃饭,然后再睡;他感到自己脏了或热了的时候,就到森林里的水塘游泳;想吃蜂蜜了(巴鲁告诉他,蜂蜜和坚果像生肉一样美味可口),就爬上树,巴赫拉教会了他怎么做。巴赫拉会躺在一根树枝上,叫道:“来呀,小兄弟。”一开始,毛格利只能像树獭一样紧紧抱住树枝不放,到后来,他已经能在树枝间攀援跳跃,如大灰猿一般大胆。他也在会议岩石那儿有了自己的位置,狼群集会的时候,他发现,如果他死死地盯着一只狼看,那只狼就会被盯得低下眼睛,他觉得这很好玩,就常常盯着某一只狼看。还有些时候,他会帮助他的朋友们从脚掌心拔出长刺,扎进狼的皮毛里的芒刺使他们非常痛苦。晚上他下山潜入耕地,十分好奇地看着小屋里的村民们,但是他对人不信任,因为巴赫拉曾经指给他看一只方盒子,非常巧妙地隐藏在丛林里,他差点就走了进去,巴赫拉说,这就是陷阱。他最喜欢做的事是和巴赫拉一起走进大森林温暖幽暗的深处,懒洋洋地睡上一整天,到了晚上看巴赫拉怎么捕杀猎物。巴赫拉饿了的时候,见到什么猎物就捕杀什么,毛格利也一样——只有一种猎物例外。毛格利长到能懂事的时候,巴赫拉就告诉他,他被狼群接纳,是用一只公牛的生命换来的,所以他以后永远也不要碰牛。 “整个丛林都是你的,”巴赫拉说, “只要你足够强大,你就可以捕杀任何猎物;但是因为那只公牛赎买过你,你绝对不能杀死或吃掉任何一只牛,不管是小牛还是老牛。这是丛林法律。”毛格利忠心服从了。
毛格利长得越来越壮了,就像一个男孩一定会是的那样,他不知道自己正在学很多东西,除了吃,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左思右想。
狼妈妈有一两次告诉他,谢尔可汗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家伙,将来有一天他一定要杀了谢尔可汗;一只年轻的狼会时时刻刻记住这样的忠告,可是毛格利却把它忘了,他毕竟只是一个小男孩呀——尽管如果他会用人的语言说话的话,他也会把自己叫做狼的。
他常常在丛林里遇见谢尔可汗。阿克拉越来越老、越来越弱了,瘸腿老虎成了狼群里那些年轻狼的好朋友,他们跟在他后面,吃他剩下的东西。要是阿克拉敢于严格行使他的权威的话,这种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谢十尔可汗还讨好他们,说他感到奇怪,这么优秀的年轻猎手为什么会情愿受一个垂死的老狼和一个人的小孩子的领导。“我听说,”谢尔可汗道, “在大会上你们都不敢正眼看他。”年轻的狼听了,气得毛都竖了起来,一阵乱叫。
巴赫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件事也知道了一些,就一次两次明确地对毛格利说,谢尔可汗总有一天要杀死他。毛格利听了,笑着回答:“我有狼群,有你,还有巴鲁,尽管他挺懒的,可是还是会帮我一把的。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这天,天气非常暖和,一个新的念头钻进了巴赫拉的心里——这是从他听说的一件事受到启发的。也许是伊基告诉他的。他和毛格利来到丛林深处,毛格利头枕着巴赫拉漂亮的黑皮躺在那里,这时,他问毛格利:“小兄弟,我告诉你谢尔可汗是你的敌人,这话说过几次了?”
“棕榈树上的硬果子有多少,你说过的次数就有多少。”
毛格利回答道。自然,他是不会数数的。“怎么了?我可困了,巴赫拉。谢尔可汗不就是长尾巴、说大话——像孑L雀莫奥一样吗?”
“但是现在可没有时间睡觉了。这一点巴鲁知道,我知道,整个狼群都知道;就连愚蠢透顶的鹿也知道。塔巴克也告诉过你了。”
“噢!噢!”毛格利说道, “前不久塔巴克跑到我跟前,粗鲁地说我是个光着身子的人的孩子,不该去挖植物的块根。我抓住塔巴克的尾巴朝棕榈树上甩了两下,教训他懂点礼貌。”
“这么做很不明智。尽管塔巴克是个恶作剧的家伙,可是他还能告诉你一些和你关系密切的事情。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小兄弟。谢尔可汗不敢在丛林里杀你;但是你要记住,阿克拉已经很老了,很快他就杀不死公鹿了,那时他就不能再当头领了。当年你第一次被带到狼群大会上时,那些仔细端量过你的狼大多也老了,而那些年轻的狼听了谢尔可汗的教唆,都认为人的孩子不应该在狼群里占有一席之地。用不了多少时间,你就会成为一个人了。”
“成了人就不能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奔跑吗?”毛格利说,“我是在丛林里生的。我服从丛林法律。我们狼群里没有一只狼,我没有帮他拔出过爪子上的刺。他们当然都是我的兄弟!”
巴赫拉伸直了身子,半闭着眼睛。 “小兄弟,”他说, “你来摸摸我的下巴。”
毛格利强壮的棕色的手,伸到巴赫拉光滑的下巴底下,那里厚厚的毛遮住了滚圆的肌肉,可是毛格利也摸到了一小块光秃秃的地方。
“丛林里谁也不知道我巴赫拉身上有这个标记——戴过颈圈的标记;小兄弟,我是在人问出生的,我妈妈也是死在人间——死在奥得普尔王宫的笼子里。就是因为这个,当你还是个赤身露体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会在狼群大会上为你付出那笔价钱。是的,我也是在人间出生的。那时我从来没有见过丛林。他们把我关在铁栅栏里,用一只铁盘子喂我,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感觉到我是巴赫拉——是黑豹——不是人的玩物,我一爪子砸开了那把破锁,跑了出来。正是因为我学到了人的那一套,所以我在丛林里比谢尔可汗更加可怕。是不是这样?”
“是的,”毛格利回答, “丛林里谁都怕你,除了毛格利。”
“啊,你是人的孩子,”黑豹十分温柔地说道, “就像我最终回到了丛林,你最终也必须返回人间——返回到你人的兄弟们中间去,如果你在狼群大会上不被杀死的话。”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杀死我?”毛格利问。
“你看着我,”巴赫拉说。毛格利紧紧地盯住了他的眼睛。
才过了半分钟,大黑豹就把头扭开了。
“这就是原因,”他说着,挪动了一下踩在树叶上的脚爪。
“即使是我,也不能眼睛对着眼睛看你,我还是在人间出生,而且还爱你呢,小兄弟。其他的动物恨你,因为他们不敢眼睛盯着眼睛看你——因为你聪明——因为你从他们的脚上拔出过刺——因为你是人。”
“我不懂这些事情。”毛格利闷闷不乐地说。他紧皱着黑色的浓眉。
“什么是丛林法律?先动手,再说话。就是因为你满不在乎,他们感到你毕竟是个人。你要聪明一点。我心里清楚,如果下一次打猎阿克拉没有捕到猎物——现在每一次打猎都要消耗掉很大的力气他才能捕到一只公鹿——狼群就会起来反对他,也反对你了。他们会在岩石那儿举行丛林大会,到那时——到那时——我想出办法来了!”巴赫拉说着,跳了起来, “你马上下山,到山谷里人住的小屋子里去,拿回一些他们种的红花,这样,到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更有力量的朋友,比我、比巴鲁、比狼群里爱你的那些伙伴都更有力量。快去取红花来!”
巴赫拉所说的红花,指的是火,只不过丛林里没有哪一只动物能恰当地叫出火这个名字。每一个动物都怕火怕得要死,他们发明出上百种方式描绘它。
“红花?”毛格利说, “就是在他们的小屋外面微弱的光线下开放的那种吧。我去取一些来。”
“这才像人的孩子说的话,”巴赫拉骄傲地说, “记住它是种在小盆子里的。快去拿一盆来,留到需要的时候用。”
“好!”毛格利说, “我这就去。可是你是不是肯定,啊,我的巴赫拉,”——他伸出胳膊,环抱着巴赫拉漂亮的脖子,深深地盯着他的大眼睛——“你肯定这一切都是谢尔可汗于的吗?”
“凭着那把我砸开的锁发誓——我因此而得到自由,我肯定,小兄弟。”
“那么,凭着赎买我的公牛发誓,我要为此与谢尔可汗算总账,也许他要多付一点呢。”毛格利说完,跳跃着跑开了。
“这才是人。这才是完整的人,”巴赫拉自言自语地说着,又躺到地上, “啊,谢尔可汗,从来就没有哪一次打猎,比你十年前的那次捕捉青蛙更不吉利的了!”
毛格利穿越森林,越离越远。他用力跑得飞快,心里像有火在烧一样。他来到狼洞的时候,晚问的薄雾已经升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