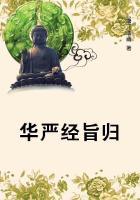老熊默不作声,但他想到了许多。
毛格利抄近路无声无息地穿越丛林,朝布尔迪来的那条路的方向走去。后来,他分开灌木丛,看到了那个老头,肩上扛着枪,循着前一天晚上的踪迹往前小跑。
狼群唱起丛林晨歌
你一定还记得,毛格利离开村子的时候,肩上扛着谢尔可汗的皮,分量很重,阿克拉和灰兄弟跟在后面一路小跑,他们三个的足迹非常清晰。不一会儿,布尔迪就走到了阿克拉回去把足迹弄混乱的地方。然后他坐下来,又是咳嗽又是嘟囔,还向周围的丛林东张西望,想重新找到足迹,他还不时地向丛林里扔石头,正好从观察他的那几个头上飞过。要是狼不想被听到,就没有什么能比他们更悄无声息;毛格利,尽管狼认为他行动起来很笨拙,可是也能来去像影子一般。他们把这个老头包围起来,就像一群海豚围着全速前进的轮船一样,一边包围还一边漫不经心地交谈。他们说话的声音低到极点,没有受过特别训练的人听不见。 (蝙蝠芒恩的高声尖叫是声音的另一个极端,许多人也根本就没法听见。所有的鸟、蝙蝠和昆虫都能用这种高音交谈。)
“这可比杀死他好玩,”灰兄弟说。那时布尔迪正弯腰、打量、喘气。 “他看起来像一头在河边的丛林里迷了路的猪。他在说什么?”布尔迪正恶狠狠地嘟囔。
毛格利翻译道:“他说狼群一定在我周围跳过舞。他说他这一辈子都没看见过这么混乱的足迹。他说他快累死了。”
“他在重新找到足迹之前会休息一下的,”巴赫拉冷冷地说,他从树干上溜下来,加入到他们正在玩的这场捉迷藏的游戏,“哎,那个瘦东西在于什么?”
“把烟吃进去,又吹出来。人老是用嘴玩这种把戏。”毛格利说道。这些悄无声息的追踪者看着那个老头装水烟筒,点燃,吧嗒吧嗒地吸,接着就闻到了烟昧,就凭着这味,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在最黑最黑的夜晚也能确认出布尔迪的位置。
一小群烧炭人从小路上走来,他们自然要和布尔迪打招呼,他这个猎人至少在方圆二十里以内是有名的。他们都坐下来抽烟,巴赫拉和其他几个都靠近来监视。布尔迪讲起毛格利的故事,说他是个魔孩,从头讲到尾,还不断地添油加醋。讲他布尔迪自己如何确实杀死了谢尔可汗;讲毛格利怎样变成了一只狼,和他搏斗了整整一个下午,又变回来成了一个男孩,对他的枪施了魔法,打出去的子弹拐了弯,明明瞄准的是毛格利,却打到他布尔迪自己的水牛身上;讲村子里的人因为他是最勇敢的猎人,就派他来杀死这个小魔孩。他还说村子里的人已经把米苏阿和她丈夫抓了起来——他们毫无疑问就是这个魔孩的亲生父母——关在他们自己的屋子里,马上就要拷问,要他们承认是巫婆和巫师,然后就把他们烧死。
“什么时候?”烧炭人问,他们十分愿意现场看到这样的仪式。
布尔迪说,他不回去,是不会烧死他们的,因为村子里的人希望他先杀死那个丛林男孩。在这以后,他们才会处置米苏阿和她丈夫,分他们的地,分他们的牛。米苏阿的丈夫有一些非常出色的水牛。布尔迪认为,消灭巫师真是一件大好事;那些接纳丛林狼孩的人,肯定就是所有巫婆中最坏的巫婆。
可是,那些烧炭人问,如果英国人听到了这事会怎么样呢?
他们听说英国人是十足的疯子,不会平心静气地允许诚实的农民杀死巫婆。
那有什么,布尔迪说道,村子里的头人会报告说米苏阿和她丈夫被蛇咬死了。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只等着杀死那个小狼孩了。他还问他们,没有碰见过那个畜生吗?
烧炭人小心翼翼地看看四周,感谢福星高照,他们没有碰见过那个畜生。他们毫不怀疑,像布尔迪这样勇敢的人一定能够找到他,如果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他们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赶到布尔迪的村子去看看那个邪恶的巫婆。布尔迪说道,尽管他的职责是杀死那个魔孩,可是他不想让这些没有武器的人就这样穿过丛林,没有他的保护,那个狼妖随时都会出现。因此,他要陪着他们,如果巫婆的孩子出现的话——正好让他们看看西奥尼最棒的猎人是怎么对付这种事的。他说,婆罗门给了他一个符咒,对付妖怪,万无一失。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每过几分钟,狼就会重复地这样问。毛格利给他们翻译,但听到巫婆什么的,他自己也不大懂,于是就只是告诉他们,对他很好的那个男人和女人被弄到陷阱里了。
“人用陷阱对付人?”巴赫拉问。
“他是这样说的。有些话我也不大懂。他们一定全都疯了。
米苏阿和她男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他们要被弄到一个陷阱里?
他们谈到红花,这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去看看。不管他们要对米苏阿做什么,布尔迪不回去,他们是不会做的。所以——”
毛格利苦苦思索着,手指抚弄着剥皮刀的刀把。这时,布尔迪和烧炭人排成单行,勇敢地动身了。
“我得赶快回到人群那里。”毛格利终于想出了主意,说道。
“这些人怎么办?”灰兄弟用饥饿的眼光看着烧炭人棕色的后背,问道。
“用歌声送他们回家,”毛格利说时笑了一笑, “我不想让他们在天黑以前到达村口。你们能牵扯住他们吗?”
灰兄弟不屑地咧咧嘴,露出白色的牙齿。 “我们可以像牵羊一样,领着他们转上一个圈又一个圈——如果我对人还算了解的话。”
“这倒不必。给他们唱点歌,免得路上寂寞,灰兄弟,也不必唱得太美妙动听。巴赫拉,和他们一起去吧,帮着唱唱歌。
黑夜降临的时候,和我在村口会合——灰兄弟知道那个地方。”
“为人的小孩子追猎,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事。我什么时候才能睡上一觉呢?”巴赫拉说着,打了个呵欠,可是他的眼睛还是流露出这种消遣引起的兴奋, “要我给没有毛的人唱歌!我们就试一试吧。”
他低下头,以便声音能够传开去,接着就发出了长长、长长的吼叫: “打猎好运——”半夜的吼叫下午就响了起来,一听就相当可怕。毛格利听到这个声音在他身后隆隆响起,起起伏伏,最后又变成呜呜声,令人毛骨悚然。毛格利穿越丛林,自己对自己笑了。他能看见烧炭人吓得挤成了一堆,老布尔迪的枪筒像香蕉叶子似地摇晃着,到处乱指。紧接着,灰兄弟发出了“呀——啦——嘿!呀啦哈!”的呼喊,当狼群追赶印度大羚羊、青灰色的母牛时,就发出这种叫声,这声音似乎来自世界的尽头,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以一声急促的尖叫戛然而止。另外三只狼响应着,后来,毛格利可以发誓是整个狼群都在响应着,拼命喊叫。接着,所有的狼都一同唱起雄伟壮丽的丛林晨歌,每一个转折,每一个装饰音,每一个优美的音符,狼群里每一只张大嘴巴的狼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下面是粗略翻译过来的这首歌的大意,你必须想象一下,这种声音打破丛林下午的宁静时的情景——
再过一会儿,我们的身体
就不会在平原上投下阴影;
现在它还黑得分明,紧跟我们的行踪,
飞奔在回家的小径。
在清晨的寂静中,每块岩石和每棵树木
都高高挺立,活生生、强硬硬。
我们高声呼喊:“好好休息,
所有遵守丛林法律的生灵!”
丛林居民身上的角和毛
与隐蔽的地方难分难辨融在一道;
我们的丛林大王,也躲进洞里和山间,
蜷着身子,静悄悄。
这会儿只有被人驯服的牛在卖力,
套着新轭犁地来回跑;
这会儿破晓的黎明红彤彤,
光芒挂上树梢。
噢!快回窝里去!太阳
在喘息的野草后面闪耀。
新竹子沙沙作响,
提醒的低语在其间传告。
我们夜里眨眼来回巡视的树林,
被白天弄得陌生了不少;
野鸭在天空下喊道:
“白天——白天向人讨好!”
湿我们的皮毛、洗我们道路的露水,
被太阳晒得无踪无影;
我们喝水处那满是泥水的岸边,
正被烤得干烘烘、梆梆硬。
黑夜叛变了,把每一道痕迹
都出卖给白天和光明。
我们听到高声呼喊:“好好休息,
所有遵守丛林法律的生灵!”
无论如何,翻译都不能表达出实际的效果,也不能体现出四只狼唱每一个字时显露的轻蔑,他们听到树枝劈啪响,原来那些人手忙脚乱地爬到了树上,布尔迪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念符文咒语。于是,动物们躺下来睡觉,因为,像任何靠自己的能力生存的动物一样,他们需要保持头脑清晰;如果不睡觉,没有谁能够很好地思考处理问题。
毛格利救出人妈妈
这时,毛格利已经把好几英里抛在了身后,他一小时走九英里,轻轻松松地前进,他很高兴在人群里拘束了好几个月之后,自己还能这样适应丛林。他脑子里有个念头,就是把米苏阿和她丈夫从陷阱里救出来,不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陷阱;人把这种陷阱叫做屋子,可是他天生对任何陷阱都不信任。后来,他又对自己许愿,他要好好和这个村子算账。
黄昏的时候,他看见了那片记忆犹新的草场和那棵大树,那天早晨灰兄弟就是在那里等他的,然后他杀死了谢尔可汗。
他对人和人的群体非常气愤,一看见村子的屋顶,就有什么东西涌上了喉咙,使他喘不过气来。他注意到人们都从田地里回来了,比平常早,可是他们不回去做晚饭,却在村子的大树下聚了一堆,叽叽喳喳,乱喊乱叫。
“人总是为人制造陷阱,要不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毛格利说, “昨天晚上关在陷阱里的是毛格利——可是那个夜晚仿佛过去了好几个雨季。今天晚上是米苏阿和她男人。明天,或者再过许多个晚上,大概又要轮到毛格利。”
他在村子的围墙外面往前爬,来到米苏阿的屋子外,从窗子向屋里看。米苏阿躺在地上,嘴里塞着东西,手脚都被绑住了,呼吸闲难,不停地呻吟;她丈夫被绑在油漆得很鲜艳的床架上。小屋朝街道开的门关得紧紧的,三四个人坐在门外,背对着门。
毛格利非常清楚村里人的行为和习惯。他敢保证,只要他们在吃饭、谈话、抽烟,他们就不会去做别的任何事情;但是只要一吃饱,他们就变得危险了。布尔迪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要是护送他的动物们尽到了职责,他就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好讲了。他从窗子里跳进屋里,弯下腰去,割断了男人和妇女身上的皮绳,拿出了塞在他们嘴里的东西,四下打量,想找一些牛奶给他们喝。
米苏阿被疼痛和恐惧折磨得半疯了(整整一上午她都在挨打、挨石子),毛格利赶紧用手捂住她的嘴,她才没尖叫出来。
她丈夫气昏了头,坐在那里从被揪得乱七八糟的胡子上清理脏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他会来的,”米苏阿终于哽咽着说道,“现在我知道他就是我的儿子!”她把毛格利紧紧地搂到怀里。
毛格利一直十分镇静,可是这会儿全身开始发抖,这使他非常吃惊。
“为什么要用这些皮绳?他们为什么要把你们绑起来?”过了一会儿,他问。
“因为生了你这样一个儿子,所以要把我们处死——别的还会为什么?”男人阴沉着脸,说道, “瞧!我都流血了!”
米苏阿什么也没说,毛格利看着她的伤口,他看见血的时候,他们听到他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这是谁干的?”他问, “我要找他算账。”
“全村子的人都干了。我太富了,有很多牲口,所以她和我就成了巫师,还因为我们收留了你。”
“我不明白。让米苏阿讲给我听吧。”
“我给你牛奶喝,纳索,你还记得吗?”米苏阿小心地说,“因为你是我那被老虎叼走的儿子,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他们说我是你的妈妈,是一个魔鬼的妈妈,所以就得处死。”
“那什么是魔鬼?”毛格利问, “死我倒是见过。”
男人阴沉地抬头看了看,米苏阿却笑了。 “你瞧!”她对丈夫说, “我知道——我说过他不是巫师。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不管是儿子还是巫师,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男人答道,“反正我们已经死定了。”
“那边的一条路通向丛林,”毛格利从窗口指出去, “你们手脚都自由了,赶快走吧。”
“我们不熟悉丛林,我的儿子,不像你那么熟悉,”米苏阿开口道, “我想我走不了多远。”
“那些男男女女会追上来…又把我们拉到这里来。”丈夫说。
“嗯,”毛格利说道,他用剥皮刀的刀尖轻轻划着手掌,“我不想伤害这个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可是,我看他们阻挡不了你们。过一会儿,他们就会有其他很多的事伤脑筋。啊!”
他抬起头,听着外面的喊叫声和脚步声, “他们终于让布尔迪回来了?”
“他今天早晨被派出去杀你,”米苏阿哭道, “你碰见了他吗?”
“是的——我们——我碰见了他。他还有一个故事要讲呢。
他讲故事的时候,可以做许多事。我先要弄清他们打算干什么。
你们想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我回来后告诉我。”
他从窗口跳出去,还是沿着村子的围墙,一直跑到菩提树附近,听得到围在那里的人群的说话声。布尔迪躺在地上,一边咳嗽,一边哼哼,每个人都向他问一些问题。他的头发披散到肩上,手和腿爬树时擦破了皮,他几乎没有力气说话,可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性。他断断续续地说些事情,什么魔鬼呀,魔鬼唱歌呀,魔法呀,正吊起了那些人的胃口,想听个究竟,他却在这个时候喊着要喝水。
“呸!”毛格利说,“喋喋不休——喋喋不休!说,不停地说!人和猴子真是血亲兄弟。现在他要用水洗刷他的嘴了,他还要抽上几口烟,等这些都做完了,他就又要开始讲他的故事了。他们真是非常聪明的家伙——那些人。在他们的耳朵塞满布尔迪的故事以前,是不会有人去看守米苏阿的。唉——我怎么变得像他们一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