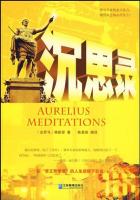第二,人有知有辨有能有主观能动性。荀子指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以可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由,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荀子·解蔽》)。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阐发人的规定性。人所以能够进行有目的的指向性活动,根源于人有知,知就是指人的主观认识能力。荀子认为,人的认识既可以感知事物的现象,也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物之理”),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有所合”)。他还初步看到了人的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并把人的认识活动看成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高度推崇。在苟子看来,基于“知”或认识,人便获得了“辨”的功能。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日,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荀子·非相》)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与动物有所区别,这区别就在于人有“辨”的功能,动物没有这个功能。动物无“辨”,故虽有父子,却不能建立起父子之情;虽有雌雄,却不能区分男女之别。人有“辨”,故动物无以企及的事体,人却能之。苟子又说:“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正名》)
如果说,前述“知”和“辨”指人的认识能力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能”即是指人的实践能力。苟子认为,不仅认识可以达到主客观的统一(“知有所合”),而且实践也可以达到主客观的统一(“能有所合”),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合而言之,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突出地表现为“善假于物”,利用规律改造和控制自然:“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君子……之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荀子·君道》)。所谓“假舆马”、“假舟揖”、“假于物”、“用其材”,说的都是利用物类帮助自己、成就自己的意思。苟子在《荀子·天论》篇还强调指出,要使作为人的形体的精神主宰的“心”保持清明状态(“清其天君”),充分发挥人的诸种感觉器官及思维器官的自然功能(“正其天官”),充分利用自然界各种造化物以养人类(“备其天养”),顺和自然政令(“顺其天政”),涵养自己情性(“养其天情”)。这样,才能使人的身心得到全面的满足(“全其天功”),才能使天地为人所治理(“天地宫”),万物为人所役使(“万物役”)。人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万物中之一物,但他却能制驭天地,支配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人。这是人的伟大、卓越之处。苟子以人有知有辨有能的特性来把人与动物和其他自然事物区分开来,高度弘扬赞颂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也就比较好地回答了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这在两千多年前实在要算是难能可贵的深刻见解。
第三,人能群。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日: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日:分。分何以能行?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他故焉,得之分义也。”(《荀子·王制》)苟子在这里提出“群”、“分”、“义”三个概念。所谓“群”,就是指人类的合作性,它的现实化即是一定的社会组织;所谓“分”,有三层涵义:一指社会结构上农、工、士、商等的职能分工,二指社会地位上君、臣、父、子、兄、弟(贵贱、长幼)
等的等级分位,三指物质财富上的利益分配;所谓“义”,则泛指一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简称为社会伦常秩序。苟子认为,人在自然生理基础方面与其他动物并无本质差别,就体力来说,人甚至竞争不过牛马之类的动物,但人却能制驭它们,使其为人所用,原因就在于人能“群”,能结合在一起组成一定的社会群体,动物则做不到这一点(根据现代生物学,有些动物也有一定的合群特征)。荀子视“能群”为“胜物”、“裁物”,支配自然,改善人类生存和生活环境的客观前提,强调人类相互协作,建立社会组织的必要性,“离居不相待,则穷”;“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那么人又为什么“能群”而动物不能呢?荀子指出,那是因为人有“分”而动物无“分”。
“分”是“群”的基础,是去争去乱去穷的保证,“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人之大利也”(《荀子·富国》)。于是,荀子提出“明分使群”的主张。在他看来,“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国》),人,就各自孤立的个体说,其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有多种技能,从事多种事业,但人的需要却是多方面的。因此,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组织中,明确各自的分职分工分位,共同合作,才能满足各自的多种需求。然则,人又何以能实行“分”呢?苟子认为,那是因为人有“义”。“义”作为社会伦常规范,构成“分”的标准和内在依据,离开“义”,“分”就会失去章法而陷入混乱。从这一层意义上说,礼义法度便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规定和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后根源。
荀子总结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
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解释,苟子这段话触及到物质发展的阶段性问题。
“有气而无生”,是指无机物;“有生而无知”,是指一般的有机物,有生而有知,是有机物发展的较高阶段;有知又有义,是有机物发展的最高阶段。高级形式包括低级形式,“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的这段话可能有这样的不自觉的涵义,但是他所注重说明的,是人与自然物之间的本质的区别。”苟子认识到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人有知有辨、有义有分、能群,故而人的价值高出于其他任何自然物之上,最为天下贵。不难看出,虽然在天人关系问题上,苟子和孔孟各异其取,但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肯定人的价值,从人与物的区别的角度揭示人贵物贱这一点上说,荀子却表现出与孔孟的严格的一致性。
五、“制天命而用之“和“敬其在已”
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和“人为天下贵”的观念出发,苟子摒弃消极无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信仰,提倡“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积极进取精神。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这一段慷慨激昂、催人向上的文字,说的是,与其崇尚天的伟大而思慕它,莫如视天为物来畜养并控制它;与其顺从天而颂扬它,莫如认识、掌握它的规律而利用它;与其空望天时而坐享其成,莫如顺应天时以求得生产丰收;与其听凭事物自然增多,莫如发挥人的实践功能以促进事物的变化发展,与其空望役使万物,莫如好好治理万物以勉其遭受损失;与其指望万物自生自长,莫如有意识地改造万物并帮助它成长壮大。因此,放弃人为的努力而等待天的思想,就会丧失万物的本性,从而也就不能获得万物的真情。苟子在这里淋漓尽致地阐发了他的相信人类自身的力量,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去利用、改造、征服和控制自然,使自然服务于人的利益和满足人的需要的思想。这与道家老庄崇自然、尚无为、弃有为的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
苟子进一步认为,人类是否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按照客观规律以尽人事人为,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他指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荀子·天论》)苟子比较分析了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两种人生观念以及为这两种人生观念所指导而导致的不同结果,他将前者概括为“敬其在己”,将后者概括为“慕其在天”。所谓“敬其在已”,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眼于人,相信人类自身的力量,突出人的主导地位;所谓“慕其在天”,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着眼于自然,看不见人的独立价值和能动作用,因而昕天由命,任凭天命和自然必然性的摆布。荀子进而以是“敬其在己者”抑或“慕其在天者”来区分“君子”和“小人”,指出以前者为人生信仰则“日进”,以后者为人生信仰则“日退”:“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悬)者,在此耳”(《荀子·天论》)。苟子这种“敬其在己”的主张较之老庄“蔽于天而不知人”,显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较之孔子“知天命”、“畏天命”的观念,也显然要积极得多。追溯其社会历史根源,则苟子“敬其在己”、“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正是他所代表的阶层在上升时期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自信的表现。
六、余论
从天的规定性的阐发到“明于天人之分”命题的提出,从人的规定性的阐发到“制天命而用之”和“敬其在己”观念的提出,展现出苟子天人观的基本内容和逻辑进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苟子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论证“明于天人之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必须把人和自然界严格地区分开来,肯定和突出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并且这种肯定和突出的程度超过了先前任何一位思想家。虽然,“天人之分”含藏有抹煞、轻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近似性的倾向,但要求区分人与自然的不同职分,进而认同人的特殊地位,这无疑是先秦天人观进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有着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后儒占主导地位的“天人合一”说尽管在总体上与苟子为代表的“天人相分”说是不相容的,但事实上也一定程度上吸纳了“天人相分”说的某些合理成分和因素,从而使自身的内容趋于完善和丰富。这是应当特别指出的。另一方面,苟子从人与动物的差别的角度,揭示人具有高出于动物的特殊价值。这种对人的卓越价值的肯定固然不无理论意义和历史意义,但在荀子这里,这种肯定毕竟还只停留在抽象的层面上。严格地说,苟子仅仅是把人作为类来加以肯定和推崇,换句话说,他所肯定的仅仅是人的群体地位和群体价值(类价值),至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地位和价值,苟子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重视。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苟子天人观逊色于孔孟天人观的地方,因为在孔孟那里,不仅人的群体性和群体价值,而且人的个体性(自主性)和个体价值(独立价值),都受到共同的尊重和高扬。不过,仅就人与动物之差异性的揭示这一点而言,苟子较之孔孟,还是前进了一步。
(原载《管子学刊》1992年第2期、《孔孟月刊》(台)第3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