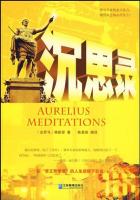《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矣。”《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正。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为知本,此为知之至也。”很明显,这是对孔孟荀为政之本在修身思想的综合和细化。这种通过个人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功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的思想,也称“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内圣”,是说个体要在道德修习上以圣人为标准,努力向着达到圣化之境用功。
所谓“外王”,就是说将成就的圣德推而广之,及于他人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王道政治。“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没有“修身成圣”的功夫,就不可能开出王道政治;“内圣”以“外王”为目的和归宿,不能成就王道政治,就说明修身还没达到“圣”的境界。“内圣”与“外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尽管儒家在为政之本在修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修身上却各有不同。
(二)克己复礼
孔子认为当政者修身的最终目标是成“仁”。他认为,个体的修身成仁,完全是靠自觉,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只要有此道德修为的自觉,努力去实行,完全是可以达到“仁”这种高尚的道德境界,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那么,修身成仁的具体进路是什么呢?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矣。”(《论语·颜渊》)
孔子这里的礼是指“周礼”,是西周社会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普遍通行的伦理规范。孔子对周礼是极其推崇的。他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礼代表着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即“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国语·晋语四》)。由于人的私欲的存在和膨胀,导致了对礼的破坏,使其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失效,社会由此陷入混乱之中。“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们克制自身的私欲,使其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孔子要求人们把礼贯彻到人之言行的全过程,一言一行都要“约之以礼”(《论语·颜渊》),努力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由于礼的本质是明分别异,即为社会建立以贵贱、君臣、父子等等级从属关系为核心的秩序,并为处于不同等级的人规定了不同的行为规范。所以所谓的“约之以礼”就是要求“贵贱不衍”,即人们的言行必须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相符合,恪守自身社会角色的本分,即“君君,臣臣,夫夫,子子”(《论语·颜渊》)。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弟子曾子也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都是要人们严格遵守礼所规定的名分。对于违礼的僭越行为,孔子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季氏八佾舞与庭,孔子十分气愤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
在礼的各种规定中,孔子最重孝悌。在孔子看来,人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其中家庭内部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父子兄弟关系是最基本的。人若能以孝悌事其亲,就能实现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家庭又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实现了每个家庭的和谐,社会自然就会和谐,同时,在周代的宗法社会中,家国是同构的,社会的政治结构便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社会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君臣上下关系可以看作兄弟父子关系的延续,处理好父子兄弟关系,就能处理好君臣上下关系。所以孔子把孝悌称为“仁之本”,他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矣。”(《论语·学而》)
为政者修身务本,依孝悌而行,就会感化民众以孝悌事其亲,能以孝悌事其亲,就能以忠事其君,依孝悌而行,也就是为政,即所谓“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当然,孔子的“克己复礼”并不仅仅要求用礼从外部规范人的行为,而是把礼对人的外在行为规范内化为自身的道德意识。他认为,当时所以礼崩乐坏,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缺乏遵守礼的规定的自觉要求。
为此他强调把礼的执行建立在个体内心自愿的基础上,把礼对人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使人从内心接受礼的精神,在无意识中自然而然地遵循礼的要求,符合礼的规范。
君子通过修身,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这还不是修身的最终目的,还不能算成“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时还有承担对他人的义务和责任,帮助他人同样树立内在的道德意识。只有每个人都能做到“克己复礼”,行为符合礼的规范要求,才可以说是真正地成就了“仁”德,也达到了重整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
(三)率性之谓道
如果说孔子的修身之道既重内在的自觉,又重外在的规范,那么孟子则只重内在的自觉。孟子主张人性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告子上》)而“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也就是说,人心固有能发展出仁义礼智的潜质,孟子称其为“善端”,故君子修身不必外求,只须反身求诸于己。具体来说,就是“养心”和“尽心”。所谓养心,就是养其本心之善,使其不受外界邪恶的侵害。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孟子·告子上》)就是说,耳目等感觉器官没有思维能力,易受外界物欲的干扰,如果放任其发展,就会对人心固有之善端形成损害。而心是有维护能力的,能够识别和保养人心的善性,使其不受外界的伤害。“立乎大者”,就是发挥心之思维功能进行反省,识别并保养本心之善。孟子认为,养心最重要者是要寡欲,他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物欲是对人性善造成损害的主要因素,寡欲,才能保住本心之善。所谓尽心,就是扩充人心固有之善端,发展出仁义礼智之德。在孟子看来,人心固有能发展出仁义礼智的潜质,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自然地具有仁义礼智之德,能否真正使潜质成为现实,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觉,即“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现实中有“尧之徒”,也有“跖之徒”,有为善者,也有为不善者,并不是他们在本质上有差别,而是能不能自觉追求的结果。前者是因为能够反省和自我追求,使本身所固有的善端发展出了仁义礼智四德;后者则不能够反省和自我追求,辜负了本心之善端,没有发展出仁义礼智四德。君子修身,就是自觉地去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发展出仁义礼智之德。有了仁义礼智四德,就能转化出道德政治。因为“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事亲又被称为“孝”。“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离娄上》)。从兄又被称为“弟”。“孝弟”又是政治之本,“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中庸》《大学》的修身之道和孟子基本相同,也是向内做功夫,并由内向外开出王道政治。《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既然是顺性的表现,那么反过来说,“性”本质上应是善的。修身也就是率性而行。如何才能率性?要之在一个“诚”。
《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大学》在讲修身时,其中心也是讲正心诚意。“诚”主要是指主观意志和信念。“诚”虽是主观意志内求的修养,但这种诚不只限于个人,求诚足为了改造社会。“诚者非自成己而已矣,所以成物也。”
(四)师法之化
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所以他的修身之道也与孟子截然不同,强调外在的师法之化。苟子首先提出一个“性伪之分”的问题,他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并进而认为“人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而仁义礼智等善德,是后天人为的。如果任由人性自由发展,必将引发争夺,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若能化性起伪,通过后天的修为发展出仁义礼智等善的品德,则天下就可归于治。为此他解释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可见,苟子的修身进路是外求,是化性起伪,这与孟子的内求,尽心养心进路正好相反。
既然苟子认为人性本恶,那么化性起伪又怎么可能呢!苟子对此解释说:“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在知性和能力人人都是平等的,禹能仁义法正而成圣,就说明仁义法正是可知可为的。那么行于道路之上的普通人同样通过努力可以仁义法正,可以像禹那样成为圣人。如此,能否仁义法正,就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努力,并不存在能力够不够的问题。具体如何化性起伪,苟子提出了以下几点:
1.节欲
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荀子·正名》)欲是性的自然外现,化性起伪,必须节欲。他说:“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节可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求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人性是天生的,所必欲不可尽去,但是通过节制,可以使之近于尽。修身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尽量地减少欲,使之近于尽。
2.导欲
苟子说:“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所受乎心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必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
(《荀子·正名》)欲是人性所固有的,是受之于天的,但对欲的追求,却是人的主观行为。社会的治乱,并不取决于欲的多寡,而足决定于对欲的追求是否合乎礼义。如果对欲的追求合乎礼义,就是欲再多,也无伤于治;如果对欲的追求不合乎礼义,就是节欲近于尽,也无补于治。
导欲就是使自身对欲的追求能符合礼义的要求。
3.师法之化
苟子提出性伪之分,认为礼义不是人性所固有,而是经过师法之化才能得到。他说:“人无师法,则隆性也;有师法,则隆积也。”(《荀子·效儒》)没有师法.就只能任性而为,趋于恶;有师法,通过学,就能走向善。荀子特别重视学在化性起伪中的作用,他说:“君子日: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鞣以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鞣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
(《荀子·劝学》)人通过师法之化,通过学,就能使恶的性向善的方向发展,这就好像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一样,所以苟子说:“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君和师可化人之性,使之从善,也就是为政之本。
4.积善成圣
苟子说:“今使涂之人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悬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荀子·性恶》)通过学习可以向善,不断地积小善,最后就能成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