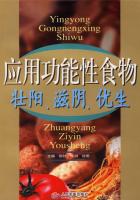勤锻炼也拾棋坛趣
气功可以不练,太极拳可以不打,但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不能一项也不搞。这是我目前身体状况所不允许的。我不能指望愚蠢会帮我排忧解难。
当然,可能像太极拳、气功一样,其他的体育运动项目在治疗癌症中不能起主要的作用,不能当主力军,却可以起辅助的作用,扮演“虾兵蟹将”的角色还是绰绰有余的。医书介绍说,美国的科学家们经研究得知:适当的体育活动和锻炼常常能减轻某些特殊种类癌的危险因子,使人避免发生癌症。只是体育运动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科学家们目前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我就想,既然体育运动有防癌的作用,也就有治癌的作用。当然了,体育运动的防癌治癌的作用不是绝对的。我住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一个病房时,与我同房而居的一位30岁左右的小伙子也是癌症患者,得的是肠癌。他是某军区排球队队员,又高又壮又威武英俊。就他那样,叫人感到,拿大铁锤猛夯他三下也夯不倒。为他的事直到现在我还纳着闷:癌细胞怎么居然也敢欺负他。不久前,一位在某家电视台的电视屏幕上教人做健康操的马女士,居然也被癌症夺走了生命。医学专家们指出:搞体育运动可以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心理状态大为改善,不为孤独、寂寞、郁虑、失望、厌世等消极情绪所困扰,乐观、豁达、自信、坚强,对意外事件如重病、丧偶、离异、亲朋好友生离死别的承受力明显提高,等等。
体育运动(当然也包括气功和太极拳)的上述诸多优良功能和作用是我目前所迫切需要的。我的癌症病尚在治疗中,随时有复发、转移的可能。我开刀后元气大伤。虽经调整,我已迅速地从颓丧、恐怖、绝望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有了往日固有的乐观情怀。但还不能说情绪上的反复现象一次也未发生过。我已进入身体多事之年,各种疾患趁虚而入,十分嚣张,搅得我烦恼不堪,人前人后,呻吟不已。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就有极大可能使我驱散阴影,走出困扰,摆脱危险,全部、至少是大部地找回病前的拥有,大大提高生活、生命的质量。
知新而需温故。如果不是生性好动,积极参加篮球、排球、乒乓球、象棋等体育运动,光靠母亲的先天的和后天的赐予,我就不可能有一个十分强壮的身体,也就不可能顶得住这一次的凶猛的、强大的癌症冲击波。这一次的不幸,有极大的可能是不幸中的一次,而不是最后的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不幸还会有。“老本”已耗费可观,无论往近处看还是往远处看,我都需要抓紧“补差”,抓紧积累,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
搞什么样的运动项目好呢?左思右想,仔细推敲,最好的莫过于再执球拍,驰骋乒坛。做这样的决定,除了由于我的爱好,也还属于在未来丈母娘面前举千斤顶——显臭劲,是要告诉癌症:我顾德如就是不吃你那一套,虽在病中,却要像病前那样生活,那时怎样干的,现在就开始像那时一样地干,我俩过过招,看看究竟是你癌症狠还是我顾德如狠。
有一天工间休息时,我抖擞精神,挥拍上阵,也就三个回合两个照面吧,我感到头晕,双脚发飘,情况十分不妙,但我仍坚持。在救一个险球时,由于心到脚未到,致使我的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水泥地上。同志们赶忙将我扶了起来,但我因右腿疼感强烈站立不住,只好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等到疼痛稍微缓解时,我一步一颠地走回家。我脱掉长裤一看,右腿有两个地方呈现青紫色。
这一跤虽然摔疼了腿,却摔醒了我的头脑:不要说现在处于病中打乒乓球打不得,往后,受年龄和其他一些条件的限制,再挥拍上阵怕也难度不小。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就来点小运动量的吧。可是,我因己制宜地发明创造了也可能永不会为世人所认可的并得以推广的一项体育运动项目——“综合运动法”,以此法坚持进行着体育锻炼。
我把我进行体育锻炼的方法起个名叫“综合运动法”,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不拘一格,不追求运动形式和动作的规范化,而是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愿意怎么干就怎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尽管即兴式的,临时动议性的,近似于胡来一气。
我刚手舞足蹈、摇头摆尾了一遍,若有人要我再“克隆”一个出来,我就“克隆”不来了。我对人说,我的每一次的运动形式和动作像是广东省佛山市石湾窑厂制作的“爆花瓶”,都是绝无仅有的。我想跑步,就去跑步;我想做操,就去做操;我想做气功,就去做气功;我想身体的某个部位需要活动一下,就临时想出一个动作去活动它一下;气从肚子里朝上涌了,好情绪从心中朝外冒了,我就扩我的胸,舒我的臂,粗粗地重重地痛痛快快地嘘我的气,尽情地尽兴地“啊啊”的吼叫几声,旁若无人,痛快淋漓。
我也不追求运动的量大小和时间的长短。能够、愿意进行下去就继续进行下去。反之,则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自己给自己叫停。也不搞大运动量。因此,不愉快和劳累感从不曾有过。
我这样做与我把体育锻炼和癌的关系想通了不无关系。
癌症是异常难攻的堡垒,体育运动在抗癌中所排座次也就那么点儿高,对它期望值太高,搞急功近利纯粹是瞎掰,胡折腾,不能不搞,搞到差不多的程度就行,这一炉香烧到了就行。我发现有些癌症病人和我的想法不一样,他们把体育运动当做法宝一样高祭了起来,对体育运动的认真劲、执着劲别提有多大了。有的居然半夜就起床做气功、锻炼。有的不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来,不注意掌握运动的量和时间,练过了头,不但没有把身体练好,反而把命练掉了。
真不是王婆卖瓜,我按我的法儿练,每次都使我获得了畅快和享受,产生了新的欲望和渴求,想继续进行下去,今天进行了,明天再进行;这次进行了,下次再进行。在以后的写书中,我曾多次因为赶稿子一连数日下不得楼去,当闺阁男士,可我还是用我的“综合运动法”来强健我的身体。这次写《我是怎样战胜癌症的》,更是赶任务赶得厉害,也从未冷清了我的“综合运动法”。对一种无竞技性的、刺激性的纯锻炼身体的体育运动如此的钟情,在我来说,算是一大奇迹,足以说明了“综合运动法”有着极强的诱惑力,无比的优越性。
别看“综合运动法”是一虾兵蟹将,我在抗癌中却得了它的很大的实惠。按“综合运动法”运动后,我的饭量增加了,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腿走路有力了,我浑身觉得有劲了。我的感觉一时比一时好,一日比一日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向好的方向发展,从未出现过异常和反常现象。
我虽和“综合运动法”情深意笃,但我们之间的“结合”到底有“强迫婚姻”的味道,要不是癌症逼的,我恐怕是不会对“综合运动法”瞅一眼的。所以,在手术1年多以后,随着我的身体状况的日渐好转,我就萌生了喜新不厌旧之意——我想在进行“综合运动”的同时也下象棋。我的棋艺是说得过去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拿不定主意。对于一个癌症病人来说,病后的5年是个关键时期,能够活过5年,希望就大大的有了,甚至可以说是痊愈了。有句话叫“5年看3年,3年看头年。”我术后才1年刚出头,正处于有较大危险的生命攸关期。
此时此刻,我必须围绕着战胜癌症这个主题做文章,有利于治癌症的就干,反之则不干或少干。体育运动是治癌时可以调动的一个积极因素,下棋属于一种体育运动,可我对它有想法,有看法。人不是有“阴阳人”吗,我觉得象棋是一种“阴阳运动项目”,它自然是体育运动项目,在我看来也可列入文娱活动项目中,下象棋时只劳驾上肢,才有多大的运动量呀。不难想像,在所有体育运动项目中,它的抗癌作用肯定是最小的当中之一。我还是不搞这种体育性不强的项目吧。我又翻过来想了,象棋既属体育运动项目,就能强体。这是它的“阳”面。它的“阴”面是娱乐性,可以使我忘情,可以使我悦心。与癌拼杀,它既能给我物质的支持,又能给我精神的援助,我该下象棋,于是也就下起象棋来了。
我不能不做“战前准备”。我考虑,我这个人脾气怪,很看重胜负,输了棋就生闷气,而这是我眼前的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我进行了“自我封闭式训练”,在家自己跟自己下,研究开局、中盘、残局的最佳着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劳,我的棋艺得到迅速的恢复和提高。术后的头两场棋的较量,是同一个曾拿过我的单位象棋比赛冠军的人进行的,结果是我连战皆捷,比分分别为一比零和二比零。
我白天一般要看书或写点什么,下得少,多在晚间下。每天吃过晚饭看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后,我便拿着象棋和小板凳,守候在路灯下,迎接各路豪杰的挑战。下起来后可真热闹,常常是几个人、十几个人,有时多达二十几个人以上。“围攻”我一人,使我陷入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我还是胜的多。即使输了,也有快慰和满足,这么多人团结一致对付我,说明我还是有两下子的,不是好惹的家伙。
我一直坚持下着棋。下棋的时候,我十分地投入。我的眼里、心里、大脑里只有面前的棋,不知周围站着的是亲不亲的人、熟不熟的人,不知棋盘外的世界还存在不存在,自然也不知有什么神在等着我去烦,有什么愁等着我去排。下得起劲时,我高高举起棋子,或重重地砸在水泥地面上,或重重地砸在木头桌面上,发出“砰”的一声响。还有并不以此为满足的时候,便配以幽默的话语,引得对手和围观者哈哈大笑。下棋的时刻,是我最快活、最忘情、最得意的时刻。有位经常观阵的朋友对我说:“看你下棋时那副得意洋洋、有说有笑、不知疲劳的样子,不知情的人绝不会认为你是一位癌症患者。”一位与我在一个干休所同住了两三年、和我下棋下了两三年的一位棋友,在看了北京电视台播放了关于我和我写的《夺命》一书的报道后,对我说:“你原来患有癌症呀!和你下了这么长时间的棋,可是一点也觉不出来,你与健康的人毫无两样。”
我对他笑笑说:“我最爱听你这样的话和类似你这样的话。”
我倒觉得下象棋对我的抗癌所起的作用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多年来,下象棋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潇洒。
我对它很满意,象棋,我怕是要一直下下去了。
慎吃喝把好进口关
病从口入。在抗癌初期,尤其是术后出院的初期,我是严格认真地、小心谨慎地把着进口关的。对我和我的亲友、熟人们认定的、通过吃、喝、抽渠道进入我体内导致我癌症的“坏分子”们,我大开红灯,不让它们入口,再造祸端。即使有时高抬贵手,让某些“坏分子”“过境”,也严格地控制它们的数量,不让他们形成声势,造成气候,破坏我体内的“安定团结”。
我不再吃被认为可能致癌的腌制和酱制的鸡、鹅、鱼、鸭、肉、蔬菜等食物。我不吃油条。我也不吃辣椒等刺激性强的东西。如果吃,也是偶然为之,并且不让其量太大。
我不再饮白酒。在有些场合下,实在回避不开,我只以润湿嘴唇为限度。在病情很稳定和我自认为我的病已治愈之后,我也极少有饮白酒的时候,即便有,量也极少。
我不喝白酒,除了主要出于自觉之外,也有一小部分出于无奈。术后,对我而言,白酒似乎变成了钢针、钢水和特别辣的狗尾巴椒,一入口,从舌头到胃这一区段上,产生了强烈的、无法忍受的刺疼感、灼烫感、麻辣感。我实在无法喝。我自然地想到,酒是直接地、明显地、强烈地刺激与影响着胃的,不信它的“邪”,吊儿郎当,怕不能说明我的文雅。
其实,我也知道,适量地喝些白酒是有益无害的。我就见过不少的高血压、低血压和心脏病人适量地喝着白酒,结果啥事也没有。医书上也这样记载着:“人类饮酒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节假日和亲朋友好相聚,对酒当歌乃是人生一大乐趣。长期的经验及近期医学研究证实,饮酒少了对人有利。”“适量的饮酒可能对松弛身体,消除疲劳,甚至对心脏健康有好处。”不过,我怕万一,一直基本坚持着不喝白酒。我曾对人夸耀:“别看我大大咧咧,对癌症一百二十个不在乎,我认为该注意的地方还是很注意的,比如酒,我体会到它和胃的关系太直接了,太不一般了,我病后就和白酒一刀两断,藕断丝连的时候未出现过。我是桃园三结义里的老三张飞,粗中存细。”
我只喝啤酒、米酒、葡萄酒之类,多在过节、过年与朋友聚会,或是碰到特别开心的事的时候,饮用量也极少。这样的喝法不在禁忌之列,医书说:“经治疗后病灶已消失的病情稳定者,喝少量啤酒、米酒、葡萄酒,以促进食欲,并非绝对不可。”可以说,我已经将自己的酒鬼的帽子抛到月宫中去了。
我一度戒了烟。此举的震动性不亚于从西边又出了个太阳。妻喜形于色,亲友连赞了不起,单位领导也颇高兴,并在高兴之余发给我一个保温杯,以示奖励。
在严防“坏分子”入口的同时,我对那些我和我的亲友、熟人们认为,可以给治癌的食物大开“绿灯”,积极地、热情地引进它们。有人说芦笋可以治癌,我就去离我住处有相当一段距离的一家菜市场将其请回来,做成菜。又有人说,大蒜治癌、防癌功能不算小,我便努力改变自己南方人不爱吃大蒜的习惯,培养感情多吃大蒜。鳖被人们一致认为是一种高效的抗癌食物,妻曾多次劝我不妨买了吃,我也曾跃跃欲试过,后未曾为它破费,但我的心意思是有的,治癌、防癌的意识也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