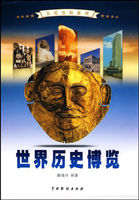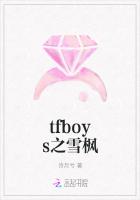当年,江隆基在兰州大学当校长时曾经说过,在兰大文科三系中,称得上有真才实学的,就是赵俪生一个。他还说:“1934年入学的清华学生,出过几支大手笔,赵俪生是一个,王瑶、韦君宜也是……”(见《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8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如今,继《王瑶全集》和韦君宜《思痛录》之后,赵俪生的《篱槿堂自叙》也已问世。读这本书,让我在体味“可怜盛世存儒雅”(殷焕先赠赵俪生诗句)的同时,也不由得想到“盛世”的由来……
对苦难深重的中国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出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长大。按理说这批人有条件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幸福的中国,但由于遇上“九一八”事变以及国共两党交恶,因此他们不但要承担救亡的重任,还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思想环境之中。于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他们的表现和选择便与五四运动有所不同。
赵俪生(1917—2007)
《篱槿堂自叙》
诚如赵俪生所言,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核心基地是北大的话,那么“一二,九”运动的核心基地则是燕京和清华。他还说,“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组织起了很大作用。韦君宜在《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也说,“一二·九”运动期间,蒋告诉她:“红军已经过了黄河,如果打起仗来,苏联的拖拉机可以改装成坦克……”(《世纪清华》第50页)。
除此之外,人们对组织的认识和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有不同。比如三十年代的韦君宜,就是所谓的很有希望的分子。她说:我没有“放弃……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由于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括在组织的信仰里面,所以她认为要爱国就必须把一切献给组织。可见她对组织的认识非常幼稚,参加组织的动机也比较单纯。加入组织以后,她常常遇到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以致产生悔不当初的念头。这时,那种献身精神就要起作用。于是她“一面牢骚满腹”,一面说服自己“继续做‘驯服工具’”(《思痛录》,4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出版)。
与韦君宜相比,赵俪生好像多一点书生气。“一二·九”运动时,赵因为表现积极,也被组织相中,于是蒋南翔跑来对他说:“你人很诚实,在搏斗中表现英勇,这说明你革命的热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热情是多变的,它还需要组织的保证。”经过认真考虑,赵认为自己受不了布尔什维克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所以他表示只愿意做一个马尔托夫式的孟什维克,即“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篱槿堂自叙》,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从后来的经历看,赵俪生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抗日战争前夕,作为外围组织的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曾派他到山西参加牺盟会的训练,他因为正在翻译一部苏联小说,便推迟了半年。到了太原后,早走一步的清华同学已经是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了,于是他只能忝列末座。不久,他离开太原辗转到长沙。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成立,他本来应该回校继续学习,但是在民先的安排下,他又返回山西抗日前线,并因为遭遇日军,撤到延安。他后来取道西安,第三次返回二战区,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四十年代后期,他又是最早被组织接收的学者之一。纵观赵俪生的一生,尽管他始终是围绕着组织在转,并因为向地下组织提供情报,被美国同行讥为特务,可是他本人却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本来,他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后来他才明白不参加组织意味着什么。八十年代初,曾经在游击队当过组织科长的孙雨亭已经是省委书记了,一次酒足饭饱之后,孙对他说:“老赵呀,当年有个事要跟你说清楚。那次晋南干部总结会之后,调整班子,你已经是公认的宣传科长啦,可是到头来还是老朱上你不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现在可以说破了,就是因为老朱是党员,你不是。论工作,无论编报、讲政治课,老朱都远远不如你,可他是党员呀。我讲这些是叫你打破学生不参加党的戒律。你不入党,党不吃亏,你吃亏呀。”(同上,80页)这就是说,倘若老赵当时就参加了组织,不也是省级大员了吗?这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没有参加组织是吃亏,参加组织就不吃亏吗?在这本书中,赵俪生还提到一些大人物,比如姚依林、荣高棠、牛佩琮、牛荫冠、韩钧、赵宗复等。与前二人相比,后几位在文化界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他们是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物,当年我父亲因为与他们共过事,所以“文革”期间前来外调的特别多。父亲忙不过来,让我帮助抄写证明材料,使我对这些名字比较熟悉,也比较注意。与证明材料相比,赵先生写的那些事例自然要生动得多。在这里,我想谈谈牛荫冠。牛出生于山西兴县蔡家崖一个大地主家庭,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比赵俪生高一级。在“一二·九”运动中,他因为表现积极而加入组织。1936年,再过一年就要毕业的牛荫冠受组织委派,率先回到山西,成为牺盟总会的主要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后,他一直在晋绥边区负责财贸工作。他父亲牛友兰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好事,被视为开明绅士。可是到了土改的时候,不知是为了邀功还是追于无奈,作为工作组组长的牛荫冠居然召开“斗牛大会”。他坐在台上,他父亲跪在台下。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结构耐人寻味。全书以政权的更替为界分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篱槿堂自叙》,从第一章《乡土和身世》,写到第九章《华北大学》,相对完整地回忆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是几篇回忆录,断断续续地写了与作者后半生有关的一些人和事。一本十几万言的回忆录在结构上居然不能统一,令人不可思议。我想,以赵俪生之“儒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或难言之苦,是不会这样的。
1997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