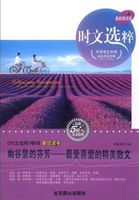亚历山大经过底比斯城
我认为,国王是厉害的,虽然年轻,
当他宣布:“你将与底比斯城等高与土地同在。”
而老元首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骄傲,
他已经看见仿佛置身在那些被传颂的时代里。
用火点燃所有的一切!国王将其他登记注册
塔、城门、寺庙——富饶繁荣……
但却沦陷于思想,然后他带着被照亮的面孔说:
“你仅仅供给了游吟诗人家里的生存。”
1961年
我们出生的地球
世界上没有任何人——
如此简单,高大,无泪——像我们。
1922年
我们不把它带在胸前护身符的小盒里,
并且在诗歌中不为它而哭泣,
它不会将我们从苦涩的休息中唤醒,
并且似乎不会面对我们作出伊甸园的承诺。
在我们心中,我们从未尝试着待它
像一个公民,因为不断地讨价还价,
当它生病了,不快乐,而在它身上有所花费,
我们甚至忘记看望或者了解它。
是的,这脚上的污垢与我们的公正相称,
是的,咬牙切齿的嘎吱声与我们的正义相称,
我们昼夜不停地践踏它——
这纯粹的并且没有施工过的尘土。
但是我们躺进它然后单独变成它,
因此称这个地球如此自由——为我所拥有。
1961年
倾听歌唱
像一阵风,女人的声音正在飞行,
似乎是一个黑人在湿漉漉的夜晚,
那些易于触摸的事物——
全都变成了另外一种。
它如洪水泛滥伴随钻石闪耀,
某个地方某种东西银光闪闪,
并且,穿着一件不可思议的
绸衫,水花飞溅。
仿佛远方并非我们的坟墓
而是一架天堂的梯子横穿而过。
1961年
科玛洛沃素描
啊,哭泣的缪斯……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
……于是我在这里放弃了一切,
大地上所有的祝福。
森林里的障碍物变成
“此处”守护者的幽灵。
我们全都转瞬即逝仿佛生命的过客,
活着——只是出于一种习惯。
似乎面对着我,在那天空之上
有两种声音正在交换意见。
两种?但都反对这东边的墙,
在一树新生的混乱的红草莓中,
有一片黑暗,老树发新枝……
它是——一个预言,出自玛丽娜。
1961年11月19—20日 港口医院
最后的玫瑰
您将从一个角度写下我们。
——约瑟夫·布罗茨基
我不得不与莫洛佐娃一起鞠躬,
与希律王的继女一起跳舞,
与蒂朵的大火所冒出的浓烟一起飞升,
只想返回圣女贞德火刑用的柴堆。
主啊!你看我已经倦于
生死和复活。
拿走一切吧,除了允许我能够再一次
感觉这种深红色玫瑰的新鲜。
1962年8月9日 科玛洛沃
“有她,这硕果累累的秋天……”
有她,这硕果累累的秋天!
某物晚熟他们谴责她的分娩,
原因是为了十五个受祝福的春天,我熔化了
于是无法自己从大地上站立起来。
那时我已经意识到她,姗姗来迟,
硬努力着靠向她然后拥抱她,
但是秋天对我诅咒着,
又在秘密之中传递着她的恩惠。
1962年
“诗人不是一个人……”
诗人不是一个人,他只是一个幽灵——
甚至他是盲的,像荷马,或者像
贝多芬,聋的——
他看见一切,他听见一切,
并且他控制并发挥所有的一切……
1962年
13行
最后,你说出了这一个具体的字,
不像他们这样……单膝跪地自我下陷,
但像他这样打破镣铐,
于是祖国的白桦林神圣的叶子看见
穿过无所等待的眼泪的彩虹。
于是寂静在我们四周开始歌唱,
于是晴朗的太阳启迪所有的黑暗,
于是世界在光明一闪中改变自身,
并且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大地上葡萄酒的标准。
乃至于我不得不操起一把刀
杀死这个寄自天堂高度的字,
在神圣的敬畏中,沉没于神圣的寂静——
让被奉为神圣的生命继续。
1963年
最后
她在我们头顶仿佛一颗明星在海洋上空,
寻找着最后的带电的巨浪,
你给她悲痛和骚动的名字,
于是永不再有——我们神圣梦想的欢乐。
白天,她盘旋在我们头顶——一只燕子;
一朵微笑——她在我们猩红的唇上开花
晚上,她和我们全都陷于窒息、空虚,
和她冰凉的手在一起——在不同的城市的深处。
不为所有单调的赞美所感动,
健忘罪恶的主人,
弓身于失眠的我们床一般的头顶,怀着悲情,
她低吟诗句,绝望并诅咒。
1963年
几乎全都收进了相册
你会听到雷声并记住我,
并且认为:她渴望暴风雨。
天边冷酷无情地红了,
你的心啊,仿佛燃起大火。
那天在莫斯科,一切成真,
因这最后时刻,我选择离开,
并加快向着我渴望的高处攀登,
我正在离去的影子还与你同在。
1961年—1963年
春天前夕的颂词
……你让我欣慰
——杰拉德·德·奈瓦尔
暴风雪平息在松园里,
未饮任何美酒,但却酩酊大醉,
——奥菲莉娅躺在水面上——
整个夜晚洁白的寂静向我们歌唱。
而他,似乎仍未清醒,
于是便与这寂静订婚,
继而,离去,他仁慈地留在这里。
与我在一起,直到我生命的终点。
1963年
“整个莫斯科被诗句淹没……”
整个莫斯科被诗句淹没,
被可怕的歌谣之矛刺穿。
让我们在不同的课程中忍受与它们同在,
让哑巴成为它们和你在一起的
秘密的象征,尽管似乎总是——和我在一起,
你除了在婚姻中团结自己,单身一人,
带着处女的沉默,乃是苦涩,
那人在吃地下的花岗岩,
并使未来的圆完全填满,
然后,到了夜里,严禁大声说话,
通过你的耳朵预告你的灭亡。
1963年
“你,是被诅咒的……”
你,是被诅咒的,你,就像下冰雹,
你的声音狂野而简单。
但是无人能够将你翻译
成人类的语言。
你将步入彻底的遗忘
像人步入神殿。
到了那里,你将总是受祝福的
被我们的双手和心灵。
1963年
“于是我们垂下我们的眼睑……”
于是我们垂下我们的眼睑,
把鲜花投放在床上;
直到最后我们也不知道
怎么称呼彼此。
直到最后我们也不敢于
说出自己心爱的名字,
仿佛目标已经接近,却又放慢了脚步
我们仿佛被施了魔法。
1963年 莫斯科
呼叫
哪一支奏鸣曲,你会
被我隐藏在心里——悉心照料?
多么不安,对我来说,
呼叫你吗,完全不公平
因为如此亲密,如此美好
你对我来说,虽然只是一小会儿……
你的梦——正溶解在一种溶剂中,
在哪儿死去——不过是对静音征税。
1963年
“我现在大步走在无欲之地……”
我现在大步走在无欲之地
在那里只有影子是最佳伴侣。
来自荒凉花园摇曳的一阵风,疏远,
于是在脚下——坟墓的脚步冰冷。
1964年
取自意大利日记
阴差阳错我们相遇在某一年——
不是这一年,不是这一年,不是这一年……
我们都干了什么,主啊,与你同在,
与跟我们交易命运的主同在?
最好我们从未降生在这大地之上,
最好我们都住在天空的城堡之中,
我们飞翔似鸟,我们盛开如花,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你和我。
1964年12月
旅行者日记
——即兴诗句
华丽闪亮——此为最后的审判日,
聚会比分离苦多。
在那里,将我托举向身后名的
是你们在世的手。
1964年12月
圣诞时光(12月24日)
——在罗马的最后一天
总结一个虚构般的假期
通常很难,对于心灵的承受来说,
我放弃了生命中的许多东西
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让我要得更多——
对我来说,科玛洛沃松树
说着一种它们自己的语言,
热爱完全独立的春天时光
它们傲然屹立,各自在天空的酒池中狂饮不醉。
1964年
最后一首
我欣喜若狂,
歌唱坟墓。
我分配不幸
以超人之力。
窗帘没有升起,
阴影旋转的舞蹈——
因此,所有我爱过的人们
已经逃掉。
所有这一切正被披露
在玫瑰花丛深处。
但我不允许忘记
昨日泪水的味道。
1964年
“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尽管并非我之故土,
但将被我永远记住,
大海微微冰封,
无盐的海水。
陆地的底部比粉更白,
天空令人头晕目眩,好似葡萄美酒,
这玫瑰色的松树干
赤身裸体在日落时分,
落日落在苍天的波峰上
令我一时难以理解
这是岁月的尽头,世界的尽头,
还是神秘的神秘在我体内重降。
1964年
离开
虽然这片土地不属于我自己,
但我会记住它的内陆海
和如此冰冷的海水
沙滩洁白
像一把老骨头,松树
不可思议的红,夕阳正落向那里。
我无法说它是不是我们的爱,
或是结束的这一天。
1964年
“今天我仍旧在家……”
今天我仍旧在家,
但是先前的
一切有点奇怪——
每件东西都在秘密叛乱。
继而它们交头接耳,好像要求
此处成为它们该在的领地?——没有我,
仿佛在一宗刑事审判中
一个陷阱在四周,突然跳了出来。
1964年
“远离高悬的吊桥……”
远离高悬的吊桥。
继而在泥泞、潮湿、十二月的黑暗里
你出现了,在你全部的伟大之中:
声名狼藉、罪恶累累、怪物一般。
此刻黯淡的此君明日将如花盛开
仿佛威尼斯——世界建筑的瑰宝——
我哭喊道:“轮到你了,赢得所有的一切,
我对竖琴也对桂冠毫无要求已经太久。”
1965年1月17日
“未向一座秘密的亭子……”
未向一座秘密的亭子
这座正在燃烧的桥没有引领:
恶魔殿下走向一笼子的黄金,
而她面对一个红色的绞刑台。
1965年8月5日
“我承受不起的痛苦……”
我承受不起的痛苦
这已过二十年的玩笑——
我差点儿收到了
一封寄自他的信,
不是在我梦里,而是事实
完全是在现实之中。
1965年
“让这位澳大利亚人坐下……”
让这位澳大利亚人坐下,无形地坐在我们中间,
然后让她讲话令我们眼前为之一亮,
好像她摇摇我们的手并抚平我们的皱纹,
好像她最终原谅了不可饶恕的邪恶。
然后让一切重新开始——我们再次独立自主的时间
然后重获和平甚至宁静。
1965年8月26—27日夜
音乐
怪物似的想生出自己,
欣赏自己并窒息自己,
你没有,唉,只有一条领带
在善良与邪恶、土坑和天堂之间?
对于我意味着:你总在分界线上。
1965年
结尾之处
而在那里,梦想被加工成形
为我们俩——差别不大的梦想
被容纳;
我看见这同一个梦想,它充满力量
仿佛春天正到达。
1965年
“被你赞美是令人恐惧的……”
被你赞美是令人恐惧的……
你历数我全部的罪行
然后将我的诗列为
最后的被告陈词。
1965年
最后的散句
多么健忘的生命,而死亡——记性多好。
——
人人都会拥有思想对我来说那是
64岁时在社会的每一个底层在商店里得到了它。
——
刺耳的声音令人沮丧、崩溃,
把过去和未来连接起来繁殖。
——
我的十四行诗站立起来,
也许是这世上最后的十四行。
——
我不知道什么在引导我
于是向回走,跨过了如此的深渊。
——
而我没有要求,
既不想站在这新时代之上也不想让它将我包围。
——
……以血做诗韵
使血中毒
是世上最血腥的事。
——
在悲伤中,在激情中,在无法忍受的重压之下
在那里死亡站在每一个拐弯处,
并且有许多废墟在四处走动。
——
什么潜伏在镜子里?悲伤。
什么轰鸣着破墙而入?灾难。
1963年—1965年
“最后的需要……”
最后的需要,她本人已经亲自提交,
然后沉思着走到一旁。
196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