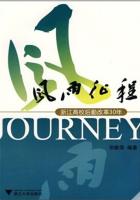一
不论是本性还是命运,都决定了我得劳劳碌碌过一辈子。回家才两个月,就又离开了祖国。一七〇二年六月二十日,我在唐兹登上了“冒险号”商船,起程前往苏拉特,船长是康渥尔郡人约翰·尼古拉斯。我们一帆风顺到了好望角,在那儿上岸取淡水。但我们发现船身有洞孔,就卸下东西就地过冬。船长害疟疾,所以我们一直到三月底才离开好望角。起航后一路顺利直到穿过了马达加斯加海峡。但是当船行驶到那个岛的北面大约南纬五度的地方时,风势突变。据观测,那一带海上,从十二月初到次年的五月初这段时间里,西北之间总是吹着不变的恒风。可是四月十九日那天,风势比平常要猛烈得多,也比平常更偏西一点,这样一连刮了二十天,我们就被刮到了摩鹿加群岛的东面。根据船长五月二日的观测,我们所在的地方大约是北纬三度。这时风停了,海上风平浪静,我真是非常高兴。可是船长在这一带海域有着十分丰富的航海经验,他要我们做好迎接风暴的准备。果然,第二天风暴就来了,开始刮起了南风,那就是所谓的南季节风。
我们看到风有可能要把东西吹落,就收起了斜杠帆,同时站在一边准备收前桅帆。可是发现天气非常恶劣,我们就查看了一下船上的炮是否都已拴牢,接着将后帆也收了。船偏离航道太远了,所以我们想与其这样让它吃力地慢慢行驶或者下帆随波逐流,还不如让它在海面上扬帆猛进。我们卷起前桅帆把它定住,随后将前桅帆下端索拉向船尾。船舵吃风很紧,船尾猛地转向风的一面。我们把前桅帆索拴在套索桩上,可是帆碎裂了,我们就把帆桁收下来,将帆收进船内,解掉了上面所有的东西。这是一场十分凶猛的风暴,大海一下子变得非常惊险。我们紧拉舵柄上的绳索以改变航向,避开风浪,接着帮助舵工一起掌舵。我们不想把中桅降下来,而是让它照旧直立着,因为船在海上行得很好。我们也知道,中桅这么直立在那里,船也更安全一些,既然在海上有操纵的余地,船就可以更顺利地向前行驶。风暴过后,我们扯起了前帆和主帆,并把船停了下来,接着我们又挂起后帆、中桅主帆、中桅前帆。我们的航向是东北偏东,风向西南。我们把右舷的上下角索收到船边,解开迎风一面的转帆索和空中供应线,背风一面的转帆索则通过上风滚筒朝前拉紧、套牢,再把后帆上下角索拉过来迎着风,这样使船尽可能沿着航道满帆前进。
这场风暴过后,又刮了强劲的西南偏西风,据我估算,我们已被吹到了东面大约五百里格的地方,就是船上最年长的水手这时也说不清我们是在世界的哪个部分了。我们的给养还足以维持,船很坚固,全体船员身体也都很好,但是我们却严重缺淡水。我们觉得最好还是坚持走原来的航道,而不要转向北边去,那样的话我们很可能进入大鞑靼的西北部,驶入冰冻的海洋。
一七〇三年六月十六日,中桅上的一个水手发现了陆地。十七日,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有一座大岛或者是一片大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大陆),岛的南边有一片狭长地伸入海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港湾,但港内水太浅,一百吨以上的船无法停泊。我们在离这港湾一里格内的地方抛锚停船,船长派出十二名武装水手带着各种容器坐长舢板出去寻找淡水。我请求船长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到那地方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上岸后,我们既没发现河流、泉水,也没有看到任何人烟的迹象。我们的人因此就在海岸边来回寻找,看看海边上是否有淡水。我则独自一人到另一边走了大约一英里,发现这地方全是岩石,一片荒凉。我开始感到无趣,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引起我的好奇心,就慢慢朝港湾处走回去。大海一览无余,我看到我们的那些水手已经上了舢板正拼着命朝大船划去。我正要向他们呼喊(尽管这也没有什么用),却忽然看到有个巨人在海水中飞快地追赶他们,他迈着大步,海水还不到他的膝盖。但我们的水手比他占先了半里格路,那一带的海水里又到处是锋利的礁石,所以那怪物追不上小船。这都是后来我听人说的,因为当时我哪还敢待在那里等着看这个惊险的场面会落得个什么结果?我循着原先走过的路拼命地跑,接着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小山,从那里我大致看清了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我发现这是一片耕地,但首先让我吃惊的是那草的高度,在那片似乎是种着秣草的地上,草的高度在二十英尺以上。我走上了一条大道(我想这是一条大道,其实对当地人来说,那只是一片大麦地里的一条小径)。
我在这路上走了一些时候,两边什么也看不到。快到收割的时候了,麦子长得至少有四十英尺高。我走了一个小时才走到这一片田的尽头。田的四周有一道篱笆围着,高至少有一百二十英尺。树木就更高大了,我简直无法估算出它们的高度。从这块田到另一块田之间有一段台阶,台阶有四级,爬到最高一级之后还要跨过一块石头。我是无法爬上这台阶的,因为每一级都有六英尺高,而最上面的那块石头高度在二十英尺以上。我正竭力在篱笆间寻找一个缺口,忽然发现一个当地人正从隔壁的田里朝台阶走来,这人和我看到的在海水中追赶我们小船的那个巨人一样高大。他有普通教堂的尖塔那么高,我估计他一步就是十来码。我惊恐不已,就跑到麦田中间躲了起来。我看到他站在台阶的顶端正回头看他右边的那块田,又听到他叫喊,声音比喇叭筒还要响好多倍,但由于那声音是从很高的空中发出的,我起初还以为一定是打雷了呢。他这一喊,就有七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怪物手拿着镰刀向他走来,那镰刀每把大约是我们的长柄镰的六倍。这些人穿的不如第一个人好,像是他的用人或者雇工,因为听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来到了我所趴着的这块田里来收割麦子了。我尽可能远远地躲着他们,但是因为麦秆与麦秆间的距离有时还不到一英尺,我移动起来就极其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设法往前移,一直到了麦子被风雨吹倒的一块地方。在这里我就再也无法向前移动一步了,因为麦秆全都缠结在一起,我没办法从中间爬过去,而落在地上的麦芒又硬又尖,戳穿了我的衣服,直刺到肉里去。与此同时,我听到割麦子的人在我后面距离已经不到一百码了。我精疲力竭,悲伤绝望透顶,就躺倒在两道田垄间,一心想着就在这里死掉算了。想到我妻子要成为孤苦无依的寡妇,孩子要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我悲伤不已。我又悔恨自己愚蠢、任性,全不听亲友的忠告,一心就想着要进行这第二次航行。我心里激动不安,不由得倒又想起利立浦特来。那里的居民全都把我看作是世界上最大的庞然大物,在那里我可以用一只手牵走一支皇家舰队,创造的其他一些业绩,也将永远载入那个帝国的史册。虽说这一切后人难以相信,但有千百万人可以做证。可我在这个巨人民族中间可能就微不足道,就像一个利立浦特人在我们中间微不足道一样,想到这一点,我真感到是奇耻大辱。但是我想这还不是我最大的不幸,因为据说人类的野蛮和残暴与他们的身材是成比例的,身材越高大,就越野蛮、越残暴。那么,要是这帮巨大的野人中有一个碰巧第一个将我捉到,我除了成为他口中的一小块食物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毫无疑问,哲学家们的话还是对的,他们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只有比较才能有大小之分。命运也许就喜欢这样捉弄人,让利立浦特人也找到一个民族,那里的人比他们还要小,就像他们比我们小一样。谁又能知道,就是这么高大的一族巨人,会不会同样被世界上某个遥远地方的更高大的人比下去呢?不过那样的巨人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罢了。
我那时心里又怕又乱,禁不住这样乱想下去。这时有一个割麦人离我趴着的田垄已经不到十码远了,我怕他再走一步,就会把我踩扁,或者我被他的镰刀割成两段。因此,就在他又要向前移动的时候,我吓得拼命尖叫起来。一听到这叫喊声,巨人忽地停住了脚步,他朝下面向四周看了半天,终于发现了躺在地上的我。他迟疑了一会儿,那小心的样子就仿佛一个人努力想去捉住一只危险的小动物而又生怕被它抓伤或咬伤一样,我自己在英国时,捉一只黄鼠狼也就是这样的。最后,他大胆地从我的身后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我的腰将我提到了离他眼睛不到三码的地方,他这样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楚我的形体。我猜到了他的意思,幸亏当时我还冷静,他把我举在空中,离地六十英尺,又怕我从他的指缝中间滑落,所以狠命地捏住我的腰部,但我却下定决心绝不挣扎一下。我所敢做的一切,只是抬眼望着太阳,双手合拢做出一副哀求的可怜相,又低声下气、哀哀切切地说了几句适合我当时处境的话,因为我时刻担心他会把我砸到地上,就像我们通常对待我们不想让它活命的任何可恶的小动物一样。可是我也真是福星高照,他似乎很喜欢我的声音和姿态,开始把我当作一件稀罕的宝贝。听到我发音清晰地说话,虽然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他还是感到非常好奇,这同时我却忍不住呻吟流泪起来。我把头扭向腰部两侧,尽可能让他明白,他的拇指和食指捏得我好疼啊。他好像弄懂了我的意思,因为他随手就提起了上衣的下摆,把我轻轻地放了进去,然后兜着我立即跑去见他的主人。他的主人是个殷实的富农,也就是我在田里首先看到的那一个。
那富农听完他的用人报告我的情况后(我从他们的谈话猜想是这样),就拾起一根手杖左右粗细的小麦秆儿,挑起我上衣的下摆,他似乎觉得我也许生下来就有这么一种外壳。他把我的头发吹向两边好把我的脸看得更清楚。他把雇工们叫到他身边,问他们有没有在田里看到与我相近似的小动物,这是我后来才弄明白的。接着他把我轻轻地平放在地上,不过我马上就爬了起来,来来回回慢慢地踱步,让这些人明白我并不想逃走。他们全都围着我坐了下来,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的举动。我脱下帽子,向那个农民深深地鞠了一躬。我又双膝跪地,举起双手,抬起双眼,尽可能大声地说了几句话。我从口袋里掏出一袋金币,十分谦恭地呈献给他。他用手掌接过去,拿到眼前看看到底是什么,后来又从他衣袖上取下一根别针,用针尖拨弄了半天,还是弄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我就示意他把手放在地上,我再拿过钱袋,打开来,将金币尽数倒入他的手心。除了二三十枚小金币以外,还有六枚西班牙大金币,每一枚值四个皮斯它。我见他把小指尖在舌头上润了润,捡起一块大金币,接着又捡起一块,可是他看来完全不明白这是些什么。他对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把金币收进钱包,再把钱包放进衣袋。我向他献了几次,他都不肯收,我就想最好还是先收起来吧。
至此,那农民已经相信我一定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了。他一再和我说话,可是声音大得像水磨声一样刺耳,清楚倒够清楚的。我尽量提高嗓门儿用几种不同的语言回答他,他也老是把耳朵凑近到离我不足两码的地方来听,可全都没有用,因为我们彼此完全听不懂对方的话。他接下来让用人们回去干活,自己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手帕,摊在左手上叠成双层,再手心朝上平放在地上,做手势让我跨上去。他的手还不到一英尺厚,所以我很容易就跨了上去。我想我只有顺从的份儿,又怕跌下来,就伸直了身子在手帕上躺下。他用手帕四周余下的部分把我兜起来只露出个头,这样就更安全了,他就这样将我提回了家。一到家他就喊来他的妻子,把我拿给她看。可她吓得尖叫起来,回头就跑,仿佛英国的女人见了癞蛤蟆或蜘蛛一般。可是过了一会儿,她见我行为安详,并且她丈夫示意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十分听话,也就很快放心了,还渐渐地越来越喜欢起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