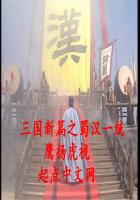在鸦片战争之前,不少西方人已经在反思鸦片贸易。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鸦片贸易就像是金庸笔下的“七伤拳”,在伤害敌人的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1840年11月9日,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悉尼商报》刊登了一篇以《鸦片贸易》为题写的文章。作者是英国的茶商威廉·弗莱。这篇文章是他在议院中发言的节选。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将给出一些证据……如果文中观点被认为是正确的,我强烈呼吁立法机关干预。”他给出的证据如下:
其一,将鸦片卖到中国在过去和现在都直接违反了那个帝国的法律,并公开蔑视清朝政府;
其二,英属印度政府在我们的东印度属地垄断鸦片生产,为中国市场种植、预备并且销售鸦片,丝毫不尊重那里的法律;
其三,在日益邪恶和残忍的背景下,在不列颠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不列颠的国民坚持将鸦片运入中国出售;
其四,作为刺激物或奢侈品,鸦片会对身心造成最大程度的伤害;
其五,在我们的东印度领土属地上,鸦片的种植和垄断伴随有严重的罪恶和压迫;
其六,这种交易在过去和现在都在损害这个国家的合法商业,威胁到我们收入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支。
最后,并且也是最重要的,它对基督教在东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干扰。
简言之,弗莱从法律、道德、经济和宗教层面分析了鸦片贸易的不正当性,以及它对欧洲利益带来的损害。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对鸦片贸易利弊的讨论仍在继续。
1843年5月30日,《悉尼先驱晨报》转载了一篇原刊于伦敦《泰晤士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基于前文提到的英国首相皮尔在1842年7月收到的那份调查报告而撰写的。确切地说,这份调查报告是一份联名文件,署名者是英国最主要的工商业城市比如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普雷斯顿、布拉德福等地的名门望族的家长们,包括利物浦的约翰·格拉德斯通(John Gladston)、利兹的杰姆士·布朗(James Brown),以及曼彻斯特的威廉·格兰特(William Grant)等。
无论是从报告本身的内容,还是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英国工商界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鸦片贸易损害了正当贸易的利益。
根据这份报告,从1803年到1808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出口额,仅毛织品一项,每年平均达到1128557英镑。虽然在1808年至1839年间,大不列颠在工艺、财富、企业等诸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并且从1834年开始用自由贸易体制取代了垄断,然而,在1839年,英国各项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对中国的出口额只有851966英镑,回到了1800年的水平。在1834年至1839年期间,年均出口额不到100万英镑。而在同样的年度区间,鸦片贸易却在大幅增长,从1816年的3000箱左右增长到1839年的3万箱以上,增幅超过10倍。文章作者评论道:
的确,这就相当于瘦黄牛吞了肥黄牛,发了霉的玉米腐蚀掉了好玉米。它就像是贸易肌体上的脓包或者浮肿,而且它的胃口贪得无厌,吃得越来越多,但是,相对于通过系统循环摄取的有益养分的数量,它对肌体的损耗越来越大。
伦敦《泰晤士报》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中英南京条约》已经签署,中国在条约中承诺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对英国工商界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商机,因此,文章作者呼吁英国政府:“我们现在正处于与中国进行更广泛交流的前夜,希望在印度的不列颠政府停止卷入鸦片贸易。”
但是,因为《南京条约》并未禁止鸦片贸易,因为有“领事裁判权”的庇护,在鸦片战争之后,这种不道德的交易比战前更为恐怖。
1853年1月出版的《美国药学杂志》写道:“鸦片战争的结果之一是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人。这个岛落入胜利者手中之后,岛上的鸦片贸易就合法化了,很快就有20家商店得到售卖鸦片的牌照。这些商店处于中华帝国的射程之内,在那里,这样的挑衅要被判处死刑。因此,这场战争并没有终止或约束鸦片贸易制度,相反,英国人的贪婪,导致为这种营生提供了比以往更大的便利。”
1857年2月出版的《北英评论》杂志引述在厦门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伯尔曼(Mr.Pohlman)的话说:“仅在这个城市,就有1000家鸦片馆,那里除了提供鸦片,还提供烟具。”
这份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开放通商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所有城镇,都可能见到这样一幕:
吸毒的父亲和丈夫让家人陷入不幸的窘境,甚至以乞讨为生。很多人失去房子和家庭,在大街上、田野中、河岸边奄奄一息,垂死挣扎,没有一个陌生人会去照顾他们。他们死去之后,曝尸荒野之中。
从事正当贸易的商人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结束4年之后,即1846年,《广州通闻》(The Canton Circular)发表评论说:“考虑到孟加拉鸦片的原始成本每箱为250卢比左右,现在的售价是1200或1600卢比,我们无需再问谁是这场鸦片战争的最大受益者。鸦片贸易确定无疑是一个大魔鬼,现在,它对其他商品的销售造成了间接伤害。”
1847年4月20日,英国议员诺顿(W.Norton)在下议院作证时说,在1846年,英国(包括英属印度)对中国出口额为232万英镑,进口额为449万英镑,中国实现的贸易顺差为217万英镑,“如果这个数据属实,我很自然就会想到,英国工业品贸易将有很大增长空间。但是,因为购买鸦片的支出达到540万英镑,中国最终出现了232万英镑的赤字……将中国逼迫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最终使他们放弃对工业品的购买”。
两年之后,已卸任的香港第一任财政司长、英国商人蒙哥马利·马汀发出感叹:“自北部开港之后,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妨害发展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
马汀举了一个生丝的例子。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前,上海运往大不列颠的生丝,每年是3000~5000包,到了1848年,增长到了17000包,“生丝出口量的大量增加,本来应该有利于对英国制成品的进口。但是,不幸的是,鸦片交易使进口减少了……没有克服这个困难的办法,鸦片贸易稳步增加。大不列颠对茶叶和生丝消费的增加,只能导致鸦片贸易的增加。大不列颠制造业在中国毫无希望”。
马汀曾询问在上海的道台,怎样才能让中国多进口外国的工业产品,“他给我的答案是,‘别再卖给我们这么多的鸦片,我们就有钱买你们的产品了’。我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英国领事巴尔弗(Captain Balfour)也在场”。
马汀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和商人。1845年1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报道说,马汀在香港财政司长任上时,曾建议英国政府放弃香港岛,与清政府交换浙江舟山,因为“现在发现舟山比香港更适合于贸易的目的,它比香港更富裕,无疑也更具生产力。香港只是一个贫瘠的船坞。舟山则相反,它出产的大米足以支撑大量人口”。
1850年1月,美国外交家、收藏家、在东印度与中国做贸易生意的美国商人基甸·奈伊(Gideon Nye)在纽约《商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茶叶与茶叶贸易》的文章引述另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西方商人的话说:“中国不能同时接受商品和毒品,因此,就英国而言,哪个工业应该受到鼓励?”
到了1856年,这场论争甚至吸引了英国军界高层的注意。在这年出版的一本论述鸦片走私弊端的著作中,陆军少将亚历山大(R。Alexander)引述了一组广州商会(The Canton Chamber of Commerce)披露的数据:
1837年,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顺差是320万英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86万英镑,二者——全都是合法贸易——合起来是406万英镑。同等水平的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到1852年。但是,这些贸易顺差都被鸦片贸易给吞噬了。鸦片贸易每年从中国人那里提走了400万英镑……据估计,中国用于支付鸦片的资金在本世纪已经达到9000万英镑左右。
亚历山大写道,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是,鸦片价格维持或者上涨的同时,西方工业品的价格却逐渐下降,降幅达到1/3甚至是1/2,在很多情况下,价格甚至低于制造成本,不包括运输成本的纯制造成本。比如,在1836至1837年,上等棉布价格为每匹1英镑,而到了1851年,最低降到了7至11先令(1英镑=20先令);同期,鸦片的交易量翻了一倍,而售价却基本维持原有水平。
尽管鸦片贸易影响到英国商人的合法贸易,取缔鸦片贸易却并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这会严重影响英属印度政府的收入,从而影响到英国在印度的控制力。在印度宗教复兴、民族主义复兴的背景下,这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正如《美国药学杂志》的评论:“没有来自鸦片贸易的巨额收入,英属印度政府将无法维继。”
鸦片对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要性,可以用《商人杂志》披露的一组数据予以说明:1845年,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40000箱,英属印度政府获得了476.65万英镑的财政收入。这笔收入占总收入的20%左右。
既然一方面合法商人不断叫屈,另一方面鸦片贸易必须维持,英国政府和议会只剩下一个选项:继续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是英国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蒙哥马利·马汀在1849年的《中国之友》杂志上已道出玄机:“关于我们不完善的对华贸易,真正的补救方式不在于削减100万或200万英镑的茶叶关税,而在于与中国进行完美的自由贸易,在于深入那个庞大的国家的内陆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