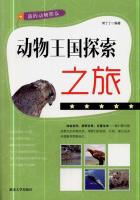橘色的手拉箱立在门口两步的地方,是逾白忘记收进来的,然而现在只是看着他也没有动作。在逾白眼里那是个着黄裳的侍女,他要等她先开口。这时江太太走来,随手拆下掖在腰里的围裙,像拉着新媳妇似的把那位侍女引向床边雕花的衣柜。
“这次住多久?”江太太蹲下去,边给他折衣服边问。
“住不了很长时间,”逾白道,“这次是要见两个同学、办几件事,然后就回去。深圳那边盯得紧,催命一样一天一个电话。”
江太太笑了一声,拍了拍手臂上搭着的衣服道:“我说什么来着,打上中学的时候你就嫌这个县城搁不下你,就准备撩翅膀往外飞。现在看真是白养你了。”
“你替肥乡县的三十万人不平?”逾白笑问。
江太太抬头嗔视了他一眼,又笑出来:“我哪儿管得上他们,我是为自己的心不平。”
她背向逾白,左右打叠着箱子里的衣物。逾白看着母亲两手的闪动,恍惚觉得是抚琴一样的天然神韵。她就是一位如此的女性,在他的衣服上都能弹拨出开花的音律。然而鬓角已经能看得见白丝线了。森森白骨的亮白,刺得他心内绞痛。
“妈妈,如果你放不下那我就不回去了。我可以的。”
江太太回过头来,认真看了逾白一回,手搁在腰袢上说:“你就这么盼你妈不开明?跟我还说这种客套话。去吧,没人给你定罪,你的好强名声都在外边传着呢。要是摁着你不放倒显得我老糊涂没药救了。”
逾白将胸前吹着的几绺毛辫子推来荡去,感激地看着母亲。
“茉莉一早就知道你要回来了,打听了几次。她也摸不准你什么时候到家,难为她一趟趟来了。”江太太又转回去,从柜子底往外刨换季的衣裳,再折好了铺进逾白的箱子里。
逾白只顾着拿手指绕着胸前的线头,似要织出什么绫罗绸缎来。
“你倒是去看看她,别老让人家过来。毕竟是女孩子。”
“我想着她是女孩子才不方便去的,”逾白微笑着说,“一年大二年小的,况且她又跟良柯订了婚,怎么好再去。”
江太太打理好衣物,回来伏在印着散花的藏青床罩上,推着逾白的背道:“你就是一头犟驴……”待要再说什么,却忽然打住了——她的儿子,全世界的名门小姐只要他瞧不上,自己也不会高看一眼。
江太太收拾了几盘香给逾白的房间熏上便出去了。烟雾甫一散开便无序地横钻过来,闻得逾白直有些醉。房里的陈设为了防尘都苫上绛紫的帘布,时间的尘灰就因为这层隔膜而无处自容。逾白揭开一抖,它们便纷纷扬扬地落转成雨。
那只橘色的箱子仍旧文文静静地立着,只不过换了一处地方。经江太太的一番打理后成了仪态万千的佳人。逾白跟她一前一后相顾无言,大约就像古时候洞房烛影下的新爱侣。这有些讽刺的意味,几个月之后茉莉的合卺之礼就到了,他不能不有些落寞。
逾白有整理的习惯,连脑中的回忆都给订成册子。这一下落寞像一阵风,带着册子哗哗地翻,电影似的回放了一遍,最后停在一对少年男女的稚脸上,双双笑得夺目。那笑自成一枚印章,在年月里戳下的印子比什么盟誓都恒久。
余温未去的下午,连树影都软塌塌地横躺成条纹波浪。逾白看着白茉莉已经有一会儿工夫了。
毛毵毵的斜光照着那侧脸,晃得他眼睛辣辣的。她胸前敞着一朵朱红的褶绒花,像极盛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身上的装束,妩媚又威严。两臂搭在绒花的侧面,微伸着汉白玉的手指虚抵在桌子上。
逾白停下来,细细回看了一下册子,像忆起来她为何会单独地立在课堂上。那时茉莉的脸上薄暮茫茫,与太阳的余晖交映莫辨,渐渐抹清楚了逾白的疑惑。是了,那时候她是在声乐课上唱一支曲子,李叔同填了词,并且取调于约翰·奥德威的《送别》。
她轻缓地哼着,把赤色烽烟的年代一点点揪出来展览给他们这些懵懂的婴儿;又用手双双团住,漏去了战争的亡故跟血腥,留下来的只是痴男怨女们的纠缠。仿佛她自己成了李叔同的恋人,引起逾白一阵忽然的妒忌。
他吃味得有道理。茉莉这支曲子摄动了声所能及的所有人,鲜红的心被她一网打尽。唱罢她又转个圈,微笑着把底下的人再瞧一遍,还要看看有没有漏网的。她的眼光免不了要跟逾白撞到,示威似的。
“如果为了她,我倒愿意去做那个李叔同。”邻座的徐良柯道。
逾白低下头在笔记簿上画着竖道子,闷声说:“送别之前是李叔同,送别了红尘烦恼后却是弘一法师了。你拿好主意,真要赔上半辈子的苦禅?”
徐良柯想了一想,道:“要是能分享她的光阴,上半辈子已经足够了;若是不能,还要下半世有什么用?”
良柯的鬓眉浓重,像上了妆的戏子。逾白抬起头来要笑他,却被一阵茉莉的香气噎住了。她走过来俯下身子,头发从一侧斜流下来,一只蝴蝶形的鎏银发卡活生生地栖在长发上。她的白手撑在桌角,与良柯、逾白各自的一只手凑在一起,恰是三分魏蜀吴。
“这两个音乐之王,睁眼瞧一瞧我们这些俗人吧。请你们弹个伴奏都死活请不动。我们真就一点儿配不上听你们的琴?”
良柯笑着摆手:“别看我,我是鼓手。弹琴是逾白的项目。”
茉莉又转去质询逾白,那边他早就不声不响地收拾整齐,拎起包咳了两声就走了。
茉莉的脸白了一下,头上的银蝶夹子颤起来。蝶翅一动,就洒出银色的光雨。
良柯大概也替逾白羞耻,忙向她说:“逾白平时不这样的。兴许是上午练琴练得不顺才这么臭着脸。”
茉莉一笑,用粉指甲抵着逾白那块桌子来回划着:“我都知道,不用你给他开脱——他什么样我怎么会不知道,他就是一头犟驴……”她说到最后简直细不可闻。笑得也很奇怪,像映在池子里的一张笑脸,水面一皱便掺进去几道忧郁的纹路。
逾白从教室里出来就感到变了天,含着怒容的低空扮成一张女人面孔用力向下凸伸,唇吻几乎要够到他的头发了。走了一两步以后就立刻开始丢雨点,而且一滴重过一滴。逾白反倒使性子似的慢了下来,从惊叫着纷纷逃去避雨的同学中间庄严地过去。他想,那些都是按了快速键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唯有他是一勺一勺取来品尝的。
路两边的白悬铃木织了一条拱顶在头上,然而枝粗叶大,兜不住雨。几株红枫树的叶子也是闻风就落,混着悬铃木的宽叶贴在雨地里。居民的住房是红砖砌的,淋了雨后红得简直要沁出来,一幢一幢地挤出一条逼仄的路径。
逾白回头望望,看见茉莉在跟着走,而且湿漉漉得娇艳——她也赌气没撑伞。逾白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再装作路人了。路上就他们两个,然而夹路的两排树静静地做打扇的宫娥,左右斜举着一只象牙柄的蒲扇。她们都冷眼看着他的绝情。
揩抹几下脸上的雨水后逾白折了回去。他的视线被雨水割得零零碎碎,拼不到一起,走近了却看到茉莉手上忽然生出一柄白伞来,衣服也从红色的绒衫褪成了素白的长裙。
逾白慢慢从回忆里剥落出来,看着茉莉三两步走到跟前将伞举在自己头上,笑说:“我还道这人怎么也像你似的那么犟,原来就是正主。你什么时候到家的?”
逾白张了张嘴,忽然噎住了。她的脸还有少女时的样子,只是头发更长了些,美得更加惊魂。从前她是白茫茫的雪原,天地一色;现在成了琉璃世界的白雪与红梅,多出来的一点儿红就红了逾白的眼眶。
逾白捂了一杯热茶在掌窝里,瞧茉莉端着熨斗给他熨衣服。她的房间也没有大变,只是时间一年年地留下了印子——譬如《卡萨布兰卡》的海报颜色淡了下来,墙壁也不像他记忆里白得那么烫眼了。黄油油的一只马丁牌吉他用带子斜挂在墙上。
“你已经变成贤惠的好太太了。”逾白看着杯子里金鱼一样游弋的茶叶片,不知是对茉莉还是对自己说。
“你放过我吧,我还想多当一阵子姑娘。”茉莉对着手中的熨斗笑道,“你不是最讨厌小县城的主妇们嚼舌头吗?深圳怎么样,大地方的人应该不像我们似的惹你烦吧?”
她揶揄的时候也不忘放出茉莉的香气。手里的熨斗像泰坦尼克在逾白的衣服上驰游。
“什么大地方的人,只不过把俗气藏在心里不露出来吧。”逾白往嘴里送了一口茶,“说真心话,外面的人没一个比得了良柯。你嫁他是嫁对了。”
茉莉忽然按住不动了,仔细看着逾白:“你这是笑话他呢,还是笑话我呢?”
隔了一会儿,逾白才笑着搪塞:“哎哎,你再这么着我的衣服都要烫坏了。”
茉莉却像没听到似的,还是盯着他不放,逾白也就不再说了。两个人都沉默着,要给那件衣服执行焚烧的极刑。
快烫得冒烟时,还是逾白先过去要挪开它。茉莉的倔强劲儿却上来了,把他伸来的手拍下去。
逾白眯起眼看她,显得两个人像是西部片里一对要决斗的牛仔。遍地黄沙中双双按着腰胯一侧的左轮手枪。这一下还是逾白先发枪,他要用蛮力去夺了,拎起那块烙铁就要扯过来。茉莉便倔强地用手扣住泰坦尼克的船舷。
“你干什么!”逾白顾不得体面,掰开她的手把熨斗咣当扔出去。然而茉莉的手面还是烧出来一片淤红,像攥着一朵红牡丹似的。
有花堪折直须折,这枝花却是逾白折不下来的。他把茉莉按到沙发上,自己去她的五斗橱里抱出来一卷子绷带和烫伤膏。
茉莉笑道:“你的记性还是这么灵光,比伦敦市图书馆的馆长还要强。”停了一停后又说,“你眼角的那粒疤还在?现在我烫了一下,也算扯平了。”说着她伸手要去摘他的眼镜。逾白往后撤了一撤,躲过去了。这一下两人都有些尴尬。
逾白想,到底是跟她生分了。
他走出去站在阳台上,蹬着圆石柱围出来的半圆栏杆向外望。天许许泛蓝,像一块被风兜起来的青花布,水洗得勤快直有些发白。
逾白摘下眼镜,用指尖碰一碰眼角那里乳白的疤,跟溅了一滴牛奶似的。
这时候茉莉也一起到了外面,拿了片做到半截的十字绣出来。刚扎下去一针就把逾白的手机扎响了。
“你现在已经是职业的主妇了。”逾白拿出来电话却不接,摆在两人中间成了采访她的样子。
茉莉嗤地一笑,转过身在格子布上穿针引线,逾白便跟打来电话的人寒暄起来。他的声儿有些大,故意要她听见——他明知她是听不懂德语的。那头是一个叫许尔勒的德国青年,他在深圳的同事。
逾白一面跟许尔勒谈工作,一面来回找眼光安放的地方。他越过她的肩看到几盏黄灯摇曳,店铺也陆续泼洒了一片橙光在门前。黑魆魆的人占满了街道中央,踏在落潮的潮头上似的往家里赶。逾白的眼光游了这半日也不愿落下去。始终那些是别家的灯火。他的故乡,还在他乡。
脚下有一阵门轴转的响声,是白太太回来了。逾白越过栏杆向下看了一眼,只来得及抓住一条杏黄影子的尾巴。他和茉莉沿着栈道似的楼梯下去,看到白太太像早就预计到了一样也没有去换衣服,就立在客厅门口等他们。逾白心想,他也是个成年人了,值得别人这样整装来迎接。
客厅四角各立着一杆落地长灯,低着头放光。地上铺着波斯羊毛毯,中央又垫了一块毛垫子,像华清池里的白波。垫子上搁着几组红沙发与一条狭长的橡木茶几。
白太太早就站在门扇边上,两手扶着杏黄长衣的对襟说:“逾白过来了。应该提早告诉我,好让我有时间去收拾饭菜。你叔叔老是谈起你,等他回来了你们叙叙。你现在做出事业了,县里几个人物可都盯着你。”
逾白笑着说:“哪儿就用得着这么麻烦。我就是来看看,立刻就走的。”
白太太又客套了几句,也没忘了给逾白端上来茶果,然后才去房间里换衣服。连换双鞋子都要避开他,可见当他是货真价实的客人了,为此不惜在毛毯上踩出一溜脚印来。
逾白将烫干的大衣折了一折放下去,伸手要去取一个茶杯来,却被白家的保姆抢先拿过去,另从底下抽了一个递给他。
“怎么,那杯子不能用?”
“那个是徐姑爷用的杯子,不好再给你用了。”保姆说话的时候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茉莉接了一通电话从里屋出来,见了忙说:“霞姐,你先放着吧,没关系。”
保姆看了两人一眼,提着两桶水似的一晃一晃出去了。茉莉坐下来,逾白便装作在糖果盘里找心仪的那颗。
“你还没定下来?”茉莉也伸出一根手指进来,跟他一起在盘子里搅。
“那边房子贵,我基础又不算厚,这事情还是要先放一放。”逾白在糖果的阵营里跟茉莉的手碰了几次,于是不战而退了。
“你跟良柯什么时候办事?赶在我假期里头就好了。”逾白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