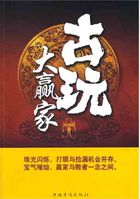平阳县西南三十五里的麻步镇,一座方圆数里的豪宅。
一丈多高的围墙内,曲径幽深的大院中,树木葱茏,流水潺潺。一方藕塘,碧绿荷叶铺得满满的,偶听三两声蛙鸣,随着淡淡荷香飘上来,在风中浮动。池边一棵古香樟树下,一座茅顶竹架的凉亭。黄梅就在凉亭之内,仰在黄藤躺椅之上。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黄大人,窦老头一去平阳县就把刘录勋软禁起来了,自己接管了整个平阳县事务。”
“刘录勋真是个笨蛋,平阳几百衙役,都是我十多年亲手调教出来的,竟然临事一个都没用上。”
“窦光鼐一接管平阳县,就将那几十个告状的乡绅全捉到堂上,直审了一上午,又是骂又是打,咆哮公堂,还把自己的一个指头给剁了。”
“窦光鼐真的动刑了吗?”
“好像动了,这个小的不太清楚,但咆哮公堂、辱骂乡绅是肯定有的。”
黄梅从桌上拿起那个紫色的嘉乐梅花斑鼻烟壶,倒出一点鼻烟来,往鼻子上抹了一些,重重打了个喷嚏,又问道:“我听说,平阳县又有人聚众,这一回是要跟着窦光鼐上杭州做证。窦老头好官声啊!事情好像闹得挺大,有几千人吧。那个吴荣烈去了没有?”
“按着大人的吩咐,只要吴荣烈敢迈出家门一步,定让他死在三尺台阶之下。那吴荣烈倒是老实,已经是三年未出家门了。”
“他儿子不是去杭州参加乡试了吗?有什么动静?”
“吴日功带了两个仆从,一去杭州便闭门读书,不与任何人交往。再过几天就是开考的日子了,看来他是求功名心切,并没其他想头。”
“继续给我盯着他,如有异动,也给我做掉他。不过,在杭州地界做得要隐秘些。李堂,还有一件事,那个夜救窦老头的黑衣汉子,你查到是什么人了吗?”
“只听说是管漕运的一个小头目。”
“一定是青帮的,要查出是哪个堂口的,然后带上厚礼去向他请罪。若不能为我所用,再想办法除掉他。此人是一大患!”
“嗻!窦老头那边怎么办?”
“咆哮公堂,聚众哄堂塞署,此乃不可恕之重罪。我会将此事转告给福岜臬台和范思敬太尊的。这么大的事,阿桂和曹文植那边也必得了消息,京中言官御史更不会闲着。到时候,京城内外,‘万箭齐发’,就算窦老头是铜头铁臂,也难逃此劫。”
杭州,阿桂的行辕书房之内。福崧、曹文植、伊龄阿、姜晟、和琳等人满满地聚了一屋子。
“皇上的谕旨,昨日就到了。福崧,你念一下。”
乾隆的这道谕旨直指窦光鼐,语气更加严厉:今窦光鼐固执己见,哓哓不休者,以为尽职乎,以为效忠乎?且窦光鼐身任学政,为国校士选材是其专责,现当宾兴大典,多士守候录科之时,该学政置分内之事于不办,必欲亲任访查,殊属轻重失当。平阳距杭州往返两千余里,寒窗之士苦守,国之大典不行,其忠心何在?且窦光鼐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冤,势必重蹈前明科道当廷争执,各挟私见,而不顾国事之陋习,不可不防其渐。其人大约亦不可承当学政之职耳!着窦光鼐交吏部议处,内阁中书陆锡熊暂代浙江学政,前往杭州交接。一俟陆锡熊到任,窦光鼐即起行入京。
福崧念罢,阿桂沉着脸道:“皇上还是下不了决心。等陆锡熊到了杭州,黄花菜都凉了!有这十多天的时间,窦光鼐还不把浙江搅翻了天!”
伊龄阿道:“桂中堂,要不要我立刻派人将他拿回杭州?”
“你凭什么拿他?谕旨上说是交吏部议处,待陆锡熊到杭后,才能行事。窦光鼐又没犯重罪,你若派兵拿他,你就先有了私捕朝廷大员之罪。不可!”
曹文植道:“那我亲自捧谕旨找到他,让他即刻入杭。”
“他听你的吗?窦光鼐的倔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软硬不吃。这道谕旨并未撤掉他吏部侍郎之职,他还能以二品官的身份压你。”
一干人正在苦思冥想搜肠刮肚地找主意,海成从门外疾步走进来,先向阿桂打个千,又向众人团施一礼道:“桂中堂,奉您的命令我派人跟踪窦光鼐留心查访。那窦光鼐一去平阳县,便监禁县令刘录勋,缉拿证人,强行逼供,当堂咆哮,竟有断指之举,又聚众于衙前,声称不做官不要命……”
在座的人听了这话都呆了,和琳惊道:“窦光鼐难道是疯了不成,怎会做出如此癫狂之举?”
一旁的姜晟冷笑道:“此人之奇异举动,超常之为,已经不止一回。和大人以前没听说过吗?”
阿桂立时有了精神,两眼放光道:“窦光鼐行为过于乖张,多行不义必自毙,也怪不得我不客气了。”转脸对福崧道,“你立刻替我写折子,参他私捕生员、用刑逼喝、勒写亲供、咆哮生事、当堂断指、聚众哄堂、监禁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