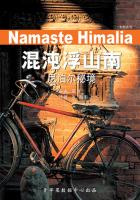乍一看随身携带的地图,可以得出这条线路有点复杂的印象;可事实上,尽管这次外出的旅程几乎全部远离公路,按这个行程计划找到去伯纳姆比奇斯的路应该是没什么困难的。从埃格姆到豪恩斯洛之间的距离,算上可能因探路而偏离的路程大约是五十六公里。埃格姆被选为唯一的极为方便的出发点,绝不会是其自身的原因,因为从此地有条通往沿江的路,直通旧温莎;从出发点我们向左急转弯去老温莎,而从火车站到出发点之间的大约一公里的马路可能是伦敦周边郡县最烂的一段柏油碎石路了;实际上从它到斯坦尼斯的大约二公里的延长线也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幸好沿河边的这条路完全不同,它是一条长长的沙质路,从拉尼米德平原贯穿而过,最先一公里带给人的是泰晤士河畔宜人的景色,左边是从沼泽地上升起的库珀山,树木繁茂、直插蓝天,右边是大宪章岛。这条沙质路在还没到旧温莎村之前就浸入了水中。注意看有个古色古香的酒吧,其招牌上写着“乌斯利之钟”,五只大钟从一棵古榆树上露了出来,摇曳多姿、生动有趣。这个招牌对游客来说是个谜。它来源于曾经闻名遐迩的牛津城那个消失了多时的奥斯尼修道院的钟塔,其悠扬的钟声远近皆知。
游客在这里面临着走哪条路的选择。到旧温莎最舒适的路是走容易骑车的纤夫走的一公里小路,它把人带入一条狭窄的小径,看起来就像一条隐秘的路,经过村子的小教堂。旧温莎教堂环境优雅,其本身并不让人有多大兴趣,尽管有些人在看到“珀迪达”一样的罗宾逊最后的安息地之后为了回忆她而要寻找些精神食粮,这个遭人遗弃的古人早期却享有“欧洲第一绅士”的美称。如果不是装扮成一个精彩的故事,她的生涯至少可以点出道德的真谛。“珀迪达”死于1800年12月26日;佛罗里泽尔又生活了将近三十多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在温莎大公园的一个马车里又老、又气喘、又肥胖、又憔悴,闷闷不乐地躲避着同胞们的视线,这个曾经快快乐乐的乔治四世死于1830年。他醉生梦死,但他那极其放荡的尸骨在靠近泰晤士河边的纤夫行走的小路旁全部腐朽而被人遗忘了。
离开旧温莎教堂,向右再转个弯就通往温莎镇,但我们不去皇家市镇,我们选择了右手边的岔路口,这里有个标志正确的路牌,我们经艾伯特大桥横过泰晤士河,进入了白金汉郡。沿河边行走不到一公里,向右转个弯,跨过达切特火车站纵横交错的铁轨就到了达切特村。这是一个很大部分重建过的村子,再过一百年(当它那现代化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住宅再经历一些风雨后)就会变得风光无限了。
我们现在走了左边的一条路到式样老套的厄普顿村去,这是斯劳这个现代化的郊区城镇的母教区,“斯劳的温莎”,乘坐大西部铁路公司火车的游客都熟悉它。也许应该记住斯劳人民,他们那时担忧并抵制这个不好听的城市的名字,为了显示他们的忠诚,经过几年的建议,把它的名字改成“厄普顿罗尔,”但这个方案最后无疾而终。
厄普顿这个如此靠近人口稠密的地方,却是极其的僻静。它有一座古老的并极为有趣的诺曼和英国早期的村庄教堂,享有斯托克波吉斯那种成为格雷的“乡村墓地上的挽歌”的景色的荣耀;但是追随本书作者车辙的游客将毫无疑问地像格雷和绝大多数到过两地的游客一样,更倾向于认为斯托克波吉斯墓地才是原型。不管怎样,也不管它那“爬满常春藤的教堂塔”是如何很好地回答这首诗的描述的,它现在都不可能夺去斯托克的声望了。
无论如何都要请自行车骑手不要遗漏去看看在教堂北面的一块破旧平整的石碑上一个极为费解的墓志铭,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意思已经完全难以理解了。它是这样的写的:
——此处躺着的是来自伊顿的莎拉·布拉姆斯通的遗体,独身女人,一个敢于在乔治二世王朝追求正义的人。
这确实相当奇怪,因为这不可能让人相信在乔治二世时代法律和规章会如此严厉地保护一个人“敢于追求正义”成为一件非常著名的事。有一首流行的赞美诗要求我们“敢于成为丹尼尔,”可是在莎拉·布拉姆斯通行走的狭窄小路旁为何有狮子在潜伏?必须要承认的是这非常激起人的好奇心。我们知道所罗门、朱利叶斯·凯撒、征服者威廉、以及其他成百上千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命运,也知道即便是他们都没有一直敢这么做;但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这块墓碑的秘密。
还要注意到,在教堂的北面有个乔治·福德姆的白色大理石墓,他是个赛马骑师,卒于1887年,时年五十岁,上有一句奇怪而有意思的引语,“这就是那致命的一步。”不了解乔治的好脾气的人很可能以此来中伤他的性格;但福德姆是最温和的赛马骑师,也是一个模范丈夫和父亲,而这只不过是一句联系不当的奇特而不幸的话。
离开厄普顿教堂,我们沿来路的相反方向横过古老的巴思路、跨过大西部铁路前往乔治格林。一条直路从那里通向兰利公园,穿过一个幽深的地方,就有一条对人车都极为便利的完全畅通无阻的道路。布莱克公园寂静无人,是个值得一游的地方;阵阵微风在一大片庄严的松树林中回荡、消散,或是没入密集的巨大的树干间,阳光从枝叶的罅隙滤过洒在有如地毯般的松针叶上,走在这样柔软的一层落叶上,你会迈过寂静的脚步,偶尔,你也能听到干树枝断裂的声音,这种破坏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越发使人吃惊。很少有人到这种林地里来过,就像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你,实际上也只有斑尾林鸽的时断时续的咕咕声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合唱。
而它那十二公顷的大湖也许才是布莱克公园的主要特征。湖边成排的大松树并肩耸立,悬垂于深沉的湖水上,你就能明白这个公园的名字恰如其分了。在这种地方你容易就能联想到自己就是罗宾逊·克鲁索,几处小沙滩露出了水面;僻静地那墨色的丛林看起来就像是在等待着探险者的到来,以寻找野性,探寻那毫无疑问隐藏在那里的大游戏;而事实上,你最想要的、最开心的就是一个木筏,一支步枪,一套山羊皮衣服,一名得力助手,还有一群用来射击的敌人。这当然是R·L·史蒂文森最陶醉的地方了。
如果不是非得赶到伯纳姆比奇去,相比起在这里呆一个下午或有可能在威塞姆街(不要把它与威塞姆村弄混了)的“普劳”喝喝茶,什么事都没有这么心情愉快。离开湖尾与其相接的小路,向右拐不到一公里就可以到达一个漂亮的小村舍,再向左拐就到了一条从威塞姆村到法纳姆罗尔和伯纳姆的宽阔的大道,到了这条路,不要横过它而是要向右转,然后还要左转一次,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条向下走的林荫小道。从牧场边俯视这条小路的右边,可一眼瞥见一座庄严的陵墓一样的纪念碑。它充分地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已经到了斯托克波奇了,因为这座纪念碑是威廉·佩恩的后代为大诗人格雷建立的,他曾经定居于斯托克公园。公园里那幢很大的、看起来很古怪的宅第可以从斯托克波奇墓地看得到,它属于光明和引路的人们。它现在是布莱恩特与梅公司中布莱恩特先生的住所了,他从杰里迈亚·科尔曼先生那里购到手,它原来是科尔曼的最爱。
这座忧伤的纪念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建在底座上的茶叶罐或者说像一个饼干盒,上面刻有格雷的忧伤的灵感闪现的诗节——它选自《挽歌》和《伊顿远眺》。在参观了格雷纪念碑之后沿小路走数米远,右边有扇白色的大门,其破旧的小屋从地面到砖砌的烟囱的最高处爬满了常春藤,从这里可以通向公园,这也是到斯托克波吉斯墓地的入口。我们把自行车靠在村舍的栅栏边,穿过一个非常漂亮的由橡树雕刻的现代停枢门,步行到朝圣之地。远远地,教堂的塔尖和“爬满常春藤的教堂塔”露了出来;说来也奇怪,整个教堂就如大家所期盼的那样非常漂亮;只是有一点例外,那就是教堂墓地现在太大、太拥挤了,那些显眼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并不能完全体现这一著名诗篇的乡村氛围。但那是细节问题了。在教堂的东窗下面的墓地里,格雷永生不死了。他与他母亲、姨妈一道躺在一个安静、质朴的坟墓里,永远地安息了。
托马斯·格雷为大家所熟知,主要在于他是《墓园挽歌》的作者,这首著名的诗歌的标题就是他亲自加上去的。他出生于1716年末,是菲利普与多罗西·格雷的儿子。菲利普似乎想做个“法律代书人,”也似乎一直处于发疯的边缘,他在他儿子二十五岁时去世。诗人在伊顿和剑桥接受教育,他一生体质孱弱,忧郁地受到诅咒,这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一部分是装扮的,他是他母亲十二个婴儿中唯一幸存的孩子。他谋生的手段极为贫乏,只是带着他的经典著作漫不经心地度过了五十四个春秋,很多事情都是计划得多完成得少。他的英文诗歌数量极少,就像他整个的作品都很少一样,他的一些诗作甚至还只是一些片断。他那病态的性格有可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只有他的亲人或朋友去世了才会激起他的创作。因而这首著名的《挽歌》起笔于1742年,直到1750年才完成,是由于其构思和连续有亲人丧亡而经历几个缓慢的阶段而致;而《伊顿远眺》也来源于同样的悲哀的习惯。除了做为学者,格雷做为一个诗人其整个生涯和声望都包含在这两首诗里了,这两首诗在英文诗歌里的排名都非常靠前。
格雷的冥想是不健康的,也是与现代的思想不相称的,同时也与他自身并不很相配。他的体质影响了他的性格;他那范围狭小的、懒散的生活使得他思想病态,最终缩短了他的寿命。他于1771年去世。据信,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接受过单笔超过四十“几尼”的文学著作报酬。至于《挽歌》这部使他声名不朽的诗篇,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也不可能接受任何金钱报酬。他允许多兹利及其他出版商出版这首诗,确实使他们从此处获得了一笔横财。也许,还有必需再说一句,这种诗人现在已经灭绝了。在科利·西伯于1757年去世后,格雷拒绝了荣获桂冠诗人的提议,有种意见认为这是在一个绅士的尊严下去接受他的“发明创造”的报酬。像丁尼生这样的人与出版商精明地讨价还价,靠着他的著作建立起财富,然后再进行牛奶贸易,他该如何鄙视啊!
顺便提一下,很有趣地读到一个对《挽歌》的现代“评论”,它是这样写的:“一首挽歌写于乡村墓地,多兹利,七页,这首小诗的优点弥补了其数量的不足。”是谁写出的这个“评论”?是布商还是食杂商,他们对这种缺斤少两的反对由于质量优胜而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