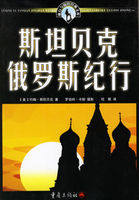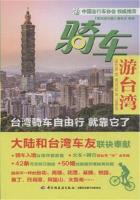沿着从北边分叉出来一条偏僻的道路,我们离开了吉尔福德漂亮的大街,过了这最有描绘价值的地段,走了不到一英里,穿过韦河,我们来到一段山坡。到了这儿向左转,我们将通往伍德街人迹罕至的小村庄,有不少路都能到那儿,有的笔直,有的弯曲。1935年威廉姆柯博特在那座“诺曼底”村逝世,如说他确实是第一位“向父亲一样关爱马鹿”的人,那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对树也怀着同样伟大的爱。在这儿,在这个有着奇怪名字的诺曼底,他一边与意气相投的同行和反对他们政客周旋,一边建造种植园,他当年亲手种的许多数苗如今都长成了森林,为整个乡村披上了绿色的外衣。
一路通往哈什和法纳姆,可以越来越明显的看到奥尔德肖特营地的周边环境,好在柯博特生前没有一颗平静的心,因为虽然他参了军,却是个典型的独立主义者,而且立场坚定,他变得仇视军人,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向军队泄愤的机会。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一定能在这儿,在他的出生地法纳姆周围找到大把大把的机会。在这儿身穿红装的英国军人(当然也有穿蓝色,灰色,绿色或者卡其色的)随处可见,不管走在路上,还是站在路上,总是被转满炸药的车队袭击,或是遇到枪击丧命。
穿梭在哈什境内弯弯曲曲的小路上,那儿的旅馆是为那些优秀的英雄军官们准备的,也有的只为皇室服务,形形色色的商店展示出士兵们平淡无奇又琐碎的生活,除了光辉荣耀,这些大概就是一个英国士兵的一切,他们拿着落满灰尘,好不体面的钻孔机,穿梭在营地大院里,日复一日地待在这撒哈拉沙漠一样的大山谷。
那些对军队生活有兴趣的人(大部人都有),会觉得奥尔德肖特周边,以及它的营地特别有意思,但它完全没有美感。
经过哈什,不知不觉已经走了一英里,早就过了萨里郡,来到汉普郡,我们又倒回去一英里,重新走了一次,不是因为走在这么体面,这么笔直的公路上突发奇想,而是被曲折迂回的边界那种难以捉摸的独特个性吸引。然后,经过一系列没开发的小村庄,虽然不被承认,它们的确是奥尔德肖特的分支,这些小村庄零零星星地散落在远处那布满沙石的荒地上,一直延伸到猪背山的尾部,而这灌木丛生的小村里那一片片落叶松和冷杉就是猪的鬓毛。
在路口处往右走我们来到法汉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儿比起一英里以外“好多了”,不过可以想象,走了整整一天之后,这儿看起来可能会“更糟糕”。尽管周边有军队,法汉姆本身却是个安静,繁华的古镇,一条巨大的街道横跨东西,镇中央还有一条很短但很宽广的街道,向北延伸到城堡,过了城堡是一片混乱的沙漠,上面立着几棵冷杉。法汉姆城堡与这个小镇有着相同的气息,这源于它的安静,近八百年来一如既往地安静祥和,温切斯特的主教就居住在这儿。虽然如今看来,主教比起军人,政治家或者牧师确实没多大分量,但当初正是亨利布卢瓦主教建了这座堡垒。法汉姆安静地高雅,安静的恰到好处。城堡的花园里柏树成荫,风光秀美,废弃的要塞就在这儿,这片庞大的建筑群,留下了不少古老的遗迹,但只有极少数曾在17世纪末被莫勒主教保留下来,近几年的主教把这当做了住宅,自然也就没了考古价值。即便如此,从这儿俯视法汉姆,面前这一长幅形形色色的画面,感觉像堵塞了街道一样,看起来依然很壮观。
大街的另一头通往教堂,人们在教堂墓地朝拜柯博特,那位热情的改革家,四十年来为了对抗政治上的谴责之声磨破了嘴皮,如今就躺在北面那座围满栏杆的圣坛形纪念碑下面。要说有什么高兴点儿的地方,就属他的出生地了,那是修道院大街上一座带三角墙的房子,现在成了“乔莉农夫的小旅馆”,它对面是横跨韦河的一座大桥。
他出生于1762年,独自生活了大半生,或许他熟悉的所有地方中,只有这间小屋还维持着原样。
过了火车站,法汉姆就在身后了,我们的目的地是韦弗利修道院。沿路到处都是工业飞速发展的迹象,不难看出这儿是个商业中心,你甚至能闻到这股气息,初秋正是啤酒花盛开的日子,在每个路口都能看到装满大麻袋(他们叫“口袋”)的卡车轰轰隆隆地驶过,袋子里满是啤酒花,芳香四溢,勾起人强烈的食欲。
过了平交路口往左走,不到两英里就来到韦弗利,左边有座摩尔公园,威廉姆特普先生曾坐在那儿,他资助过斯威夫特——一个“行为古怪,笨手笨脚,坏脾气的爱尔兰年轻人”,曾担任这位退休的政治家的秘书。对于这个比男仆好听点的职位,只要看看斯威夫特在仆役大厅和吉福德夫人的女仆开始的一段调情,你就知道它多没尊严,“哪一个”,麦考利问,“能像比特拉克阿伯拉德的情事一样出名?”那位女仆是“斯特拉”,而这位可怜的秘书成了那位讨人厌的天才,哲学家斯威夫特。
公园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崎岖不平的地形,阴森森的针叶树,还有静静流过这儿的韦河。根据这儿之前的主人——威廉姆特普先生的要求,他的心脏被装在一个银盒子里,埋葬在房前的日晷下面。这片地区的另一个尽头是个有名的洞穴——“拉德拉姆修女之穴”,洞里有洼泉水,为了防止那些粗俗的亵渎行为,四周都用装饰性的铁轨围了起来。据说韦弗利修道院的修道者就是在这儿找到了饮用水源。“拉德拉姆修女”只是个虚构的人物,像小精灵一样,据迷信的农民说,她能满足恳求者的任何要求,只要他们在午夜时来到山洞,来回折返三次,每次都重复他们的要求,并承诺两天内归还借走的东西。第二天一早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就会出现在山洞口。这位善良的修女最后把一个大锅借给了某个不守承诺的人,也或许是忘了归还,从那以后这魔法就不灵了。这个故事是有依据的,那个大锅就保存在弗兰汉斯教堂的礼拜室里,至今还能看到。这一定是事实,千真万确!
摩尔公园的入口旁有间玫瑰盘绕的漂亮小屋,如今还叫“斯特拉的小屋”,对面是条公路,公路右边是韦弗里修道院的大门,从那儿进修道院,里边只有几处废墟留在韦河边平坦的草地上,这儿可以看到坎特伯格山,山上覆盖着松林,一片昏暗。小河流过这些破碎的墙壁,流过英格兰第一座西多会修道院这点可怜的遗迹,正好饶了四分之三个圆圈。实际上,这座修道院留在地下的部分比较多,地下室就保存得非常好。
或许这里最有趣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一点体现在韦弗利小说的标题上,因为它来源于这些破碎的墙壁。斯考特曾阅读过这座宗教同宗一些现存的记录(“韦弗利年鉴”),那充满音乐感的标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了韦弗利修道院,眼前是那座黑暗的,松林覆盖的坎特伯格山,要想去斯格勒和一些周边村落,必须的爬到北边山肩那儿,这些村落就在下边,在从吉尔福德到法汉姆这段北部高地的背阴面,这段绵延10英里的山地就是著名的猪背山。希尔是个笼罩在松林里的隐秘小角落。从那儿顺着通往吉尔福德的山脉,沿着山脚下一条荒僻的小路向前走两英里,我们便来到普顿汉,这一派风景如画,都要归功于背后群山耸立,密林丛生的宏伟景象,没有了这片美景作衬托,这儿就没什么特别的了。
我们从这儿转弯,沿东南方向走,离开山脉和丛林的怀抱通往康普顿,康普顿能够闻名于世得益于一座诺曼底的早期英国式教堂,因为环绕在茂密的树丛中,顶尖又是用木瓦制成,一点也不出风头,所以对陌生人来说几乎很难发现。注意屋顶上奇怪的老虎窗,和一般住宅里的也差不多。不过最奇特的是这儿的圣坛有两层,这样的结构很不常见,这也是它最不同寻常的地方。圣坛的外形不说丑也算很普通了,曾在1860年重建,那时外面有段楼梯的遗迹损坏了,这段楼梯正好通往圣坛上层,但这里面还是特别漂亮、特别有意思的。圣坛被一座半圆拱从中殿隔开,半圆拱上点缀着着狗牙状的模刻,一上祭坛,立马又有一座一模一样的,不过只有它的一半大。这些与交叉拱结构的天花板一起把整座建筑的东半部分隔成了两层,圣坛也就成了两层。人们猜测上半部分有两个用途,一个是作为摆放圣十字架的阁楼,另一个是用附属教堂。但是除了猜想,没有人能进一步去探索,因为整个教堂历史从没提到这一点。
从康普顿到鲁斯利公园的入口只有一英里.大门在入口左边,从那儿进去,整个公园路树成荫,那份独居的幽静和野性的气息,很可能就是睡美人的原型.这就是鲁斯利,还有建于早期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灰白色石头屋,像幽灵般矗立在林荫小道的尽头。威廉姆摩尔于1515年开始建造鲁斯利,但建筑师设计完以后,这儿却一直没建成。即便这样,它依然是座雄伟的大宅院,珍藏着许多着色玻璃和各种雕刻品,还有保留下来的盔甲和遗迹,这些足以让它声名远播。保存在这儿的“鲁斯利抄本”,收集了近五百年来英国最出名的政治家和历史杰出人物的信件,是此类收藏中最优秀的一部。
围着公园漫步你会来到一条左右叉开的路口,往右走会继续绕着公园转,经过另一座古宅——布拉普夫公寓,然后是古老的普利茅斯公路,最后到达圣凯瑟琳山。往左走是通往吉尔福德的下坡路。在旅途结束前,我们不妨沿着这条好爬的小路上山,俯瞰陪伴我们大部分旅途的这位神秘伙伴——韦河,它正远远地流过圣凯瑟琳渡口。我们所在的这条山谷,坐落在山腰上,是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地方,古老的公路从山谷中穿过,一直通往朴茨茅斯。很多年前一些公路信托——如今再就解散了,曾因为马的原因降低了通往山顶了公路,从那时起,著名的“圣凯瑟琳山谷”成了画家的天堂。特纳就曾经在这作画,不过他更注重展现远处那座废弃的圣凯瑟琳教堂,没有花心思雕琢这份野性美,细细描绘那些弯弯曲曲突起的陡坡。它们由深黄色的沙子和极其柔软的砂岩组成,在各个地方形成一座座悬崖,悬崖看起来并不小,但崖沙燕却在这挖好隧道安了家,这里成了它们安全的避难所。这悬崖看起来密密麻麻的全是洞穴,就像多佛白崖上的炮台,如果你有耐心,愿意安静的等会儿,你会看到这些可爱的居民正在那边进进出出。其他的隧道要大一些,也没有这么整齐。这都是兔子洞了。下面还有个更大的隧道——在从吉尔福德到高达明的西南铁路上,它在1895年的一个午夜突然坍塌,从山顶别墅的马厩里驶下来的马匹和马车都被掩埋了。还有一些马匹和车辆跌入下面的深渊,摔得粉碎。这条路堵塞了一个星期,其间人们在隧道另一头的路边草坪上建了个临时车站——“圣凯瑟琳站”,这儿竟然堆满了从英国进口的公共汽车,用来搭载往返于吉尔福德站和临时车站的乘客。那座早就毁坏了的圣凯瑟琳教堂侥幸躲过这场灾难,没有完全毁掉,但它还是那样,没有屋顶,破旧不堪,像是死了好几个世纪一般。或许在这个古迹修复盛行的时代,它会被恢复成原来漂亮的样子,甚至连附近山顶那座圣玛莎教堂也可能重修。带着这个猜想,我们将结束这段漫长的旅程通往吉尔福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