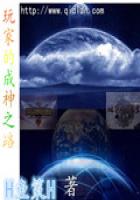“嘭!”屋子里猛然传出一声拳击几案的巨响,紧接着是一串清脆的爆裂声。
四风闸辛宅的院落里,刘汉正在教刘忠舞剑,听到这阵奇怪的响声,连忙推开房门,走进屋来。只见辛弃疾一个人愤怒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只磁花瓶在地下打得粉碎,一摊碎纸七零八落地扔在几案上。刘汉看到这一情景,不解地问道:“怎么啦?”
辛弃疾冲到几案前,抓起那摊纸片,朝刘汉手中一塞:“汉老爹,你看看上面,真把我肺都气炸了!”
刘忠站在一旁,忍不住笑了:“哥哥,你气胡涂了,我爷爷哪里识字呢?”
辛弃疾也失笑起来。
“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刘汉摸不着头脑,再次追问道。
辛弃疾的脸色严峻起来:“汉老爹,这是党怀英寄来的信。今年他又去燕京赶考,在那里见到了他那个姓刘的老师。他说,就是那个刘瞻,巳在金廷里面混上个什么史馆编修的伪官了!”
刘汉恍然大悟:“原来是生你老师的气!”
“不,我根本不承认他是我的老师!”辛弃疾把手一挥,用鄙视的口吻说道,“不过,我主要还不是气的这个!”
刘忠插嘴道:“那哥哥就赶快说吧,说出来,我和爷爷帮你出气!”
“是这样。”辛弃疾压住怒火,一口气说了下去。
原来党怀英在信中说,刘瞻因为在金廷里面担任“国史”的编修工作,知道一些内幕消息。据说早几年前,完颜亮秘密派了一个画工随同使者到南宋朝廷去,偷偷把南宋京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的全景画了一张图带回来。完颜亮看到临安山明水秀,就叫画工把自己骑马的肖像补画在图中临安的最高峰上,并且得意洋洋地在上面题了一首七言绝句,夸下海口,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刘瞻说,这早晚完颜亮就准备带兵大举南下,消灭宋王朝了,因此希望党怀英劝说辛弃疾,别再不识时务,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在金廷里面弄个一官半职,才是唯一的出路。
刘汉静静地听着,不时抬头望望眼前这二十二岁的青年。啊,这孩子变化多大啊!高大的身躯和宽阔的肩膀,看上去有使不完的力量;长方脸上一双大眼,放射出逼人的光芒;两道又宽又黑的浓眉,又给这张英俊的脸庞添上了几分粗犷的气概——“长大了,成人了!”刘汉默默地思忖着。
“汉老爹,”辛弃疾越说声音越高,“你看,完颜亮是这样的猖狂跋扈,咱们大宋朝廷却是那样的懦弱无能,而且在咱们汉人当中,竟然也有象刘瞻一类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这怎能不教人悲愤啊!”
刘汉的情绪也随之激动起来。他那银白色的长须不停地抖动着,古铜色的伤疤也泛出了红光。他霍地站起身来,猛击几案,愤怒地说道:“完颜亮那小子要立马吴山,咱们不能做绊马索?他要带兵南下,咱们不能背后刺他一剑?”
“对!”辛弃疾受到启发鼓舞,斗志昂扬地叫道,“听说中原的百姓已在到处起事,咱们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咱们要拖住他的后腿,刺穿他的脊背,砸碎他的脑袋!”
早饭过后,辛弃疾的心情还是无法平静下来。他走到马厩里,牵出那匹心爱的枣红马,纵身一跃,上了马背。那枣红马好象了解主人的心情,不用鞭策,四个马蹄就翻盏撒钹似地向南飞奔。辛弃疾骑在马上,敞开衣襟,尽情承受着呼啸的秋风……
枣红马顺着驿道一个劲儿地奔跑,直到太阳快当顶,才开始放慢它的脚步。这时,一座山冈横在辛弃疾的面前。
绕过这道山冈,眼前豁然一亮。青山脚下,是一座巍巍古塔。古塔旁边,绿树掩映着一带黄墙。微风过处,悠悠地传来钟磬和檐铃的清音。辛弃疾勒住马缰,抬头一看,原来已经到了灵岩寺了。
这灵岩寺在四风闸东南七十多里。寺院背靠苍郁的青山,面临清澈的泉水,风景极为幽美。特别因为寺院大殿上有着四十尊泥塑的和尚,相传出自盛唐时期巧匠之手,塑得栩栩如生,出神入化,更使这灵岩寺名声远扬。眼下,这寺里有二、三百个和尚,住持的方丈名叫义端。辛弃疾从谯县回到家乡以后,曾经到这儿来游览过几次。义端知道辛家在济南一带有些名望,辛赞虽巳去世,但过去做过开封知府,所以辛弃疾每次来到,他总是殷勤接待,亲自陪着辛弃疾喝茶、闲谈,慢慢成了熟人。
现在,枣红马小跑着来到山泉旁边。和以往一样,辛弃疾在山门外的塔林前翻身下马,把缰绳甩给了迎上前来的当班和尚,便一径踱进寺来,穿过古柏参天的院子,登上了大殿。
展眼望去,排列在佛像两边的四十尊泥塑和尚,确实是不同凡响的艺术珍品。你看,各人有各人的姿态,各人有各人的表情。只要站到塑像前面,你就仿佛可以触摸到他们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甚至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辛弃疾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屏息静气:端详着这一尊尊塑像——不,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久久不能离去。他似乎从这里看到了当前这充满着灾难和痛苦的人生。今天,辛弃疾又在西边的一个塑像面前站住了,他凝视着,一动也不动。这是一个老僧,枯瘦的双手无可奈何地张在胸前,破旧的袈裟勉强遮掩着干瘪的身躯,眼眶里闪着泪光,但泪水巳快干枯,凄凉的眼神透露出他内心的孤独和绝望:这难熬的岁月什么时候才是尽头?看着这老僧凄楚的神情,辛弃疾的心紧缩起来。他想,在金人铁蹄下煎熬了几十年的父老乡亲,不同样快哭干了眼泪吗?难道能让金兵再渡淮过江去践踏南中国的土地吗?
辛弃疾正想得出神,忽然一阵铿铿铿锵的金属碰击声传到了他的耳边,心里非常诧异,便寻声走去,进了一个宽敞的院落。院落里摆满了兵器架,架上遍插着刀、枪、斧、戟之类兵器,原来义端正领着一群和尚在练习武艺。辛弃疾没有打扰,只在一旁观看。
不一会,义端发现了辛弃疾。他马上收起兵器,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双手合十,打个问讯(佛教的一种礼节),笑道:“辛公子,真是失迎得很,是什么风把您吹来的呀?”
“是西北风。”因为灵岩寺在济南的东南,所以辛弃疾这样风趣地回答。“在家里实在愁闷得慌,所以来看看大和尚。”
义端打了一个哈哈,说道:“公子生长富贵之家,还有什么愁闷的?”
辛弃疾叹了一口气,说道:“目下金人到处征丁夺马,看来又要对南方大动刀兵了……”
义端笑了笑:“这同我们佛门子弟不相干,反正不会碰到小庙这块清净之地的。至于府上……”
“那也不见得吧,”辛弃疾打断了义端的话头,试探地说道,“不然你这个以慈悲为本的佛门子弟怎么也耍起刀枪来了呢?”
义端叹息道:“您也知道,俺这庙虽不算大,田产倒也有好几十顷。正如公子所说,目下局面不稳,人心思乱,万一庙里的佃户放起刁来,不交租粮,那时不靠刀枪这玩意儿,庙里的几百号人岂不要喝西北风了吗?”
辛弃疾摇摇头,反驳道:“用这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庄稼人,算不得英雄好汉吧!”
义端见辛弃疾不以为然,搭讪地说道:“阿弥陀佛,这不过是以防万一罢了。我们出家人可不比你们读书人,除了念经之外,也需要打熬筋骨嘛!”
“看大和尚这般筋骨,倒真象是一尊铁铸的罗汉呢!”辛弃疾也调转了话题。
义端得意地说道:“见笑!见笑!不过,谈起这十八般武艺嘛,小僧倒还真有点根基。不是小僧夸口,认真较量起来,别说象公子这般读书人,就是几十个壮实庄稼汉,也休想近得小僧!”
辛弃疾一时兴致上来,笑道:“我可不信,咱俩来比试比试!”
义端只是笑,站着不动。
“怎么,胆怯啦?”辛弃疾故意逗引义端。
义端嘻嘻笑道:“小僧只是不敢。这刀枪是没眼的,要是误伤了公子,那可……”
辛弃疾一本正经地说道:“那可不一定,倘若我赢了大和尚呢?”
义端哈哈大笑道:“公子真会说笑话!”
辛弃疾见义端不肯比试,也就罢了。义端又把辛弃疾让到客堂喝茶、闲谈,态度非常殷勤。在交谈中,辛弃疾发现义端对兵书也颇为熟悉,不觉暗暗称奇。心想:“这个和尚倒不是个简单角色,可惜竟隐没在山林之中了……”
第二天,辛弃疾从灵岩寺回到四风闸,太阳巳快落山。刚要进庄,只见庄前柳树下系着三匹马。一个庄客迎上来接过缰绳,低声说了几句。辛弃疾点点头,径向堂上走去。堂上坐着一个县尉和两个百户长(女真族统治阶层中的下级军官),都是女真人。他们看见辛弃疾,也不站起来打招呼,只略略抬了抬眼皮。辛弃疾冷冷地问道:“几位有什么公干啊?”
“是这样,辛公子,”县尉解释道,“我们大金皇帝即日御驾南征,粮草催得紧。今天上午,知县相公派我带了几个差役到东边五十里地外的李家庄征粮,谁知那里的刁民竟造起反来。为首的几个人,本事好生了得,把我们的人打了一顿就逃走了。亏得这两位百户长相助,逮了几个闹事的主犯,一路押送过来。看看天色不早,怕路上再出差池,所以权借宝庄打扰一宿,明天一早就上路。”
辛弃疾眉头刚一皱,便立刻改容笑道:“好说,好说。几位请放心吧,到我庄上是不会出岔子的!”
一个百户长接嘴道:“当然,当然,府上的老大人做过我们大金的知府,公子现在又是一庄之主,还能信不过!”
“承情,承情。”辛弃疾一边应付,一边对庄客大声叫道,“快给我宰一头肥羊,杀两只高头,抬三坛上色酒来,好好招待客人!”
庄客忙去准备了。这里辛弃疾又向三人打了一个招呼,说是要到屋里去换一身衣衫再来陪客。他转过后堂,只见刘汉、刘忠正在等他,便使了一个眼色,一道进入内室。辛弃疾一面换衣,一面同刘汉爷孙俩商量。计议一番后,刘汉、刘忠就各自安排行事去了。
辛弃疾换了一身待客的衣衫,又回到堂上来。
不多久,酒菜都摆上了桌。辛弃疾起身把盏,殷勤地劝酒劝菜,又吩咐家人在下房招待同来的几个差役。县尉几个折腾了一天,肚里正饿得慌,当下也不客气,狼吞虎咽地吃喝起来。空肚子喝酒是最容易醉的,三坛酒才喝了半坛,县尉几个就已经东歪西斜,舌头转不过弯来了。下房里的几个差役更是喝得烂醉如泥,有的干脆就在桌肚里躺下,呼呼大睡。辛弃疾吩咐家人把他们分别安顿到客房里睡好,这才离开。
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几个差役惊醒过来,赶忙到牛房去带人。到得牛房前,只见门虚掩着,门上的锁已被打开。推开门一看,只是连声叫苦。几头牛在安静地吃草,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两手两脚被捆着,昨天抓来的农民却不翼而飞了。几个人慌了手脚,忙去向县尉报告。县尉等人赶到现场,辛弃疾和刘汉也随后来了。
县尉喝令差役解开小青年身上的绳索,掏出小青年嘴里的破布,盘问道:“你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小青年吐了几口唾沫,喘了几口大气,慢悠悠地说道:“昨天夜里,我来给牛添草料,谁知刚下了锁,开了门,就被人拦腰抱住,先用布塞了我的嘴,接着用绳子捆住了我的手脚,最后把门带上就走得无影无踪了!”
县尉呆呆地说道:“奇怪,昨天明明绑得结结实实的嘛!”他转过头,厉声厉色地对辛弃疾问道:“是谁把犯人给放了?”
辛弃疾冷笑道:“你问我吗?昨夜我不是同你们一样,喝得人事不知了?”
县尉又转向刘汉:“准是你!”
刘汉噗哧一笑,指着几个差役道:“你问他们!”
差役齐声说道:“汉老爹陪我们一齐喝的酒,他倒比我们先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