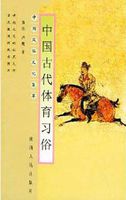《八娼九儒》一支曲儿
大冬天里,大年下的,人人吃得饱饱的,听支曲儿消食儿啊。待会儿还有表演呢。生活真是这么美好吗?可不,进了咱北京城了,就别说奔命来了。咱这座老城,站出来跟别人儿比比,除了文化还是文化。跟哪儿能听见文化呀?海子边儿上,大概其是条胡同儿就行。今儿是哪出戏啊?《窦娥冤》吧,元大都土生土长的,它走不了调儿。不给唱京戏吗?没到时候儿呢。是演员没化妆吗,还等几个钟头啊?再过三百多年吧。哪算了,元杂剧也好听。可不,关汉卿、马致远,还有好些优秀剧作家,他们那些个脍炙人口的巨作,可都是这元大都海子旁边儿长起来的。走着,咱也一路听去。
南边儿的戏,北边儿的曲儿。文艺的力量,无疑很伟大。您看看,《东海黄公》、《樊哙排君难》、《陈桥兵变》、《西厢记诸宫调》、《董西厢》;参军戏、傀儡戏、影戏、词话、院本、诸宫调、元杂剧……就这些个微薄的乐舞、小调儿,景明景暗,声高声低,它们散落在各个不同时代里,或演或唱,或低沉或张扬。总之,是以自己的方式折射着的现实生活的光影,还真真儿给劳苦大众找着精神寄托了。
百花丛中花开花谢,其中有一朵漂亮花儿就是北方杂剧。它赢得大家伙儿的心了。它好哪儿了?首先,杂剧替咱老百姓说话呀。您看,它歌颂人民反抗,揭露民族矛盾,也怒斥朝廷黑暗统治。它不回避现实,想要申张正义,不跟统治者一个鼻孔儿出气儿。来,咱插播一段儿。什么?《望江亭》,关先生的。您听:“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迫我步步相随。我呵怕什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越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觑着,看怎生地发付他赖骨顽皮。”
说的啥呀?这段儿是谭记儿唱的,也是个守寡的女子。后来,她改嫁给白士中,一段美好的姻缘刚刚开始。好家伙,恶霸后脚儿来了,说是奉了御旨,要杀害她夫君。糟了,还得再嫁一回。别介,这小女子宁死不屈,定要“发付他”,为自己的命运抗争。您想,咱老百姓没少挨欺负,哪儿敢说这个呀。嘿,这回出了气了。
杂剧还充分利用了原有的曲艺形式。您想,话本、词曲、讲唱,大家伙儿听惯了。元杂剧把它们揉和揉和,取优点去不足,饶上歌曲、舞蹈、表演、念白等通俗曲艺元素。曲词优美干净,通俗易懂,还琅琅上口。嘿,雅俗共赏了,老百姓没事儿也能哼几句。杂剧成功的塑造了底层民众的舞台形象。大元朝那会儿,剧作家创作水平整体有所提高,杂剧剧情也更趋于合理了。还有了关键性突破。突破什么了?您看看,咱这舞台不再关二爷,包大人他们家开的了。瞧见没,丫鬟、书生、衙役、妇人,平民老百姓,都在戏里寻着了自己个儿的影儿。这么着,蒙古族进驻中原期间,杂剧成为北方城市艺坛的独秀一枝。
“一本四折一楔子”,这是杂剧的基本模式,当然也有例外的,像《赵氏孤儿》,它是五折的;《西厢记》是五本连缀,共二十一折。杂剧本子有末本和旦本之分,三五个人一场戏,除了末角儿和旦角儿,其它人只说不唱。您看看,由男角儿主唱的,称末本,正末一唱到底;女角儿主唱的,叫旦本,由正旦一唱到底。瞧戏可比听书过瘾,您想,书场里上下翻飞一个人儿,听的说的都疲劳。杂剧就不介了,妖魔鬼怪,好人坏鸟儿……敢情,都活生生儿的到您跟前儿了。这不,来了个涂脂抹粉儿,怪里怪气的女人。谁呀?“搽旦”。衣冠表里呀,她就是“坏”女人的代表,专门儿撺掇西门庆潘金莲。对,就那样儿的邻居大妈,正合适这身打扮儿。杂剧角色分的细呢,您看,“孛老”就是老头儿、乞丐称“都子”、“驾”是皇帝、“来”是小孩儿……老太太叫做“卜儿”。对,《窦娥冤》里的蔡老婆婆就是“卜儿”。
瞧瞧,“蔡婆婆”她开腔儿了:“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不须长富贵,安乐是神仙。老身蔡婆婆是也,楚州人氏,嫡亲三口儿家属。不幸夫主亡逝已过,止有一个孩儿,年长八岁,俺娘儿两个,过其日月,家中颇有些钱财。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我数次索取,那窦秀才只说贫难,没得还我。他有一个女儿,今年七岁,生得可喜,长得可爱,我有心看上他,与我家做个媳妇,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岂不两得其便……”明白了,蔡婆婆先作了自我介绍:她孀居,领一八岁儿子单过,手头儿有些个积蓄。主要事件是借钱。窦秀才跟她借了二十两银子,利滚利,都四十两了,总是没有钱还不起。怎办呢?秀才闺女七岁了,挺好看的孩子,就是窦娥。蔡婆婆挺喜欢这孩子,跟她爹说,咱两家结亲吧,你欠我的债就了了。后来,阴毒的张驴儿父子,草菅人命的桃杌太守,都点了一笔。怎这么快呀?嗨,这是楔子,以总全剧之纲,不给您细说。什么时候儿说呀?折子里呗,那才是情节单元呢。您看,一个折子底下再包含若干个场次,有时折与折之间也有楔子,相当于过场戏。
大元朝是我国戏曲史上的巅峰时代,元杂剧作品见于书面记载的曲目超过五百种,今儿尚可寻见的剧本约一百种有余。您比方说,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王实甫的《西厢记》等等。元杂剧艺术精品不胜枚举,很得后世褒奖。有资料可考的杂剧作家达八十位以上。您看,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纪君祥、康进之、王实甫……优秀剧作家多了,他们都是大元朝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骄子。朱权《太和正音谱》誉:“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插嘴问一句,朱权是谁呀?他爸爸是朱元璋。“贤王奇士”朱权,封号宁献王,在兄弟中行十七,是明初年的戏曲家。公元1398,明洪武三十一年,《太和正音谱》成书,分上下两卷。《音谱》首卷着重阐释戏曲理论;次卷主要收录了绝大部分北方杂剧的曲谱。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就像朱权和朱棣,一个宁静淡薄,一个嗜权如命。所以朱棣当了大明皇帝,而朱权著成了很多典籍,比方说《茶谱》、《太和正音谱》、古琴曲集《神奇秘谱》、道教专著《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多着呢。
大元朝步月登云的的年景儿里,海子也随之丰裕起来了。您走近了瞧,波光映堤,柳成行,莺低飞,慕名而来的游人衣襟儿都挨着衣襟儿了。呵,连衽成帷就是这样儿啊。百花开时,一定会有蜂蝶翩跹吧。那些生活在元大都里的,知名的抑或平淡无奇的剧作家们,都曾是海子的客。那时,他们久久徜徉在这美丽的湖畔,亦觞亦咏,酬答唱作,下笔有神。关先生、马先生、纪君祥、王实甫,全都是土生土长的大都人。您看看,《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汉宫秋》、《赵氏孤儿》、《西厢记》……还有李好古《张生煮海》等等,这都是承了大都城水土滋养的经典剧作。没错儿,海子是元杂剧的摇篮,海子边儿上的胡同儿天天儿哼着摇篮曲。
书童:“我去哪里寻你?”丫环:“你去兀那羊角市头砖塔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说什么呢?替主子传话儿呗。怎回子事儿?约会。就为这个,张生把大海都烧开了锅了。是这样,潮州书生张羽进京赶考,就寄宿在西四辟才胡同儿的石佛寺里了。这个张生,实在是才华横溢啊,他不单做一手好文章,而且还懂音律。这不,闲来在寺中抚琴,乐声那叫悠扬,飘啊飘啊飘啊。飘哪儿去了?就到了东海龙宫了。不偏不倚,叫龙王爷的三闺女琼莲听见了。于是,神仙出海,琼莲“寻琴”去了。一见面儿,呵,郎才女貌,哪儿还顾得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么着,俩人儿一拉钩儿,就定好了。怎定的?八月十五月圆夜,你我再见。然后,琼莲回龙宫了,张生岸上等。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仙配仙,龙找龙,龙王爷的女儿却偏寻个凡间的姑爷回来。家里那个老父亲听了信儿,怎想也想不通了,急的脑仁儿疼。
眼瞅着,中秋节快到鼻子底下了,小龙女跟他爸还没协调一致呢。风筝断了线,俩人间不通音信了。哪儿能?琼莲的丫环不来了嘛,正跟张生的书童聊着呢。书童问得直来直去,丫环回的这句话有噱头了。怎么说?您看,“羊市角头”,又叫“角市”,咱老北京有两处儿,马、牛、羊、骆驼、骡子,其实带犄角不带犄角的,跟“角市”里全能找见。对了,是个倒腾牲口的地儿。这样儿的市场,西四有一处儿,另一处儿是东四西南角儿的枢密院角市。就为了这俩角市,政府在西四和东四各立了一个牌楼,说是要督促公平交易。丫环说的那个角市,十有八九是西四这个,因为离着张生的住处儿近便。您瞧瞧,西四牌楼前头儿,是个丁字街,您抬眼往西南,就望见砖塔胡同儿了。辟才胡同儿就在砖塔胡同儿南边儿,都在西四牌楼底下,两个长短相同,平行走向。您说,“总铺”是什么地儿?瞅瞅吧,坊巷之内,差不多三百多步就有一个,一个“铺”安着三五个铺兵。敢情,它大名儿叫军巡铺,主抓防盗防火,怎么也算是个官衙。这丫环她差点儿把张生支到“消防队”去了。对了,您要是没摊上案子,最好别跟它前头儿晃悠。
砖塔胡同儿、烟袋斜街、银锭桥这一竿子地界儿,连枝儿连理儿,呼吸间有着某种相似的气息。瞧瞧,勾栏、瓦肆、酒楼、饭馆儿、旅店,都备全和了。吃喝玩乐,好哪口儿您就进哪个门儿。“八娼九儒十丐”几乎一样的爱着海子,也爱着海子跟前儿的胡同儿,因为这里有他们赖以存在的土壤。什么八、九、十啊?等级,人的等级。大元朝那会儿,人民群众共分十等,而儒生排在第九,竟然比娼还低了一等。官,排在了一等。但是,一等的官爷和九等的儒生,全有着近似的爱好。您看,“儒丐娼”们最扎堆儿的去处儿,也通常也安插有官府的“便衣”。咱北京城的胡同儿真是叫什么的都有,您听听,“猪”市口儿、骡马市、“狗尾巴”……总归,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手儿取名字的多。老皇历翻过去,“打劫”胡同儿,就叫大吉胡同儿了。可是,砖塔胡同儿没改过名儿。砖塔胡同儿看什么呀?青楼女子,说白了这并不是个好去处儿。剧作家爱去,是收集创作素材,达官贵人也去,为的是寻个乐子。真怪了,当初怎没听它叫过“妓院”胡同儿呢。嘿,胡同儿得“逛”,牌坊也得立。比方说,胡同口儿上,张县令、李捕头一不留神,俩人儿走对面儿了。这互相心里明镜儿似的,好说不好听。愣装成没瞧见,使不得。眼珠子一转,嘿,瞄见万松老人塔了。得,大大方方的:来了,您呐。可不,今儿又“拜塔”来了。
十九世纪上半叶,砖塔胡同儿又迎来了两位文学巨人。鲁迅先生先到的,1923年8月2日下午,他离开阜城门内八道湾胡同,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可能是新中国以后吧,砖塔胡同儿的门牌号有些变动,鲁迅先生这处院子叫八十四号了。1946年2月,张恨水先生也来了,从南京来的。打那以后,北沟沿儿甲二十三号的大院子就是“张宅”了,四进,有三十多间房,大院儿的后门就冲着砖塔胡同西口儿。1949年,张先生卖了北沟沿儿的大院子,正式搬到了砖塔胡同,再就没走。
大元朝走了,海子也干了。我们,是干等着京戏来吗?别介,大明朝写了多少小说儿、话本呢,咱可以瞧故事啊。您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人家有仨。还有《封神演义》、《金瓶梅》……没人不知道。故事可以读,当然也可以唱。咱北京城自有态度。您看,乐是乐儿,苦也是乐儿。走着,咱找乐儿去。
天子的天,天子的桥
您看,元、明年间,京都南郊的珠市口儿、永定门一带,水渠错落、河泽广布。其中,由虎坊桥儿出发的一条小河缓缓东流,从北京城的南中轴线潺潺而过。春日伊始,河岸边,杨柳提早欢快起来了,它们在暖洋洋的和风中甩开水袖儿。然后呢?就静静期待着莺来轻歌,燕来低语。这么一来,连带着夏和秋,总共三季。您看看,柳芽儿,柳叶儿,燕回燕走,直到落叶钻回泥土的那一时刻,这流水、这香花、这飞鸟、这行人,全都游在一幅活着的山水画儿里。北国的冬天素来是缺少色彩的,北京城也是一样。唉,冷了,咱也该别处儿去吧。别介,我们还要趁着霜雪的写意,站在冰封的河水旁张望呢。枯树,冻河很有诗意是吗?您看那石桥,那座架在河上的,为了过河的桥。嗯,桥单孔、拱券高、身极陡、通体汉白玉制,栏板、望柱、镇兽,雕工甚是精美呀。这是什么桥啊?天桥。谁从桥上过呀?皇上呗。
明朝初年,永乐皇帝在正阳门正南五里偏东一侧兴建了“天地坛”建筑组群,在偏西一侧建山川坛建筑组群。两坛东西相望,分别作为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祈谷和祭祀农神的场所。每年孟春时节,皇帝从紫禁城出正阳门到“天地坛”的祈谷坛行祈谷之礼,以祈丰年;仲春亥日到山川坛祭祀农神、行躬耕之礼;冬至日到“天地坛”的圜丘坛行祭天之礼,以期一年平安。
早年间,南城多水。所以,皇上要去到那些坛庙,必须过桥。您看,皇帝是天子,天子所走之桥——对了,天桥。那会儿,为了强调这桥的特殊身份,平日里都用木栅栏将桥封锁。敢情老百姓过河都得游泳啊?不介,您请绕行。绕哪儿?对不起您嘞,“天桥”两边儿,木头桥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