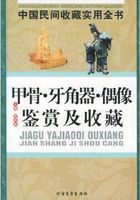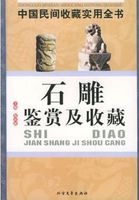唐代的俳优表演主要以参军戏为主,参军戏也属于一种滑稽谐谑的优戏,偶尔也借用对白、动作对时事进行讽刺。一般认为,参军戏起于石勒参军周延的盗官绢,“后每设大会,使与俳儿,着介帻,绢单衣”,重复“受审”以使其受辱。这种由当事人直接参与的表演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演员,而且具有戏弄的性质。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参与表演的“着介帻”、“黄绢单衣”,这已经可以看做是比较固定的行头妆扮。
唐代的参军戏表演非常盛行,据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06号墓出土的一批土木俑来看,这些“正在演出”的土木俑,“滑稽木偶也着黄绢单衣,动作表情也正似“斗数单衣”,又狼狈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似乎这些木偶也正是弄馆陶令的傀儡。”以上土木俑的时间在贞观年间,属于唐朝初期,与之前的演出区别不是很大,这种演出风格知道盛唐前后,还有弄真人的情况出现。以《太平广记》卷四九六所引温庭筠的《干巽子》为例:
及(陆象先)为冯翊太守,参军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于是与府僚共约戏赌。一人曰:“我能旋笏于厅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可乎?”众皆曰:“诚如是,其输酒食一席。”其人便为之,象先视之如不见。又一参军曰:“尔所为全易,吾能于使君厅前,墨涂其面,着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趋而出。”群寮皆曰:“不可,诚敢如此,吾辈当敛俸钱五千为所输之费。”其二参军便为之,象先亦如不见。皆赛所赌以为戏笑。其第三参军又曰:“尔之所为绝易,吾能于使君厅前,作女人梳妆,学新嫁女拜舅姑四拜,则如之何?”众曰:“如此不可,仁者一怒,必遭叱辱。倘敢为之,吾辈愿出俸钱十千,充所输之费。”其第三参军遂施粉黛,高髻,笄钗,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为怪。景融大怒曰:“家兄为三辅刺史,今乃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语景融曰:“是渠参军儿等笑具,我岂为笑哉?”
以上记载为真实的参军对上级官员的戏弄,并不是俳优的演出,但我们可以想象,诸参军之所以敢如此胆大妄为,必然是由于自己的官职与“参军戏”中的参军脚色同名,即使戏弄上级有点过分,也可以借演参军戏为名免于责罚。
到了盛唐时期,俳优的演出形态上就有了很大变化,尤以“韶州参军”的出现为其标志。据《乐府杂录·俳优》载:
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参军’,盖由此也。
另据陆羽《陆文学自传》记载:
因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诣伶党,着《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
可以看出,开元间唐代出现了“韶州参军”的演出,而且这种演出非常盛行,以至于到咸通时仍有擅此戏者演出。而且,从盛唐开始,“韶州参军”逐渐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弄“假吏”的演出形式。
前文谈到,唐之前的参军戏要让犯官直接入戏,戏弄的为真人或当事人,即使像陆象先的被迫演出,也属于真正的官员的直接“表演”。但到了陆羽时,则发展为戏弄对象由“假吏”来扮演,就是以优人扮演假官而非官员扮演假官,并接受戏弄,这可以说既是参军戏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同时也是戏曲因素——“表演”在俳优表演中的发展。
唐代参军戏有参军和苍鹘两个基本角色,为了达到应有的表演效果,参军和苍鹘之间构成了特定的配戏体制和表演关系。从表演方式上看,参军戏主要通过两个角色之间的相互问答来演述故事,同时辅以一定的表情、动作。也就是说,参军戏以科白表演为主要方式。这和宋代以来“合言语、动作、歌唱演一故事”的戏曲表演方式显着不同。在舞台上,参军、苍鹘之间有着明显的角色分工,参军是主角,苍鹘是配角,参军是正角,苍鹘是丑角,参军的表演相对严肃、庄重,而苍鹘的表演则比较活泼、诙谐,参军是故事的主要叙述者,而苍鹘起辅助、配合的作用。这种表演体制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相声表演,参军与苍鹘的角色分工也类似于相声中的捧哏与逗哏。
另外,根据一些古代我文献可以得知,苍鹘在舞台上是可以扑打参军的,如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院本名目》条:“鹘能击禽鸟,末可打副净。”这种形式即使在今天的相声舞台上也可以看到,如逗哏演员用扇子等物件扑打捧哏演员的情形就与此相类。虽然有一些研究者对陶宗仪的说法持有异议,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唐代参军戏的演出的确开始有了明显的角色分工,有了表演地位的变化,还有表演功能的区分。这种分工到了宋代的杂剧中便逐渐发展为副净与副末的表演关系。而且,在宋杂剧中,有副末击打副净的表演,这种表演进一步影响到了元杂剧的演出与发展。
在“韶州参军”之后,中唐时期又出现善弄“陆参军”的刘采春,据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条载:“(元稹)乃廉问浙东。别(薛)涛已逾十载,方拟驰使往蜀取涛,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这条记载透露的信息是唐代的俳优表演不仅仅是“白”,还有“歌”,这其实也是戏曲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时有融合的表现。唐代的参军戏很普及,李商隐的《娇儿诗》中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的诗句,路延德《小儿诗》中也有:“头依苍鹘裹,袖学柘枝揎”的诗句,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参军戏不但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而且普及到妇孺皆知的程度。
唐代是一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佛、道两教尤其兴盛,一度成为了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局面,因而儒教、道教、释教三教之间互相辨难、发明义理的讲经宣教活动,即所谓“三教论难”的情况也时有出现。唐代规模较大的“三教论难”活动有两次。一次是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降诞日,三教讲论。儒者第一赵需,第二许孟容,第三韦渠牟,与僧谭延嘲谑,因此承恩也。”另一次是另一次“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诞日,(白居易)奉敕召入麟德殿内道场,对御三教谈论。”这些“论难”其实三教之间为了说明自己教义的合理性而所做的学术辩论,是否曲直虽然很难说清,但唐王朝对三教并立给予了极大的宽容,而这种论难给社会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言论自由的社会氛围,这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心性解放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儒家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挑战,侮圣贤、渎乱经传之俳语片断不断出现,连一直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也成为了戏弄的对象。相对于官方的学术论争,俳优的表演就完全是借用这种自由的氛围所进行的谐谑演出。以插科打诨为主,兼有戏拟性装扮表演“弄孔子”的表演甚至发展成为了一种特殊的戏剧形式。出自《太平广记》所引唐代侯白《启颜录》“读书岂合不解”是比较早的一条优人戏弄孔门弟子的俳语记录:
北齐高祖时优人石动筩观国子博士论难,因问七十二达者着冠之事,博士言经传无载。动筩曰:“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辨之?”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座中大噱,博士无言以对。
这种表演可能是一个片段,从“座中大噱”的演出效果来看,观者对于优人通过曲解《论语》所造成的笑料是非常喜欢的,即使今天读起来也有可笑的成分,我们可以从这种取我所寓,以虚为实但妙在言中的表演中,看到参军戏中表演的概况。
唐代“弄孔子”最有名的当属《李可及戏三教》,据唐人高彦休《唐阙史》载:
咸通中,优人李可及者,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惊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而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喻。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为何人?”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以上表演虽然“亦当属参军戏”,但内容相对完整,陈寅恪明确指出:“《白氏长庆集》伍玖有《三教论衡》一篇,其文乃预设问难对答之言,颇如戏词曲本之比。”
另外,唐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合生”据洪迈的《夷坚志》乙集卷六“合生诗词”载:
江浙间,路歧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于席上指物题咏,应命辄成者,谓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
张安国守临川,王宣子解庐陵郡守印归,次抚。安国署酒郡斋,招郡士陈汉卿参会。适散乐一妓言学作诗。汉卿语之曰:“太守呼为五马,今日两州使君对席,遂成十马,汝意作八句!”妓凝立良久,即高吟曰:“同是天边侍从臣,江头相遇转情亲。莹如临汝无瑕玉,暖作庐陵有脚春。五马今朝成十马,两人前日压千人。便看飞诏催归去,共坐中书布化钧。”安国为之叹赏竟日,赏以万钱。
也就是说,,所谓“合生”,应该是一种“指物题咏,应命辄成”的表演形式,与之相关的“滑稽含玩讽者”称之为“乔合生”。关于这种表演形式的记载最早见于《新唐书·武平一传》:
后宴两仪殿,帝(中宗)命后兄光禄少卿婴监酒。婴滑稽敏给,诏学士嘲之,婴能抗数人。酒酣,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因倨肆,欲夺司农少卿宋廷瑜赐鱼。平一上书谏曰:“……伏见胡乐施于声律,本备四夷之数。比来日益流宕,异曲新声,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妖胡人街市童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舞蹈,号曰合生。昔齐衰,有《行伴侣》;陈灭,有《玉树后庭花》,趋数骜僻,皆亡国之音!夫礼慊而不进即销,乐流而不反则放。臣愿屏流僻,崇肃雍,凡胡乐备四夷外,一皆罢遣。
《武平一传》中所记载的合生是一种演唱形式,这与后来洪迈《夷坚志》中的记载有出入。到了宋代,合生的表演就更为普遍,宋初张齐贤《洛阳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载:
有谈歌妇人杨萝,善合生杂嘲,辩慧有才思,当时罕与比者。少师杨凝式以侄女呼之,盖念其聪俊也。时僧云辨,能俗讲,有文章,敏于应对。若祝祀之辞,随其名位之高下对之,立成千字,皆如宿构。少师尤重之。云辨于长寿寺五月讲,少师诣讲院,与云辨对坐,歌者在侧。忽有大蜘蛛于檐前垂丝而下,正对对少师于僧前。云辨笑谓歌者曰:“试嘲此蜘蛛,嘲得者,奉绢两匹。”歌者更不待思虑,应声嘲之,意全不离蜘蛛。而嘲成之辞,正讽云辨。少师闻之绝倒。久之,大叫曰:“和尚!取绢五匹来!”云辨且笑,遂以绢五匹奉之。歌者嘲蜘蛛云:“吃得肚撑,寻丝绕寺行,空中设罗网,只待杀众生。”盖云辨体肥而肚大故也。
以上记载其滑稽玩讽之意味颇有戏剧性,几与先秦两汉、南北朝与隋唐俳优表演一脉相承,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在进行“合生”表演时,应该是一种既有语言、动作,又有歌唱与舞蹈的综合表演形式,是否还有一些简单的情节不得而知,但无疑,这种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大量戏曲的因素,对后世戏曲的形成同样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节戏曲其它因素的发展历程
以上从戏曲的四大因素出发分别从歌舞与表演形式进行了论述,但由于中国戏曲是一门综合艺术,除四大因素外,还有很多其它艺术形式也对戏曲的形成和成熟有很多关系,所以,我们撷其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论述。
一、傩舞傩戏中的戏曲因素
傩,也称“大傩”,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形态,本是古代原始宗教领域内的巫术活动,是由上古时图腾崇拜仪式直至商周逐渐形成的一种驱鬼劫病的祭祀仪式,与我国古代的蜡祭(即在每年的十二月,人们扮成各种神兽,头戴面具、载歌载舞来祈求长寿的祭祀活动)、雩祭(旧时祈雨的一种祭祀,周时极为成行,设有专司雩祭的司巫官,求雨时众多巫女戴面具歌舞,向上苍祈求)并列成为中国三大祭祀仪式。由于傩是攘祭活动,是先民自然崇拜的产物,所以,其表演样式和审美观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被民间所认同,即使是当代社会,民间依旧在年节之时,还会进行各种不同的面具舞的表演形式。由于面具舞是傩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与我国戏曲中的脸谱有着及其相似的地方,因而在傩舞傩戏的流传过程中也对我国戏曲的成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据《说文》解释,傩的本义是“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段玉裁注:“行有节度。按此字之本义也。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摊为驱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也就是说,傩的本义是行为有节度,而当其作为驱逐疫鬼解的时候,其含义就失去了原来的意思,成为了“难”的假借字。